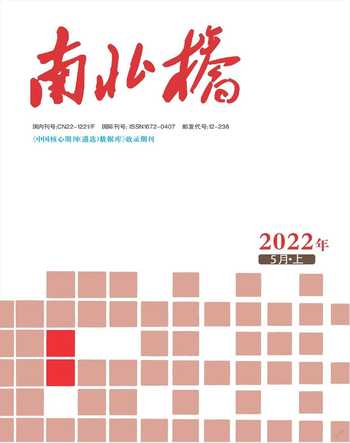轉化型搶劫罪之調查研究
[ 作者簡介 ]
周芳,女,河北衡水人,青海民族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方向:刑法學。
[ 項目名稱 ]
青海民族大學研究生創新項目,項目全稱:“轉換型搶劫罪之調查研究”(項目編號:04M2021012)。
[ 摘要 ]
轉化型搶劫這一概念最早提出是在雅典時期亞里士多德的著作《雅典政體》中,隨著西方法律觀念的不斷發展,在羅馬帝國時期搶劫和盜竊被正式地定義為了兩種性質不同的犯罪。隨著我國學界對于刑法的研究不斷深入,轉化型搶劫作為刑法學界中具有較強爭議性的內容成為許多學者關注的熱點。在中國社會經濟全面發展正步入新時期的今天,刑法的發展應當配合時代的變化,針對存在的轉化型搶劫問題進行進一步的探索與明確,以此來保障實踐的落實。在此背景下,推動轉化型搶劫相關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加大轉化型搶劫的研究力度是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刑法體系的必由之路。對于轉化型搶劫罪,世界各國的刑罰規定也各有不同。為針對轉化型搶劫進行更全面的深入研究,以更進一步的方式探討轉化型搶劫在當前國情下的實際應用,未來轉化型搶劫的相關研究將會更加集中于轉化型搶劫在我國的具體實踐適用方面。
[ 關鍵詞 ]
轉化型搶劫罪;搶劫罪;犯罪構成
中圖分類號:D9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22.09.029
1 “轉化型搶劫罪”的概念
轉化型搶劫罪是指實施了盜竊、詐騙、搶奪行為,在行為過程中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行為。法律之所以將轉化型搶劫擬制為一種犯罪,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它具有嚴重的人身與財產雙重法益侵害的屬性,并嚴重損害了社會穩定。
2 轉化型搶劫罪研究現狀
2.1 國內研究現狀
根據筆者的調查研究,目前國內針對轉化型搶劫犯罪的研究現狀主要爭論焦點為:
第一種觀點被稱為盜竊說,該觀點認為他人的暴力行為屬于實行過限,先行為人對暴力予以沉默是反對表達,不應對暴力負責,僅構成盜竊罪。事先與他人共謀實施盜竊罪,但未參與實施后續的暴力、威脅行為的,只構成盜竊罪共犯,而不構成準搶劫罪的共犯。幫助犯是指在共同犯罪中,對決定實施犯罪的行為人提供援助或使其實行行為易于實施的一類犯罪參與形態。無論是物理的幫助還是精神的幫助都須達到對正犯實行行為有直接重要影響。先行為人沒有對暴力行為人提供犯罪工具犯罪場所,也未一同實施暴力行為,可以認定沉默行為與結果之間不存在物理因果聯系。關于心理性的因果關系的認定:第一,先行為人的沉默行為雖然表明對暴力手段的知曉,但知情不等同于故意且其未實施暴力行為,既不能進行目的支配也無法實現對行為的機能控制。第二,先行為人的沉默行為只是表明其知道暴力行為人轉化為事后搶劫,無論暴力行為人對于先行為人的沉默進行默認的同意理解或是客觀上使其暴力行為易于實施,只是暴力行為人“單通道”的理解,而未形成兩者之間較為明確的事后搶劫的共同犯意,兩者不構成事后搶劫的共犯。
第二種觀點被稱為搶劫共同犯罪說。該觀點認為即使先行為人未實施暴力行為,但是其與暴力行為人關乎暴力行為的性質及其所造成的結果存在犯意溝通,達成犯意聯絡,形成轉化型搶劫罪犯罪故意,其行為應轉化為搶劫罪,與暴力行為人構成轉化型搶劫罪共同犯罪,只是在量刑層面按照主從犯、社會危害性進行分別處罰。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關于審理搶劫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對轉化型搶劫共犯作出了進一步解釋,關于共同盜竊下部分行為人實施暴力,其他行為人是否全部轉化為搶劫罪,關鍵在于其與暴力行為人關于暴力有無達成共識、提供援助,成為幫兇。由此可知共同盜竊下,部分人為窩藏贓物等特定目的而實施暴力,在其他未使用者加入暴力手段的情況下,是否構成轉化型搶劫罪應從未實施暴力的先行為人對暴力行為人及其暴力的態度來認定。
2.2 國外研究現狀
持有真正身份犯說觀點的前田雅英教授主張真正身份犯,認為轉化型搶劫罪盡管損害了財產和人身雙重法益,但本質屬性是侵犯財產法益的犯罪,沒有盜竊犯的暴力行為僅侵權了人身權益,不具備本罪完整犯罪構成要件,不能獨立成立本罪,但可以和具有盜竊身份的行為人構成共同犯罪。采用廣義的身份說,即身份是特定的資格、社會地位或特定的法律關系。將盜竊犯理解為具備盜竊法律關系身份,且是一種定罪身份,無盜竊犯身份不能成立轉化型搶劫。先行為人盜竊被發覺為窩藏贓物等而實施暴力,構成轉化型搶劫;后行為人雖不具備盜竊身份,不能獨立成立轉化型搶劫罪,但在知曉了轉化型搶劫犯的盜竊行為后仍然和其共同對事主實施了暴力手段,具備轉化型搶劫的共同犯罪故意,與其構成轉化型搶劫的共同犯罪。
持有不真正身份犯說觀點的山口厚教授主張不真正身份說。即盜竊行為帶來的特殊地位是一種量刑身份,即對量刑的加減產生影響的身份。不具備盜竊犯身份,而實施暴力只能成立強制罪或者是單純恐嚇罪;而盜竊犯基于護贓等特定目的而使用暴力手段則成立搶劫罪。由于我國未規定強制罪或者單純恐嚇罪,所以對于未實施先前的盜竊行為,僅為窩藏贓物等而實施暴力的行為人可以采用故意傷害罪來進行規制。行為人盜竊被發覺為防護贓物等而實施暴力,成立轉化的搶劫罪;后行為人不具備盜竊這一加重刑罰的身份,其暴力行為造成事主輕傷以上的后果則成立故意傷害罪。先行為人盜竊被發覺為窩藏贓物等而實施暴力,構成轉化型搶劫;后行為人雖不具備盜竊身份,不能獨立成立轉化型搶劫罪,但在知曉了轉化型搶劫犯的盜竊行為后仍然和其共同對事主實施了暴力手段,具備轉化型搶劫的共同犯罪故意,與其構成轉化型搶劫的共同犯罪。
3 我國轉化型搶劫罪中存在的問題
3.1 轉化型搶劫罪與搶劫罪行為要件界限模糊
關于如何準確定位轉換搶劫罪的司法實踐和刑法理論都存在著很大爭議。因為轉化型搶劫罪與搶劫罪有很大的相似之處,但卻是一種比較復雜的搶劫形式,所以一般把兩者放在一起比較。為解決這一問題,以轉換搶劫罪的定位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最終通過區分轉化型搶劫與搶劫罪的行為要件之方式明確了轉換搶劫罪與搶劫罪的異同。
3.2 先行為的范圍,以及后實施暴力行為的犯罪階段問題
通過案情介紹和對爭議焦點的分析,第二次盜竊后實施暴力的行為是否犯罪、構成何罪這一切入點,首先論證第二次盜竊行為構成盜竊罪,符合認定轉化型搶劫罪的前置犯罪要求;第二個層面再通過對轉化型搶劫罪客觀行為的分析,從正面論證第二次盜竊后實施暴力的行為符合轉化型搶劫罪的構成。
3.3 轉化型搶劫罪中的共犯認定問題
在罪名認定上具有特殊性和復雜性。共同犯罪是各犯罪人互相配合的犯罪方式,更易于造成法益損害的后果,較之于單獨犯罪具有更大的社會危害性。轉化型搶劫共同犯罪結合了兩者的特征,加之法律規定的原則性和模糊性、理論界的學說爭論以及現實生活中案例的錯綜復雜,使得司法實務中對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的相應條款存在不同理解,在轉化型搶劫共同犯罪的認定上采取不同的標準,出現同案不同判。
3.4 轉化型搶劫罪中是否存在既遂、未遂問題
犯罪形態是中國刑事法學基礎理論上非常關鍵的問題,要想進一步完善中國刑事理論體系,怎樣正確定義犯罪的既未遂形態是其非常關鍵的一方面。同時既未遂的正確界定還能影響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這么重大的一種學說,在中國的刑事學術界始終缺乏統一的概念,關于此學說的具體定義也始終存在較大的爭論。最高人民法院曾在《關于審理搶劫、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意見》第10條規范過既未遂的問題,此“意見”對搶劫罪的既未遂問題也進行了很清楚的定義。不過,轉化型搶劫罪與普通的搶劫罪畢竟是不同的犯罪,雖然二者都有很多的共性點,但并沒有完全混為一談,那么在我國司法機關實踐中,怎樣對轉化型搶劫罪的既未遂問題加以準確解釋呢?
轉化型搶劫罪的既未遂性問題爭論頗多,但不少專家或學者對此問題都有自己獨到的看法:首先,如果行為人所采取的先前行動已經既遂,轉化型搶劫罪才可以成立,而這個標準是指采取了先前行動的人所采取的較粗暴或威脅的手法,才可以使財物最終被被害人所搶奪。若是行為人所盜的財產最后被追繳,那么這個案件便是未遂,若是財產最后被行為人所獲得,則案件便是既遂。很顯然這個論點認為,轉化型搶劫犯的得逞與否同先前行動的既未遂密切相關,只有行為人所采取的先前行動既遂的,最后方可形成轉化型搶劫犯。筆者并不是很贊成這個說法,因為這個說法明顯與基本實際相悖,轉化型搶劫的行為罪,也就是說不管后果怎么樣,只要行為人最終采取了危害活動,就會構成本罪,即使目的尚未達成,也不能影響本罪的確立。再者,盡管基本作案不是全部完成,不能獲得被盜物品,但因為抗拒逮捕和破壞罪證都是該罪的設立條件,出于這幾個目的所進行的暴力犯罪,有可能會形成轉化式搶劫罪。第二,根據行為人所采取的暴力或脅迫的行動來確定既未遂,如果犯罪行為是根據刑法所規定的三種目的而采取了暴力、脅迫等行動,即使先前罪行也是因基本罪行而不能得手,轉化為新的搶劫罪也算既遂。
4 轉化型搶劫罪的司法認定及立法完善
4.1 從兩階層的角度明確犯罪構成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規定的轉化型搶劫罪是指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行為。應當修改為實施盜竊、詐騙、搶奪行為,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行為。從客觀違法階層,明晰轉化型搶劫罪的客觀危害行為是什么,再通過主觀責任階層對轉化型搶劫罪做整體評價。一是可以使罪與非罪之間有一個明確的界限;二是這樣的立法規定有利于更加準確地認定該罪先前行為的范圍,從而明確該罪的犯罪構成要件。
4.2 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發生的階段
根據我國刑法中行為與目的同時存在原則,行為人的先前行為的故意并不能理解為搶劫的故意,只能理解為先行行為的故意,實施先行行為并非是該罪的實行行為,此時并非該罪的著手,只有著手時才會成立該罪,即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只會發生在該罪的著手實施階段,該罪沒有發生于犯罪預備階段的余地。從這一分析不難看出,轉化型搶劫罪有其自身的特點,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并不是所有的犯罪都有相同的犯罪階段。
4.3 只參與實施先行行為的情況下不構成共犯
根據部分犯罪共同說,我國刑法規定的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共同的內容有所不同,一種情形指行為人共同實施了偷盜行為,且僅一人(或一部分人)為保管贓物等,當場對他人使用了暴力,則僅參加偷盜活動的一人是否成為轉化型搶劫罪的從犯。
按照我國刑法的規定,無責任能力者是不構成轉化型搶劫罪的共犯的。 其理由主要在于首先這不符合我國刑法關于共同犯罪的規定。先前行為的共犯人即便具有先行行為的共同故意,也不構成轉化型搶劫罪的共同犯罪。根據前田雅英教授的觀點,即便只是具備犯罪身份,由于后行為沒有實施,無法轉化為整體的共犯。二者只在前行為中構成共犯。
5 結語
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刑法法律體系的完善來說,轉化型搶劫罪是實現法律體系完善的關鍵一步,本論題的研究重點正在于轉化型搶劫成立的要素上,筆者需要根據現有資料,結合自身所學知識,進一步明確轉化型搶劫這一罪名的具體成立要件。除此之外,本研究的重點與難點部分還集中在學界觀點的總結上,目前我國學界針對轉化型搶劫罪的各類爭議較多,學者的意見不一。筆者需要在結合大量文獻調查的基礎上將大致持有同一觀點的學者進行分類,再通過結果論的視角反推學者的觀點,詳細揣摩不同學者的研究思路。法律思維的嚴謹更讓筆者體會到了思維的邏輯性。筆者深深地體會到學習法律不僅僅是學習理論層面的知識,更要深入實踐去分析和處理問題。法律讓筆者明辨是非、追求真理、客觀公正,這是學習期間筆者的感悟。學習法律讓筆者具備了辯證思維、證據思維、公平思維、平等思維、權利思維、程序思維、尊重客觀事實等法律思維。這對于筆者今后的學習將有極大的幫助。
參考文獻
[1]石魏,余亞宇. 扒竊轉化型搶劫罪中對公共交通工具不能重復評價[J]. 人民司法,2013(14):66-68.
[2]肖中華. 論搶劫罪適用中的幾個問題[J]. 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學院學報),1998(5):84-90.
[3]王彥強. 區分加重構成與量刑規則罪量加重構成概念之提倡[J]. 現代法學,2014(3):116-129.
[4]柏浪濤. 加重構成與量刑規則的實質區分——兼與張明楷教授商榷[J]. 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6,34(6):52-61.
[5]方圓. “轉化型”搶劫危險物品行為的刑法適用[J]. 經濟刑法,2019(11):189-196.
[6]趙益奇. 轉化型搶劫法律認定的邏輯順序解構[J]. 中國檢察官,2018(16):58-61.
[7]陳振. 論轉化型搶劫[J]. 山西青年,2019(14):79-80.
[8]柴國娥,杜瑞娜. 轉化型搶劫罪及其既遂與未遂標準的認定[J]. 中國檢察官,2017(22):80.
[9]趙擁軍. 轉化型搶劫罪的司法認定思路及其要點[J]. 青少年犯罪問題,2017(5):88-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