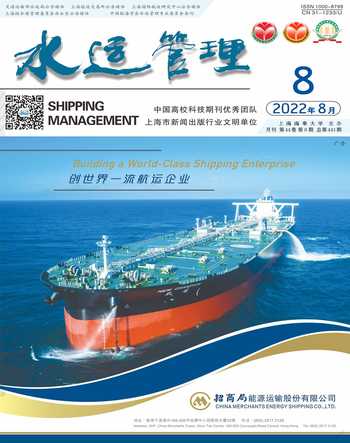艙位互換經營模式下實際承運人的認定
劉博林
【摘 要】 為正確認定在艙位互換經營模式下的實際承運人,闡述艙位互換的定義和性質,分析在艙位互換經營模式下實際承運人認定的關鍵要素包括對是否接受承運人委托的認定和對實際從事貨物運輸的認定兩個方面。由實際案例分析得出:實際從事貨物運輸不僅包括船舶的實際控制人,還應包括海上貨物運輸的實際組織者和操控者;此外,艙位互換的出租方簽發提單也是正確識別實際承運人的關鍵因素。
【關鍵詞】 承運人;艙位互換;實際承運人;提單
1 艙位互換的定義及性質
1.1 艙位互換的定義
在海上貨物運輸業務中,隨著各航運企業之間的合作關系越來越緊密,合作方式越來越多樣化,航運企業之間以艙位互換經營模式開展合作的情形也越來越常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海運條例》(以下簡稱《國際海運條例》)第14條第3款規定:“以共同派船、艙位互換、聯合經營等方式經營國際班輪運輸的,適用本條第一款的規定。”可見,艙位互換經營模式已是我國法律法規明確規定的國際船舶運輸經營者的經營方式之一。
我國《國際海運條例》未給出艙位互換的法定定義,國內學界對此定義也并不統一。天津海事法院在某一涉及艙位互換模式的代理合同糾紛案件判決中,對該種經營方式作了如下定義:“艙位互換”是指有兩家以上的集裝箱船公司組成的航運集團,各船公司分別提供一艘或多艘性能及設備相近的集裝箱船,通過相互協商,共同調整班期,各船公司在彼此的集裝箱船上都擁有一定比例的艙位使用權,以承運集裝箱貨物或者空集裝箱,船公司之間獨自承攬各自的集裝箱貨。[1]
結合上述定義,筆者認為艙位互換的定義可以歸納為:航運企業之間通過協商一致簽訂合作合同,在獨自承攬的貨物運輸業務中,彼此利用對方船舶的艙位完成相關貨物運輸服務的經營活動。
1.2 艙位互換的性質
關于如何認定艙位互換協議的性質,學界看法也不統一,主要存在“租用性質論”和“買賣性質論”兩種觀點。“租用性質論”強調艙位互換協議具有互租性質,各經營者彼此間相互租用對方的一部分艙位;“買賣性質論”則突出艙位互換協議具有買賣性質,一方經營者購買對方船舶艙位,同時又將自己的船舶艙位出賣給對方,雙方之間為雙向的艙位買賣關系。
根據艙位互換定義,結合實踐,筆者認為艙位互換的性質實際上是一種租賃關系,理由是:
(1)艙位互換的船公司之間僅享有對方船舶艙位的使用權,并不享有所有權。如果認為艙位互換具有買賣性質,無疑是承認了雙方享有對方船舶艙位的所有權。從上述天津海事法院對艙位互換的定義來看,“各船公司在彼此的集裝箱船上都擁有一定比例的艙位使用權”也是強調了艙位使用權這一說法。
(2)根據航運實踐,艙位互換協議一般都是有期限的,但按買賣性質來理解,所買賣的艙位則不應有期限限制。基于此,艙位互換的本質應該為艙位互租,艙位互換的雙方互為承租人和出租人,兩者互付租金和互受租金,在實踐中可以通過相互抵消的方式來結清租金。
2 案例分析
2.1 問題的提出
2015年12月,國內某環保公司向國外K公司購買一套環保設備,賣方K公司委托S公司將該套環保設備從波蘭某港口運輸至天津港,S公司接受委托并向K公司簽發了提單。然而,S公司并未實際從事貨物的運輸,其接受委托后又將貨物委托給日本某航運公司進行運輸,日本某航運公司簽發了海運單。其后,涉案貨物在收貨人處發現損壞,某保險公司在賠償被保險人(某環保公司)損失后,取得代位求償權,起訴日本某航運公司,認為其是本案貨物的實際承運人,要求其賠償損失。然而,日本某航運公司否認自己是實際承運人,辯稱其與案外人C公司簽訂有《船舶共用和箱位分配主協議》。根據該協議,其使用C公司的船舶艙位出運貨物,該船舶的實際經營人為C公司。
該案是海上貨物運輸中的涉及艙位互換經營模式的典型案例。S公司與K公司訂立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根據我國《海商法》第42條第1款的規定,S公司就是該案貨物運輸的承運人。S公司接受委托后又將貨物委托日本某航運公司進行運輸,如果日本某航運公司接受委托后實際進行了貨物運輸,根據我國《海商法》第42條第2款的規定,日本某航運公司是該案的實際承運人。但實際上,由于日本某航運公司與第三人C公司簽訂有艙位互換協議,涉案貨物實際是由C公司經營的船舶運輸的。在此種情況下,正確認定實際承運人是破解案件問題的關鍵。
2.2 不同實際承運人的認定
艙位互換經營模式的出現使得一艘船上可能同時出現若干個實際承運人。從當前司法實踐來看,艙位互換經營模式所帶來的法律問題首先是實際承運人的認定問題。
我國《海商法》第42條第2款對“實際承運人”作了規定,“實際承運人”是指接受承運人委托從事貨物運輸或者部分運輸的人,包括接受轉委托從事此項運輸的其他人。根據這一定義來看,實際承運人的構成要件有以下2點:(1)接受承運人的委托,承運人的存在是實際承運人存在的前提;(2)實際從事貨物運輸或者部分運輸。在海上貨物運輸中,還經常出現轉委托的情形。然而,只有真正從事貨物運送的人,才具有實際承運人的法律地位。
由此可見,實際承運人應當為接受承運人的委托或者轉委托后實際從事貨物運輸或者部分運輸的人。正確認定實際承運人應從我國《海商法》對實際承運人的定義和實際承運人的構成要件兩個方面進行,即:該主體是否接受了貨物運輸承運人的委托;該主體接受委托后是否實際從事貨物運輸或部分運輸。這也適用于艙位互換經營模式下實際承運人的認定。
(1)對是否接受承運人委托的認定。實際承運人是受承運人的委托參與到海上貨物運輸過程的,承運人是實際承運人進入海上貨物運輸過程的媒介和存在的前提,認定是否是實際承運人首先要識別其是否接受了承運人的委托。該案中,S公司與K公司訂立海上貨物運輸合同,S公司是涉案貨物的承運人,接受承運人委托的是日本某航運公司。雖然貨物最終由第三人C公司經營的船舶運輸,但第三人C公司并未接受承運人的委托,日本某航運公司的行為也并非轉委托,C公司不符合實際承運人的構成要件。
對是否接受承運人委托的認定問題比較容易辨析,在理論和實踐中容易出現爭議的是如何正確理解“實際從事貨物運輸”這一問題。
(2)對實際從事貨物運輸的認定。是否實際從事貨物運輸是識別是否是實際承運人的另一個關鍵要素。在理論和司法實踐中對“實際從事貨物運輸”的理解存在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是以船舶的實際控制人作為認定實際承運人的標準,即認為只有船舶的實際控制人才是實際從事貨物運輸的人;第二種觀點認為除了船舶的實際控制人外,海上貨物運輸的實際組織者和操控者也可以認定為實際承運人。
在艙位互換經營模式下,甲公司承運的貨物并不一定裝載到甲公司經營的船舶上,而是根據船公司之間的合作協議來決定運輸的船舶,有可能是裝載到乙公司經營的船舶上,甚至可能是裝載到其他船公司經營的船舶上。在此情形下,甲公司并不一定實際控制了運輸該票貨物的船舶,但其仍然是該票貨物運輸的組織者和操控者,與該船舶的實際控制人共同完成了貨物運輸。筆者認為,海上貨物運輸的實際組織者和操控者也可以被認定為實際承運人,甲公司對海上貨物運輸的組織和操控行為也應該被認定為“實際從事貨物運輸”的行為。
該案中,日本某航運公司是全程運輸的組織者,其負責在裝港和卸港保管并照料集裝箱和貨物,安排轉運及在目的港交付貨物,是實際參與到海上貨物運輸的部分環節中并履行相應的運輸義務;因此,可以認為其實際從事了涉案貨物的運輸,符合我國《海商法》中關于實際承運人的規定,是該案的實際承運人。
天津海事法院在某一無單放貨賠償糾紛案件的判決中認為,實際從事貨物運輸不能簡單理解為利用自有船舶或經營船舶進行運輸,還應包括海上貨物運輸的實際組織者和參與者。[2] 這進一步肯定了第二種觀點。
2.3 正確識別實際承運人的關鍵因素
在實踐中,艙位互換的雙方關于互換行為的協議通常約定的是一段時期,且航線往往是固定的;因此可以認為,艙位互換協議包括了一個時期內的多個航次租船合同,艙位互換的雙方互為出租人和承租人。在艙位互換經營模式下,艙位互換的出租方簽發提單也是正確識別實際承運人的關鍵因素。
我國《海商法》第95條規定:“對按照航次租船合同運輸的貨物簽發的提單,提單持有人不是承租人的,承運人與該提單持有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適用提單的約定。”根據該條規定,圍繞提單持有人可作如下分析:
(1)若艙位互換的出租方簽發提單,而提單持有人不是承租人,則出租方與提單持有人之間的法律關系應當定性為提單關系。在此種情形下,以提單法律關系作為基礎,可能存在實際承運人。
(2)若艙位互換的出租方簽發提單,且提單持有人為承租人本人,則出租方與提單持有人(即承租人本人)既存在航次租船合同關系,又存在提單關系。根據我國《海商法》立法的本意來看,此時兩者之間的法律關系仍應當定性為航次租船合同關系。原因是此種情形下只有出租人與承租人,缺少承運人這一媒介,不存在實際承運人。
由此可見,在艙位互換經營模式下,只有在艙位互換的出租方簽發提單,且提單持有人并非艙位互換的承租方的情況下,才會出現實際承運人的問題。該案中,第三人C公司既沒有向日本某航運公司簽發提單,也沒有向其他人簽發提單,因此C公司與日本某航運公司之間的法律關系可以認定為航次租船合同關系。
3 結 語
艙位互換本質上是一種艙位互租,雙方互為出租人與承租人關系。
在艙位互換經營模式下,實際承運人的識別應抓住實際承運人構成要件中“接受承運人的委托并實際從事貨物運輸”這一最本質的法律規定;海上貨物運輸的實際組織行為和操控行為也應該被認定為“實際從事貨物運輸”的行為,海上貨物運輸的實際組織者和操控者也可以被認定為實際承運人;艙位互換的出租方簽發提單也是認定實際承運人的關鍵因素。
參考文獻:
[1]王寧,艙位互換下實際承運人的識別[J].中國海商法研究,2020(4):74-80
[2]劉棟,現代集裝箱海運業務中實際承運人的識別:大連SC有限公司訴香港YT有限公司、HH海運有限公司無單放貨賠償糾紛案[J].世界海運,2011(9)::4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