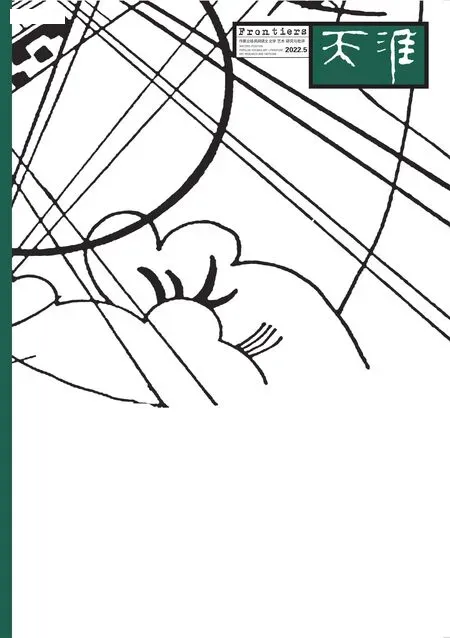七個消失的故事
雍措
一
降澤是阿媽去地里撒青稞時生下的娃。生降澤的那天,全凹村的人都在地里撒青稞。這天是尼瑪村長請格勒活佛打卦算出的春播日。尼瑪一回凹村,挨家挨戶把這個春播日說給了凹村的人聽。聽完尼瑪帶回來的好消息,村人的身子朝向格勒活佛身處的寺廟雙手合十,鞠躬,嘴里默默念誦著六字真言。等尼瑪走后,他們回到屋里,凈手、煨桑、誦經,感謝格勒活佛為凹村選定的春播日。凹村每年的春播日都是請格勒活佛打卦算出的,這么多年有格勒活佛的加持,凹村播種的青稞很少遇到干旱和蟲災,青稞長得郁郁蔥蔥,每家每戶的糧倉被豐收的糧食裝得滿滿當當的。生降澤的那天,朝霞把遠處的雪山涂抹得紅紅的,雪山頂上懸掛著一朵像馬匹的紅云,馬匹上馱著一個人,他朝著凹村的方向張望,仿佛是一個即將遠道歸來的人遠遠看著凹村。當時凹村的人都在忙碌著這天的春播,煨桑、備馬,從經堂里取出被祈福了一年的種子放在自家的馬背上。人們在忙碌中都看見了那朵紅云,無論是正準備出門的人,還是已經在路上的人,都放下了手中正在忙碌的事情,駐足,對著那朵紅云念誦起了六字真言。有一朵像人騎著馬的紅云向凹村張望,人們更確定今天是播種的吉祥日,一邊說著祈福吉祥的話,一邊向自家空了一個冬天的青稞地走去。那天全村人念誦六字真言的嚶嚶聲飄浮在凹村的上空,仿佛凹村在這個早上發出的一種聲音。那朵紅云是在凹村人的誦經聲中慢慢消失的。降澤的阿媽身子笨重,走在最后。降澤的阿爸和爺爺等不及,趕著馱著青稞種的牦牛走在了前面。降澤的阿媽走到一棵老樹下時,走不動了,她感覺降澤在自己的肚子里動,隨后是一陣連著一陣的痛。她后悔沒聽降澤阿爸不讓她下地的話。她扶著老樹喊降澤的阿爸和爺爺,聲音顫顫的,沒傳出去多遠,就被晨風吹斷,落在了離自己不遠的地上。降澤的阿爸和爺爺早就走到前面去了,一條通向青稞地的路空空地擺在那里。降澤的阿媽知道,今天是凹村忙碌的日子,不會有像她這樣一個人遲遲地落在最后。降澤的阿媽滿頭大汗,她感覺自己身體的隱私部位正在慢慢打開。這種打開是一種她沒辦法控制的打開,這種打開是一種就快撕碎自己的打開。她快昏過去了,但是她知道無論怎樣,她都不能讓自己就這樣倒下去。眼前是一棵早年枯死的老樹,樹的根部有個大大的黑洞,降澤的阿媽忍著劇痛,慢慢爬進黑洞里,在那朵紅云消失的時候,她在這棵枯死的老樹的洞里生下了降澤。降澤的第一聲啼哭是從一棵枯樹里傳出來的,直直地、嫩嫩地順著一棵空心的枯樹傳向半空中。后來,降澤在凹村慢慢長大,長得不聲不響的。我們都沒注意降澤的長,一個娃的成長就像一棵小樹的成長,一兩天沒見就馬上變了一個樣。娃在小的時候,除了自己的家人會天天盯著看——特別是有些心虛的阿媽,生怕自己的娃長著長著就長成自己偷偷相好過的那個人的樣子了——外人是不關心別家一個娃的成長的。外人不太關心的原因是外人不可能每天盯著別人的娃看,反正幾天不見一個娃就變了,過幾天不見又變了,自己記不住一個娃的變,干脆就等這個娃長定型了,才慢慢去記住這個定型的人。一個人在什么時候是定型的,看過幾茬生死的人總結說過,一個娃會走幾步歪路,會說幾句嫩話了,這個娃其實就定型了。這些人說,不信你們看,一個娃在凹村剛走出一兩年的步子和這個娃在凹村活過幾十年之后走出的步子的姿勢是一樣的,一個娃剛學會說話的樣子和這個娃在凹村活過幾十年之后說話的樣子是一樣的,一個人幾歲和幾十歲的差別就在于骨頭長粗或長大,身體長胖或長瘦,皺紋長多或長少,其他是沒什么變化的。只有一種情況會改變一個人的生長,就是一個人生在凹村,后來卻不在凹村生活了。這樣的人,他在外面踩的路和在凹村踩的路不一樣,他在外面說話的語氣和在凹村說話的語氣不一樣。他在外面聽見的聲音和在凹村聽見的聲音是不一樣的,這樣的人再回凹村,無論怎么糾正他都回不到從前了。降澤長大后可能也聽過幾茬生死的人說的這些話,有一次我在路上遇見降澤,他問我,生他的那個樹洞可不可以讓他走出凹村?我抬頭望望那棵樹,那個樹洞在降澤成長的日子里,沒什么變化。那天那個樹洞陷在黑蒙蒙里,一只喜鵲站在樹上,一會兒飛到地上,一會兒又飛上樹頂,偶爾的叫聲落在越來越深的黑里,很快就消失了。我告訴降澤,樹洞是喜鵲的路,不是他的路。降澤聽完我的話,死死地盯了樹洞好一陣子,最后他告訴我,喜鵲有路,他就有路。這事沒過多久,降澤就在凹村消失了,沒人看見降澤走出凹村,但降澤就是不在了。降澤不在凹村的那天,雪山頂上又出現了一朵像馬匹一樣的紅云,上面馱著一個人,只是這個人不再向凹村張望,而是緩緩朝遠處走去,直到消失。那年,降澤十二歲。
二
那些年凹村的土地上長出了一種植物,那種植物是突然從凹村的土地上長出來的。人們最先沒有在意那種植物,只把那種植物當做是一種新長出來的草對待。在路上看見那種植物,手里拿著鐮刀的人一個順手把那種植物割了丟在路邊;肩上扛著鋤頭的人如果沒有太要緊的活,也會順便彎個腰揮起鋤頭把那種植物挖掉扔了。人們最先都是隨意地在對待那種植物。人們想,草總歸是草,干不了什么大事,不想把過多的精力浪費在一種自己不認識的草上面。凹村的動物是人教出來的,人不待見的東西,凹村的動物也不待見。人們經常看見一些狗把屎尿往那種植物身上拉,拉了再放個響屁,一溜煙跑了。一群大雞帶著小雞常常圍著那種植物使勁地啄,啄了一地莖葉不吃不說,還仰著頭圍著那種植物一個勁兒地吵鬧,仿佛一群雞在不分青紅皂白地罵那種植物。還有凹村的牲口,明明可以繞著那種植物走,它們卻偏偏不,故意往那種植物身上踏,踏一腳不行,還要回轉身再補上幾腳。凹村養慣的懶風,睡醒了,想刮幾下了,就往那種植物身上刮,身子刮歪了不解氣,非得把那種植物刮到趴在地上好一會兒,才悻悻離去。人們空閑的時候,坐在一起笑話這些凹村的動物和風,說凹村的動物和風鬼得很,跟人一樣。有人說,你們偷偷看索拉家養了八年的那頭豬,竟然一點不出老相,又或者說豬出老相不像人出老相一樣一下就看出來了,豬有一張黑皮和茂密的毛藏著它的老。那頭豬跟了索拉八年,還跟一頭年輕的豬一樣,眼睛水靈水靈的,吐氣和吸氣剛剛硬硬的。索拉在人前最得意的事情就是凹村沒有誰家的豬活過了他家豬的歲數,按索拉的話說,他家的豬在凹村祖祖輩輩的豬中算得上是豬仙。一天索拉把“豬仙”當個寶帶出來在人前晃,索拉走在前面感覺整條路都是他家的,屁股扭得都要甩出了身體,那頭豬跟在索拉后面,豬仗人勢,屁股跟索拉走路的屁股一模一樣,那扭法,見一次就想上去踹一次。還有你們看,卓瑪家那匹馬,你們有沒有覺得和其他家的馬有什么不同?經人這么說,坐在一起的人皺著眉頭想,想了好一陣子也想不出結果。說的人繼續說,你們想不出結果,那是你們平時只注意到漂亮的卓瑪,沒關心卓瑪家的馬。卓瑪家的馬和別人家的馬看人的眼神都不一樣,歪著頭,隨時淚眼汪汪地眨巴著眼睛盯人,那勾人的眼神和卓瑪就像一個模子里倒出來的,害得凹村的很多馬見著卓瑪家的馬就慌了神,路不好好走,活不好好干,必要的時候莫名其妙地為那匹馬打上幾次閑架。經說的人這么一提醒,聽的人都記起了自己家的馬見卓瑪家馬的樣子。人人直搖頭,這凹村的動物都活成精了。回到那種植物上。人們發現,無論人怎么對待那種植物,凹村成精的動物和風怎么學著人對待那種植物,那種植物一直在長。有人曾經用鐮刀割掉和用鋤頭挖掉的那種植物在扔掉的地方重新長起來,植物的樣子越長越不像草的樣子,葉子方方的,稈黑黑的,粗粗的根直直地往凹村深土里鉆,在根鉆過的地方凹村綠綠的莊稼慢慢枯萎。人們說不能由著這種叫不出名字的植物在村子里繼續撒野。在凹村,自古以來只有沒長大的娃可以在人前撒野,沒長醒的動物可以在人前撒野,一股村子養熟的風可以在人前撒野,還沒見過一種叫不出名字的植物可以在人前撒野的。人們說,植物在人面前撒野得治,一種植物撒野不治,以后一凹村的植物都給人撒起野來就麻煩了。植物和植物之間,別看在地上頭不挨著頭,手不牽著手,一個個傲氣得很,鬼才知道它們在地下干著什么。凹村人對治這種植物的想法積極起來了,第二天老村長就組織村人扛著鋤頭去挖這種植物。大家分兩路挖,一路從村東頭開始往村子中間挖,一路從村西頭往村子中間挖,想的是先挖完村子里的,再去挖青稞地里的。大家開始挖的那天,天上的云從天空的東西兩頭往村子中間飄,風從村子的東西兩頭往村子中間刮,動物各分兩撥跟在大家的屁股后面往村子中間擠,它們都是來幫忙的。人們知道凹村的所有人都在幫忙,挖這種植物的時候雄心壯志,不想把自己活了幾十年的臉面丟在凹村的云面前、風面前、動物面前。人們先是把自己帶來的鋤頭舉得高高的,往土里挖,一挖一個坑,一挖一塊板結的土就松動了,那時全身都是滿滿的成就感。這種成就感讓人們全身上下似乎都充滿了力量,一個間隙都舍不得休息,想使勁地挖,一刻不停地挖。后來人們發現坑大根本沒有作用,坑再大這種植物的根還深扎在土里。為了節省力氣,人們把坑挖小,耐著性子慢慢順著這種植物的根往下理,越往下理根越深,越往下理根越粗壯。在理的過程中,還發現,這種植物除了在地上長枝長葉,還在地下長枝長葉,地下葉子長得好的地方,油亮亮的,跟抹了一層自家壇子里的豬油一樣光亮。人們愣住了,說這種植物仿佛不是從地下往上長的,而是從地上往下長的。人們繼續挖,挖到一人深還見不到植物的底,挖到兩人深還見不到植物的底,上面的人往下喊,見底沒有?下面的人悶聲悶氣地說,還沒有見底。過了兩個時辰上面的人又往下喊,見底沒有?下面的人說,還沒有見底。天暗下來,上面的人把下面的人一個個從土里拉出來,出來的人全身附著一股生土味兒,告訴外面的人說,越往下挖,下面的葉子一層比一層密,越往下挖,那種植物的根粗壯得像一棵樹的樹干。大家說,今天挖不出來,明天再來挖,明天挖不出來,我們后天再來挖,我們總不能輸給一種叫不出名字的植物。那些天,凹村處在一片人心惶惶中,人們回到家心是散的,剛想做的事情正準備去做馬上就忘了,剛說著的話下半句就不知道說什么了,要站在原地想好一會兒才想起自己要去做什么,想要說什么。那些天,總能看見一些人站在一個地方,愣愣的,什么話也不說,一直盯著腳下的地看。那段時間人們開始懷疑自己腳下的地,說活了幾十年了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懷疑過自己住慣了的一塊地。人們一直認為,人對地掏心掏肺,地就會對人掏心掏肺。人沒事的時候經常對地說掏心窩子的話,現在才知道地從來沒把地下正在發生的事情給人說過一次。而且自從天天開始挖這種植物之后,人們發現地在騙人,地可以讓一樣東西腳朝上、頭朝下地長。地平時長給人吃的都是些敷衍人的東西,從那種植物身上可以明白,地在地下藏著很多不為人知的秘密。地騙了人,不但騙了現在的凹村人,還騙了凹村的祖祖輩輩。人們開始恨地,鼓著大眼睛盯著地恨,教凹村的動物和風,走在地上要多往地下看,多用點力氣在地上,免得地在眼皮子下騙他們。人們知道這樣做,對一片騙了凹村祖祖輩輩的地來說,起不到任何作用,但人們想的是,起不到任何作用不要緊,至少要讓一塊自己住慣了的地知道,凹村的人不再像以前那么傻,凹村的動物和風不再像以前那么傻,凹村的人、動物和風已開始注意到它了。自從那之后,凹村刮的風都是從地面刮起來的風,風刮得遲遲疑疑的,刮得滿天都是凹村地上的土,風在幫人掏土,風想幫人看看土里到底有什么?凹村的動物,對地也多了一份疑心,走幾步往地下踏兩下,踏完之后,側著耳朵聽地下的聲音,它們想聽自己在踏過兩步之后,地下有沒有什么動靜。那段時間,人們還沒有放棄追著一種叫不出名字的植物的根往下挖,越挖越深,越挖越深,下去挖的人本來挖一天回一次家,后來挖兩天回一次家,再后來挖三天回一次家,再后來挖十天回一次家,最后下去挖的人有幾個就再沒有回過凹村。人們在地上面大聲往下喊那幾個人的名字,聲音在一個很深很深的洞里一直往下竄,至于喊出的聲音竄到哪里去了,人們說不清楚。人們想自己的聲音可能也往下長了,就像那幾個沒有歸來的人,也往下長了。
三
我不知道措姆在哪里,很多人都不知道措姆在哪里。有人說措姆早死在了十年前,也有人說措姆沒有死,路過措姆以前生活過的房子,總覺得那座荒廢的房子里有人住,房子里偶爾傳來水缸里舀水的聲音,不過仔細聽那聲音又沒有了。也有人說,措姆不可能生活在那座房子里,一個人十年不可能不走出房子,她總得吃東西過日子,可誰都沒有看見過她家的煙囪里冒過一次煙。還有人說,一節煙囪冒沒冒煙有時還真說不準。凹村人做飯都在一個點上,即使有幾個急性子和慢性子的人哪天沒有按這個點做飯,他們也不會拖得太長。也就是說,凹村煙囪里冒出的煙基本都在同一時間,不過凹村好事的風,特別是人做飯的時候風最愛來,仿佛凹村的風也是來蹭人的一頓飯吃。風一來,凹村上空的煙就亂了,誰家的煙囪冒沒冒煙誰知道?說到煙囪,人說措姆以前最愛她家的那個煙囪,措姆給人說過,人與人之間比要在煙囪上比,煙囪是朝天長的,煙是往天上升的,一家人的氣和話都可以通過一座房子的煙囪和煙捎到天上去。措姆每年都要請人修整一次煙囪,每修整一次,人們看見措姆家的煙囪又往上升了一節,措姆家的煙囪是凹村最高的煙囪,也是平時冒煙最勤的煙囪。那時就有人問措姆,你一天讓煙冒得那么勤,是不是通過煙囪給天上捎了很多話?措姆笑著說,捎了,捎了,幫你們也一起捎了。人問措姆,你幫我們捎什么話給天了?措姆神秘地說,這就不能隨便說出來了,要不就不靈了。措姆這樣說,人知道從她嘴里問不出啥,也就不問了。措姆那么愛自己家的煙囪,如果她在房子里就不會忍心看著自家煙囪上的土今天被幾只鳥啄走幾粒,明天被雨水沖走幾粒,后天被風吹走幾粒。在措姆的心中,那是她和天說話的一個通道,絕不允許誰去破壞它。那措姆去哪兒了?人們又問起最初的這個問題,答案還是最初的答案:不知道。措姆是在凹村一點一點地消失的。措姆剛嫁到凹村時,哪里都可以看見措姆的影子,即使哪一天沒看見措姆,措姆的歌聲也會在某個角落里傳出來告訴別人她在哪里。那時凹村人說,松尕找的老婆不是老婆,是只百靈鳥。松尕說,百靈鳥怎么啦?讓你們看得見、聽得見就是抓不住。有人說,松尕你娃是那個半山上的塔修得好,第一年修第二年就娶了個好老婆回來。松尕得意地說,那是一個人的命,該我松尕的就是我松尕的。有段時間,松尕的臉上常常洋溢著一道莫名的光,那種光讓松尕無論走在再多的干活的人群中,都馬上能讓人從灰撲撲的人群中把松尕辨別出來。那段時間,松尕是個內心生長光亮的人。人們都認為松尕會把這種光亮延續下去,但是很快發現,松尕內心的光在某個誰都沒有察覺的晚上或早上慢慢丟失。丟失光亮的松尕垂頭垂腦的,說出去的話、呼出去的氣弱弱的,打蔫得很。他把日子過得閑散起來,每天沒事就在村子里閑逛,哪里人多就垂頭垂腦地往哪里蹭,哪里事多就垂頭垂腦地去哪里湊熱鬧,人和事都沒有的時候,他就跟在一群牛、一群羊、幾只狗中間湊一群畜生的熱鬧。人們都不知道松尕怎么了,松尕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他說自己的心在這三年間突然就松了下來。這種松是他沒法控制的松,讓他感覺自己的身體里有某個東西在扯著自己。他說,這種扯來得快去得也快,那東西在身體里扯自己的時候,他感覺自己的身體在正在走的路上、正在說的話里、正在笑的聲音里下墜,自己的夢也會因為這種扯停上好一會兒。心松下來就什么都不想干了,松尕說,感覺自己不是自己,自己沒有自己。他每天眼睛一睜開,腳就不停地想讓他往外走,即使他的身子不想動,腳也一個勁兒地扯著身子。他說,他心里明白,卻什么也做不了,他的身子只能跟著腳往外走,哪里熱鬧他的腳就帶他往哪里去。后來他說自己病了,他的病表現在身子在變,眼睛耳朵鼻子在變,手在變,只有一張嘴巴沒變。起初他用嘴罵他身上正在變的這些東西,最初他罵出的話是他想罵的話,可過了沒多久,他罵出的話就變成了一些其他的話。那些話都是一些討好他身上正在變的東西的話,他氣極了。但他氣了也沒有用,他的生氣只能表現在他的“吱吱”咬牙上,他的生氣并不影響他身體的其他地方。有人說,松尕你就是在給自己的懶找理由,你的手腳、眼睛、鼻子都長在你自己的身體上,你怎么會控制不了它們?那人說著就去拉松尕的手,一拉松尕的手,就趕快把手縮了回來。拉松尕手的人說,松尕的手心很硬,沒有一點皮膚的彈性,像一塊在角落里放了好多年的鐵。措姆是在松尕的變中一點一點在凹村消失的。最先消失的是措姆的歌聲,措姆剛到凹村來時,天天都能聽見措姆的歌聲,后來隔一天才能聽見一次,慢慢隔幾天才能聽見,后來只有夜里才聽見,再后來夜里也聽不見了。接著一點一點消失的是措姆的影子,以前凹村婚喪嫁娶上都少不了措姆忙里忙外的影子,后來措姆在婚喪嫁娶上的身影一次次地減少,最后婚喪嫁娶上再看不見措姆了。再后來一點一點消失的是措姆在土地上干活的身影,以前措姆干活把鋤頭舉得高高的,力氣用得大大的,挖出的土松松的。后來人們看見措姆在地里干活,鋤頭越舉越低,地越挖越淺,剛挖過的地上到處長著沒有鋤盡的草。措姆的地越種越荒,越種面積越小,措姆漸漸沒有了地。措姆家的羊群讓措姆越放越少,有人說,措姆,你家的羊咋越來越少了?措姆說,她放出去是一群,回來就少了,到山上去找,一只也找不到,羊回羊自己的家了吧。晚上,人看見凹村的燈全在黑暗里亮起來了,措姆家的燈要在天黑后好久才亮起來,亮起來沒多久,又很快地熄滅了。再后來,無論春夏秋冬,無論天上有沒有月亮,措姆家的燈都很少亮了,人們不知道措姆和松尕在黑夜里是怎么過的。人們后來說,措姆是一點一點把自己從白里過到黑里去的,是一點一點把自己過得沒有自己的。措姆就這樣一點一點消失在凹村,但很多人說,感覺措姆沒有離開凹村,只要走到措姆以前種過的地邊,路過措姆家的木窗邊,都能聞到措姆的味道,那味道淡淡的,帶著最后人們見她時那種說不出來的憂傷。松尕一直待在凹村,有人經常看見一個腿扯著身子走的人在凹村的地里、山上晃蕩,那時的松尕已經不說話了,他的嘴長得歪歪的,把半邊臉都拉得變了形。有人說,那個松尕已經不是松尕了,松尕把自己的一切都失去了。這樣的一個松尕在凹村是怎么活到十年之后的,人們搞不明白。可能有某種東西在暗地里幫松尕活吧,有人說。
四
貢布和我同歲。確切地說,貢布大我一天。貢布的阿媽生貢布的時候難產,兩天兩夜生不出貢布。貢布的阿媽躺在床上滿頭大汗地急自己,她說,她之前生過兩個娃,也沒生貢布這么難,早知道生第三個娃這么難,她就不生了。貢布阿媽在生貢布的時候,勁兒特別的大,氣特別的足,但不管她的勁兒有多大,氣有多足,就是生不出肚子里的貢布。這些勁兒和氣憋在貢布阿媽小小的身體里沒處使,快炸了她的身。接生婆說,你把它們都使出來,無論用什么方法都使出來,千萬別讓它們在你身體里壞了你的身。貢布的阿媽開始喊,郎澤你個牛犟的,力氣不用在土地上,天天晚上來折磨我,這下好了,所有的罪都得我來受,你卻躲得不見了蹤影。郎澤你個雷打的,白天你就跟個死灰似的,放哪兒軟哪兒,東頭的那塊地叫你去種你不種,你非說太遠,走著腿軟,那塊地因為你腿軟今年荒了一年。澤郎你個牛犟的,你腿軟,晚上老娘就沒見你腿軟過,你是一頭夜里的野牦牛,你說你就是一頭野牦牛,在夜里你可以耕完凹村所有的地。貢布的阿媽在屋里咬牙切齒地喊罵,從她嘴里罵出的每一個字都有一種深深的疼附在上面,仿佛每一個字都跟著疼起來。郎澤能感覺到從貢布阿媽嘴里罵出的每個字的疼,他躲在窗戶外聽貢布阿媽罵,他知道這個罵是作為丈夫的他該承受的。他聽一陣,賊賊地蹭著身子往拉著布簾的窗戶里看一陣,又偷偷地蜷縮在墻角抽一支煙。那兩天郎澤的臉皺巴巴的,無數道皺紋像凹村的一道道地坎一樣一層層爬到他的臉上。有人看見郎澤跟條老狗一樣兩天兩夜守在窗戶前,于是站在小路上取笑他,要你晚上還那么多勁兒,勁兒要分散著用,看你家那塊荒地,草一人多高了,高高地立在凹村干干凈凈的地中間,荒得我們都臉紅。地是懂得羞的,地一羞幾年都不給你長出好糧食。你郎澤倒好,不懂一塊地的羞不說,跟個沒事人一樣,把一身蠻勁全用在夜里,這下好了吧!郎澤撿起地上的土塊就往那人身上扔,那人邊跑還邊笑著說,勁兒別往一處使,要分散著使。人走了,郎澤這兩天沒有放上山的牦牛嘎嘎走過來,郎澤最疼這頭叫嘎嘎的牦牛,他摸著嘎嘎的頭,知道這兩天虧欠了嘎嘎,他嘴里說著道歉的話,眼睛不時朝屋里看。嘎嘎是郎澤平時嬌慣了的牦牛,懂幾分人心,它見郎澤對自己不用心,心里生氣,抬著頭就往郎澤看的窗戶里哞哞地叫。嘎嘎一叫,貢布的阿媽在屋子里本來就生不出貢布,更氣。你個嘎嘎,沒良心的,你跟郎澤是一個樣,腦袋里整天想的都是些不三不四的事情,別以為我不知道,郎澤晚上在我身上撒勁兒時,你就在屋外豎著耳朵聽,有好幾次我一抬頭就看見你那黑黑的眼珠在屋外泛著光,見我看你,你立馬跺著步子轉身看其他地方了,你別以為我不知道你在裝,我這輩子是犯什么錯了,都來欺負我。牛看看郎澤,郎澤看看牛,都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自從貢布的阿媽罵了牛之后,牛忍著扁下去的肚子,再也不叫了。貢布是在阿媽罵了兩天兩夜之后生下的。那兩天兩夜,貢布的阿媽把凹村的什么都罵遍了。貢布后來說,他在肚子里就聽見了阿媽的罵,他是故意不想出阿媽的肚子的。我說,貢布你吹牛,人在肚子里是啞巴、聾子,人在肚子里就跟人在墳墓里一樣,是不知道外面發生什么事情的。貢布說,那是你笨,不過不只是你笨,其實很多人都很笨。很多娃在阿媽的肚子里時,只知道睡覺,很多人從上一輩子到下輩子都是睡過來的,這個過程在很多人那里就像一場夢。說到這里,貢布問我,在你身上有沒有發生過這樣一些事情:一個地方你明明是第一次去,但看什么都很熟悉,仿佛這個地方你早早就去過一次了?你有沒有遇見過一個人,明明是才認識,但一見他就好像已經認識了很多年,你們的這次遇見只是對過去很多年的認識的一次回顧?你有沒有見過一件事情明明才發生,但就在發生時,你的腦海里閃過一些莫名的回憶,仿佛這件事已早早發生過,你甚至能說出這件事情最后的結果,而你說出的結果恰恰就是那天那件事的結果?我埋頭想,想著想著我想到有一次我從日央村路過,在路上遇見一個女人,她手提茶桶,穿著紅色的毛衣,外面套著一件棕色的藏袍,她一眼一眼地看我,雖然我和她是第一次見,可總覺得在哪里見過。貢布見我思索,說,有吧?我說,有又能說明什么?貢布說,有就說明人的上輩子和這輩子像線一樣連著,很多人認為一輩子過完了這輩子就結了,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我說,貢布,那你知道你上輩子是什么嗎?貢布說,當然知道。我說,是什么?他說,是鳥。我不信。貢布說,你肯定不信,因為你在你阿媽肚子里是睡過來的,而我不是,我在阿媽的肚子里一直醒著,我是親眼看見自己從上輩子走到這輩子來的,是慢慢向一只鳥告別的過程。你知道我當初為什么不想從阿媽肚子里出來嗎?我搖頭。他接著說,我當時是舍不得那只鳥,我知道我只要從阿媽的肚子里出來,我的人生就是另外一種人生了。貢布這樣說,我突然想到有人說過,貢布一出阿媽的肚子,眼睛睜得大大的,嘴里嘰嘰喳喳地亂叫,他用手去抓旁人的手,沖每個人笑,好像一生下來的貢布就經歷了很多人生。你記得嗎?我們第一次見面,我就喊出了你的名字,貢布說。我說,我不知道,但我聽阿媽說你是個聰明的娃,阿媽還說你以后肯定是凹村大有出息的人。貢布笑笑,并不告訴我他為什么第一次見我就知道我的名字。貢布說,我總有一天會重新變回一只鳥,飛得高高的,飛得和我的上輩子接上。我說,貢布,鳥是你上輩子的事情,上輩子已經被你過完了,你該多想想這輩子的事情才對。貢布說,哪有過完的說法,人的幾輩子就像一根藤上結的果,無論一個果和另一個果離得再遠,藤都連著。我不說話了,我知道我說不過貢布,我對我的上輩子一無所知,就像貢布說我是從上輩子睡過來的。后來我和貢布一個在村子中間長到十六歲,一個在村子東邊長到十六歲。那十六年里,我們都在忙著各自的成長,長在那十六年里是我們最重要的事,雖然我們不知道我們為什么要長,長大了到底要干什么。那十六年是我們為長而長的年齡。也許貢布在那十六年的成長中明白了什么,阿媽說過貢布是個聰明的娃。十六歲的貢布就再沒有在凹村長下去。一個黃昏,貢布爬上凹村東頭的木電線桿,從電線桿頂上飛了下去。看見貢布飛下去的人說,貢布仿佛并不是想往下飛,而是伸展著雙手往天上飛,人沒飛上去,伸展著雙手的貢布迅速掉下了懸崖。那個人最后說,那天的貢布,像極了一只落在黃昏里的鳥。
五
索朗離開凹村,大家都知道他離開了。索朗最先跟大家說自己要離開凹村,大家都把索朗的話當成是耳旁風,以為索朗只是生活過得太平靜,想在人前出出風頭。有人說,索朗老婆跑了就跑了,事情都過去年把了,日子要照樣過,你不會夜里床頭缺了女人就過不下去了吧?男人缺了女人是照樣能活下來的,你看咱們村的嘎拉,這輩子就沒有過一個女人,照樣活得有筋有骨的。索朗的女人是在去年春天離開凹村的。索朗的女人離開時,索朗正準備去放牛,牛和人剛走到圈門口,就遇見了女人的離開。女人背上背著一個鼓鼓的包,看見索朗和牛站在圈門口,也不躲閃,她說,她要走了,不再回來了。有人看見索朗和牛站在圈門口,愣愣地看著女人,索朗一句話沒說,牛也沒一聲哞哞聲,女人就從索朗和牛的面前眼鼓鼓地走了,一個轉身也沒有。等女人走遠了,看不見了,才發現索朗和牛一前一后地往達澤山上走。那天的索朗和一頭牛一樣沉默。后來,有人看見索朗每天該干嗎就干嗎,日子并沒有受到什么影響。索朗想離開凹村是在一年之后,他的想法全凹村人都知道。那段時間,他見人就說,給人說了不夠,還去給凹村的樹說,給風說,給動物說,給一條自己走了幾十年的小路說。樹沒因為索朗的話多搖擺兩下頭,風沒因為索朗的話多吹兩下,動物沒因為索朗的話多看他兩眼,路沒因為索朗的話少彎一下。索朗無論向什么說,都得不到回應,仿佛向什么說,都是自己和自己的對話。索朗不在乎這些,凹村是索朗生活了大半輩子的村子,他想讓這里的所有人和動物都知道他要離開,他每對什么說一次,都是一次告別,一次依戀。那段時間,人們經常看見索朗的嘴在動,上嘴皮和下嘴皮啪啪地響。還有一次,一個走夜路的人從鎮上回來,遠遠看見索朗坐在村口的大石堡上,對著凹村的一片青稞地說著告別的話。走夜路的人喊索朗,索朗轉過頭看了他一眼,沒答應,又把頭轉向凹村的那片青稞地,說著他想說的話。那人說,那天晚上天空掛著圓月,索朗看他的眼神帶著讓他捉摸不透的灰光。他從索朗身邊經過,索朗的身上有一股濃濃的夜的味道,索朗的頭上、肩膀上落著一層灰土,那時的索朗仿佛是從土里鉆出來的。就在人們都不在乎索朗要走時,一天夜里索朗一把火點燃了自己的房子,通紅的火苗在風的助推下,上下左右地亂舞在凹村的黑夜里,仿佛想點燃凹村的一片夜。人們忙著提水澆滅這場大火,索朗木木地站在忙碌的人群中,向房子說著告別的話。那一夜,索朗的家徹底毀了,人們終于明白平時把索朗說的要走的話當成是耳旁風是自己的錯,索朗是一個一心想走出凹村的人。有人說,索朗,家沒有了,你現在要到哪里去?索朗笑著說,我的另一個家早早就在我心里建成了。說著,他把手指向凹村的西坡,我想住在那里,守住另一個凹村。人們驚住了,雖然西坡離凹村近得只有一點五公里的距離,但是人們平時都不想往西坡看一眼,西坡是每個凹村人最終要去的地方,那里住著凹村祖祖輩輩離世的人。有人說,索朗,你要好好活,人一輩子就那么幾十年,這一輩子和下一輩子很近,你別著急去那里。有人說,索朗,如果你晚上寡得慌,嫌床冷,隔壁日央村有一個寡婦,模樣還是有幾分的,那寡婦單著身子好多年,一直托人幫尋新人家,但人的命誰說了都不算,這么多年她還是把自己空在那里。說不定她的空,就是等著像你這樣的人去填。你和她干柴烈火的,很快就能暖起來,只要你愿意,我哪天就幫你說她去。有人還說,索朗,房子沒有了不要緊,村子里多的是勁兒多到用不出去的年輕人,讓他們來幫忙,要不了一個月,一座房子就建起來了……人們對索朗說了很多話,凹村人第一次對索朗說這么多掏心掏肺的話。索朗從人群里站起來,一句話沒說,扛著提前準備好的被褥和糧食,手里提著幾樣做飯的家什朝西坡走去,人們看見索朗的身影穿過凹村的土路,繞過西坡那棵長了上百年的白楊樹,越來越薄的身影漸漸消失在西坡的一片荒蕪里。從此,索朗再沒回過凹村,凹村里少了一個叫索朗的人,西坡的荒蕪里多了一個守墓人,有人每天看見一縷青煙從西坡的荒蕪中緩緩升起,仿佛那里活著另外一群生機勃勃的凹村人。
六
如果真是他,那他已經在凹村消失了好多年。說這句話的時候,說話的人的眼神空空地望著天,仿佛藍藍的天能填補這些人眼神中的空一樣。人們平時很少用這種眼神看其他的事物。平日里,人們眼睛裝的東西不是能給他們帶來糧食的地,就是和他們相處最多的人,人們對地和人有用不完的眼神,從來不吝嗇把自己的眼神用在地和人的身上。人們用一輩子眼神看著地和人,眼神跟磨了的針尖一樣想穿透對方,進入對方的心,可惜看了一輩子又一輩子,到臨終都沒有看透一片地和一些人。記得大前年村子里的大旺堆死的時候,躺在藏床上告訴兒子,自己這輩子沒什么后悔的事情,唯一覺得不甘心的是沒有把一些人看透。大旺堆說,人別看只有一層薄皮裹著身子,心卻又大又雜,看不見底。大旺堆讓兒子以后少看人,多看腳下的河,遠處的山,一條河和一座山變的機會少,要多信賴這些變得少的東西。兒子臉上掛著兩行淚,不答應也不點頭。大旺堆難過,把頭側向一面黑墻,不看兒子,接著緩慢地說,我知道你現在聽不進我說的話,我也不怪你,你還沒長到我這把老歲數,沒活過我比你多活的這幾十年,沒吃過我比你多吃的這幾十年的苦,有些事情你現在還想不明白、看不透,是我太急了,這一急讓我忘了人是需要在日子里磨自己的,外人再說都是外人說的話,外人再急都是外人的急,即使我是你的阿爸也改變不了你什么,一個人一輩子的路是自己走出來的,最后把自己變成什么樣子,那是一個人的造化。說到這里,大旺堆不說話了,兒子以為阿爸在看一堵黑墻,沒去管他。大旺堆臨近要死的那段日子,總喜歡把一些話說到一半就停了,他死死地盯著一個地方看,仿佛那個地方是自己這輩子都沒有看夠的地方。這次大旺堆再也沒有把頭側回來,說自己下一次繼續想說的一半話,看自己下一次沒有看夠的一個地方。大旺堆是盯著一堵黑墻死的,等兒子把大旺堆的頭轉過來時,大旺堆僵硬的臉上鋪著一臉的失望。大旺堆失望的不止是自己的兒子沒把他的話聽進去,大旺堆還失望活了一輩子的自己沒能力看透一些人。大旺堆的話沒引起兒子的注意,也沒引起凹村其他人的重視,人們還是不厭其煩地盯著地和人看,覺得只有把自己的眼神用在這些上面,才是有意義的,不浪費的。人們只有說到他的時候,才舍得把自己的眼睛騰出來久久地望向頭上的一片天空。天除了一望無際的空,什么也沒有,那時人的眼珠里也裝著一望無際的空,什么也沒有。有人說,他走出凹村的時候是騎著他家的黑馬海子走的,海子不想走出凹村,走幾步停幾步,頭不斷地往凹村看。他騎在海子身上,用自己的黑背對著凹村,一個回頭也沒有。快到村口,海子不走了,在村口叫,海子一叫,凹村的馬都叫起來。馬從來不低著頭叫,馬似乎特別怕自己的叫聲落在地上被埋了。馬的叫聲怕地,馬可能知道自己一直踩在腳下的地的一些秘密。那天凹村幾百匹馬的叫聲扭在一起直直地沖向天,仿佛要把地上的一件事情捅到天上去。人們那天似乎看見天在動,人們是第一次看見罩了自己很多年的天在動。人們說,天在動,那是天知道了地上的事情。人們怕了,每家每戶的人對著天念誦著經文,誦經聲是附著幾百匹馬的叫聲一起升上天的。那天,凹村的馬對著天叫了多久,人們對著一片天誦經就誦了多久。最后,馬的叫聲是稀稀拉拉減下來的,誦經聲也是稀稀拉拉減下來的。那天,人們的頭上、身上都有被從天上落下來的馬叫聲砸中的感覺,砸中的瞬間,頭腦里也覺得自己像一匹馬,想奔跑,想跟馬一樣嘶鳴。人們說,確實也有幾個凹村的人在那天伸著長脖子望著天像馬一樣嘶鳴,那嘶鳴聲穿插在一群馬的聲音中,攪亂了一群馬的叫。只是人們后來追問,那幾個人怎么也不承認自己對著天叫出的那幾聲,他們想隱瞞。追問不出結果,也不想追問了,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后來有人發現,自從那之后,凹村的夜里經常會有幾聲不倫不類的馬叫聲飄在凹村的天上,連自家馬圈里的馬聽著都別扭,急忙羞著一張馬臉把頭深深地埋進自己的身體里。這些都是后話了。那天他的馬站在凹村的村口不想走出凹村,他騎在馬背上駕駕地喊,他再喊馬也不走,馬踏著凹村的土路,一個勁兒地沖著天上叫。那天海子的叫聲混合在凹村幾百匹馬的叫聲里,被頂到最前面,直沖凹村頂上的那片天。他在馬背上急,可再急也沒回頭往凹村方向看一眼。后來,有人看見他把身子俯在海子身上,一遍一遍地撫摸海子,一遍一遍地對著海子的耳朵說著話。海子先是不理,后來慢慢把伸向天空的頭低了下來,叫聲也沒有了。馬的叫聲只朝著一片天。凹村幾百匹馬的叫聲是在海子的叫聲停止之后,一層層從天上稀稀拉拉減下來的。村子里的馬靜靜地站在原地,蹭著身子,豎著耳朵聽海子的聲音,它們想的是如果海子再朝天叫,它們也跟著前面一樣一起叫起來,它們還會把海子的叫聲推到所有聲音的最頂上,讓海子的聲音離天最近,海子想向天表達的東西也離天最近。海子想向天表達的東西也是那天所有馬想向天表達的東西。可海子后來沒有朝天嘶鳴了,它在村口又頓了很久,最后一個縱身朝著凹村出村的小路飛奔出去,一會兒就不見了蹤影。有人說,當時海子的那個縱身,果斷、敏捷,很像一個下定決心的人,赴死而去。四十年之后的冬天,天空飄著毛毛雪,每家每戶的地爐里都架起了青岡柴,那時候的人們越來越怕一個冬天的來臨。上點歲數的人說,一到冬天晚上睡覺,自己經常聽見一種哧哧的聲音,最先認為那種聲音是夢里帶出來的,人老了,夢多得整個晚上都睡不好覺。上點歲數的人經常從一場夢里醒過來,黑黑地盯著屋里的暗看,看久了,仿佛暗并不是暗,一場場夢里的情景在暗里重新生長起來,分不清楚自己是在一場夢里,還是已經回到了現實中。那種聲音是在夢與現實中一次次響給自己聽的。后來,用手揪自己的手背,揪自己的腳,痛了就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在一場夢里了。有了這種辨別,人們說很多次那聲音響的時候自己是在現實里,他們說在一場夢里倒是好事,夢里發生什么都是正常的。但是這種聲音恰恰不在夢里。后來,他們在暗里到處找這種聲音,最后發現那聲音離自己很近,近得只能自己聽見。他們重新躺在一片暗里,靜靜地聽,最后終于聽見那聲音是從自己的身體里傳出來的,那聲音響一次,身體里的骨頭就麻酥酥一次,像是一只蚯蚓在骨頭里爬。人們說,過一個冬天,那聲音就比以前多響幾次,以前不覺得痛,現在那聲音在暗里響一次,骨頭就痛一次,那痛法感覺自己的骨頭在暗里裂。人們是越來越怕冬天了。冬天來之前,就早早開始準備青岡柴火,一到冬天,沒有要緊的事情,人都不想把自己的頭探出窗外,讓一個冬天的寒冷浸進骨頭里。娃就不一樣了,娃的骨頭還沒有長好,他們不懂大人的骨頭在冬天的痛。一到冬天,娃就往外面跑,大人的聲音喊不住娃,娃是在一個個冬天里跑大的人。人們經常看見一個娃在冬天里跑一天回來,滿頭大汗,全身散著熱氣,邊擦娃身上的汗,邊覺得這娃和早上從家里跑出去的娃有點不一樣了。人們也說不出來那一點點不一樣的到底是什么,只是在一堆青岡火面前一再感嘆,娃總歸是娃,娃永遠不懂有些命里的痛。那個冬天,是娃先發現了一個人在大雪里往凹村走。娃想,這個人不是凹村的,凹村的大人在冬天里都坐在一堆堆青岡火前,烤自己的骨頭。娃往家里跑,把自己在雪地里看見一個人的事情告訴了家里人。家里人先是不想挪動自己的身子往雪地里走,但又怕娃說的是真話,這樣的冬天一個人往凹村里趕,身上的寒氣足以讓一個人的骨頭裂開。他們想看看是怎樣的一個人會在這樣的一個冬天往凹村趕。家里人走出家門,第一次在飄著大雪的小路上等一個來凹村的人。家里人看見那人走幾步,停幾步,停下的那人一直往凹村看。家里人哆嗦著身子想那人在雪里看什么。雪里的凹村除了大片大片的白,什么也沒有。家里人急急地站在雪里等,在等的間隙偶爾聽見一兩聲哧哧聲。家里人四處看,不知道這種聲音是響在自己的身體里還是響在那個人的身體里。不過,不管響在誰的身體里,家里人都明白了那是一個人骨頭在裂的聲音。雪地里的家里人離那人越來越近,最后在焦急地等待中,那人終于來到家里人的面前。他摘下頭頂落著厚雪的帽子,抖了抖,第一句話問的就是,這里是不是凹村?家里人說,是。那人兩行淚馬上就下來了。家里人看見那兩行淚下來之后,立馬在他臉上凍成兩豎透明的冰柱。他說他以為自己又迷路了,這些年他一直在迷路,如果這次再找不到回凹村的路,他真想死了。家里人看著他,問他找凹村的誰。他愣了愣,說,找一個過去的自己。那人說出的話,像是被很多個冬天的寒冷凍過的話,到處都是傷。家里人聽不懂他說的話,他也沒怎么想讓別人聽懂他的話。說完這話,他離開圍著他的人,朝凹村荒廢了四十年的一座老房子走去。人們發現,即使是厚雪蓋住了路,蓋住了房子,他對凹村的一切還是那么熟悉。人們說,如果真是他,他已經在凹村消失了四十年,那四十年的消失,是永遠的消失,再在人心里補,也補不回來。
七
第七種消失,我想說的是我們隨時都在消失。說一句話的時候我們在消失,跨一個步子的時候我們在消失,抬一次頭的時候我們在消失,打一個噴嚏的時候我們在消失,眨一下眼睛的時候我們在消失。只要我們活著,我們就在這個世界上無時無刻地消失著。我們不愿承認自己的消失,總是對這個世界充滿著無限的貪婪和留戀,永遠一副沒有活夠的樣子待在這個世界上,覬覦著這個世界上的很多東西,仿佛要和這些被覬覦著的東西待一輩子,直到最后實在待不下去的那天才肯撒手。其實,這個世界上的很多東西都不會和人待到一輩子。很多東西在變,有些變是我們能看見的變,有些變是我們看不見的變。有些變離我們很近,近到長在我們的身體里,它們變的時候我們能聽見它們的聲音,那聲音弱弱地隔著我們,仿佛它們離我們很遠,這種遠讓我們錯誤地認為那些東西變與不變都和我們沒有多大關系,我們只有在很久以后才發現那變之后的結果。有些變雖然離我們很遠,我們卻一下就能感知到,我們把這種變告訴家人,告訴自己親近的人,不過告訴就告訴了,我們只是在為告訴而告訴,不為別的什么。我們很多時候都在裝傻,經常對別人撒謊,對自己撒謊,編織美麗的謊言騙別人也騙自己。我們明明早早明白死了什么也帶不走,人來世上就是為走一遭而來,我們還是想在活的時候,用力地為自己爭取些什么。我們是為活而活著的人。活著就要喘氣,活著就要吃飯睡覺,活著仿佛就是來這個世界上索要某些東西的,即使知道索要的東西最后一樣也帶不走,即使這些帶不走的東西最終的命運將賦予一份我們殘留給它們的不負責任,在活著的時候我們還是想擁有。只要活著,我們就把活著當成了一個人的頭等大事。在凹村,我看見過很多活得很用力的人,他們大口喘氣、大口吃飯、大聲說話,走到凹村的哪條土路上,哪條土路就被這些人踏出一個小坑,他們說這個坑是自己故意留下的,他們要讓一條土路記住村子里有一個每天給自己身上踏出小坑的人。他們一年四季在凹村的荒坡上開墾,土地里的糧食仿佛永遠也不夠吃。他們把鋤頭舉得高高的,彎刀揮得高高的,哪怕離他們很遠都能聽見一把鋤頭挖向一塊荒地、一把彎刀砍向茂密荊棘的聲音,他們很享受這種用自己的大力氣在一片荒坡上發出的聲音,那聲音給他們再一次揮出去的鋤頭和彎刀增加了無限的力量,這種力量讓他們的心越來越大,越來越野。他們把一片荒坡開墾完了,又去開墾另外一片荒坡,開墾出來的生地他們第一年撒一麻袋青稞種,收回兩麻袋半的青稞,第二年撒兩麻袋的青稞種,只收回三麻袋的青稞。他們立馬覺得一塊地不再對自己忠心了,便扔下那塊地,繼續下大力氣去開墾一塊他們覺得會對自己忠心的荒地。過很多年,我看見那塊曾經被同一個人開墾過的荒地又被那個人重新開墾。他們已經活過了記不住自己開墾過同一塊地的歲數。他們在自家的羊圈旁今天修一截斷墻,明天修一截斷墻,他們每次從地里回來,都不會空手空腳回來,他們覺得自己的力氣還沒有在一塊地里用完,回來的時候,順手從地里挖半背簍黃土背回來,或在回來的路上順手撿幾個石頭背回來,背回來的黃土和石頭放在一個角落里將來用來修一堵土墻,他們說等哪年有大塊時間,他們會把這些斷墻好好連成一堵完整的好墻,在里面新養幾十只羊,過幾年,又產幾十只羊,這樣一年一年下去,自己就會有數不清數目的羊了。我見過一個一輩子帶勁兒活著的人的死。那個人死的那天,他活在世上的大力氣還沒有用完,他的死不像一場死,而像一個人拼命想活過來。他說,他在雅拉山后面發現了一塊石頭,上面有個人像,只要他閉眼,石頭上的人就會開口和他說話。他說,他本來是想把那塊石頭帶下山的,可那塊石頭上的人像說,讓他第二次上山再帶自己下山,說自己和雅拉山生活了一輩子,自己一下舍不得離開。他理解石頭上的人像說的話,他說如果讓自己一下離開凹村去一個陌生的地方,他也不習慣。他說,哪天有空就去取那塊石頭,讓大家長長見識。他說,雖然自己七十歲了,但身體里還有一股勁兒憋著,這股勁兒天天在身體里喊自己的名字,想讓他放它們出來,它們說如果他再不放它們出來,它們就會在他身體的某個地方把它們用完。他無奈地告訴那股藏在身體里的勁兒,說,不是他不想放它們出來,他是想省著用它們,等哪天他把地里的事情干完了,心放寬了,他還想用它們修兩座房子,一座拿來晚上住,另一座拿來白天住。晚上住的房子做晚上的夢,白天住的房子做白天的夢,兩座房子的夢連起來,就像兩個不同的人把兩種人生連起來,他活了一輩子就相當于活了兩個人的一輩子,劃算得很。他說,幸虧他這么給那股勁兒說了,才得到了安寧。不過他知道那股勁兒之所以能安靜下來,是它們信他,愿意在他的身體里等。他說,其實自己也在等自己說的那個時候。他說,自己還想去雅拉溝砍兩年的樹,他想用砍回來的大木頭建一座木橋,自己和一條從雪山上融化下來的河生活了一輩子,還沒有順順當當地從自己的房子直直地走到河對面,河經常在夢里笑話自己。自己在一條河的笑話中,生活了一輩子,覺得太窩囊。說到這里,他突然從床上爬起來,叫家人給他準備上山的斧頭和皮繩。他說,他馬上就要上山,馬上就要去砍幾段大木頭回來修一座橋。家人急忙攔住他,他焦急起來,用大力氣踢身旁的土墻,用手臂打攔他的家人。他大聲地叫罵一屋子的人,罵著罵著一股氣沒有上來就死了。他身體里僅剩的一點大力氣用在了他倒下去的那一個瞬間。我緩了好一陣子才相信他死了,我開始相信即使用大力氣活在這個世界上,也會有說消失就消失、說不見就不見的時候。我們隨時都在消失,比如就在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文字雖在,那個剛才還在堂而皇之講大力氣的人已經消失了。當然,文字也會消失,文字的消失是一種緩慢的消失,當沒有人再注意到它的時候,它就沮喪地、孤獨地、默默地讓自己消失在了無盡的空氣中。只是作為這些文字的主人,我希望我寫的文字能在這個世界上多存活一段時間,它們是我用大力氣留下的產物,我也想為它們在這世間爭取些什么,就像那些用力活在凹村的人,不斷地開墾土地,不斷地修一截一截的土墻……我們是為活而活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