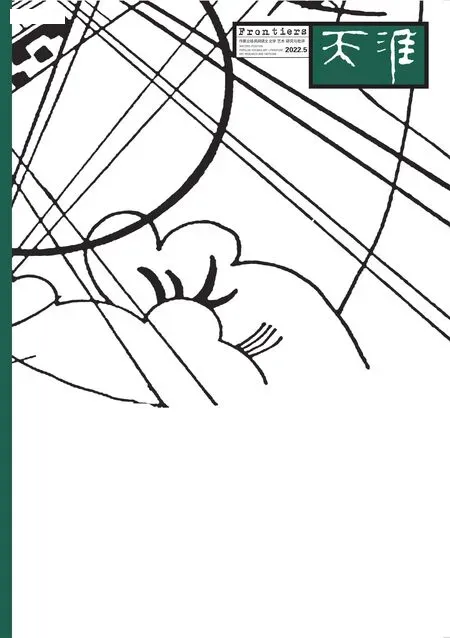人間遇雨
丁威
一
他身后是一間矮小到輕易碰到腦門的土坯廚屋,背對著太陽,一天到晚不見陽光,屋內黑麻麻的像夜色照進了濃稠的蜂蜜。屋里矮于地面,雖墊上了一層泥門檻,但一遇上大雨,雨水便漫灌著淌進廚屋,像澆灌水稻那樣把屋里浸潤透。廚屋又照不著陽光,便終年是滿屋子的潮氣。鍋門巢堆積著燒火的柴禾,有早已曬得干透散發著草木暖香的稻草,有堅硬耐燒的大豆秸稈,有長長的扎成一捆的芝麻秸稈,有巴掌大小一爬簍一爬簍撿回來的楊樹葉……它們在鍋門巢里挨不過一個夜晚,就被屋內的潮氣咬噬得渾身癱軟發霉了。一到燒火做飯,屋內便狼煙四起,柱狀的粗滾滾的濃煙從煙囪里鉆出去,多余的,又粗滾滾地從矮小的屋門擠出來。我媽在廚屋里高一聲低一聲地咳嗽,眼淚像捻動的珠子一樣滾落下來,一頓飯做好,我媽便像嚎啕大哭了一場,雙眼通紅如棗。
另有一間高于廚屋的土坯房子,既做堂屋又做臥房,一日三餐,待客閑談,日落而息,都在這一間土坯房子里。年歲久遠,屋根腳已有不少殘缺處,讓人覺得它仿佛是一個醉漢,根底飄忽,腳掌不穩,隨時都要傾倒下去,把自個兒狠狠地丟在地面上。也未見我爸去填補它,但一年年過去,雖一直像要倒塌,卻始終一年年看過去,依舊是老樣子,新出現的那幾塊殘缺,也無傷筋骨,屋子仍舊是茍延殘喘般站立著。那墻面上閃電一樣的裂痕,在日曬雨淋中,也新添了皺紋,卻如同老人被風霜割面,只要還能走動、做活,還能到荒地里捆一背的柴禾,把水挑進缸里,把米挖進鍋里,讓炊煙在煙囪上升起,吃下一碗飯,便繼續活下去。我們看那道道裂痕,就泰然處之,那是一間老房子歷經風霜的自然現象,打我落地在這間老房子里,在這鋪就散發著新鮮稻草暖融融的草木陽光氣味的新床上,后又用尿溺讓整張床成了整間屋子熏人窒息氣味的生產地,到我漸次知曉周遭事物,知曉時間在四季里寫下的種種,這座老房子就是這般面貌,我看它如同看自己的身體,我接受它也一樣如接受自己的身體。
但我爸是不同的,他知曉的事物要比我多得多,他不但知曉我們朱皋村,還知曉往流鎮,知曉固始縣……再過幾年,他將知曉更遙遠的北京、新疆,知曉天南海北。在他骨子里扎下最深根莖的是“人情世故”,是“樹活一張皮,人活一張臉”,是“爭氣”。
先前,逢一個閑散晴朗的天氣,他還挖土和泥拌上稻草,拿泥抹子把屋根腳的殘損處仔細地抹平加固,把墻上的裂縫用泥灰細細地填塞,直到圍著屋子前后轉悠一圈,四面的根腳再無破損處,四面的墻壁也都再無空隙處,他才滿意地點燃一根煙,像端詳一件藝術品那樣享受著自己的成就,仿佛是他把這間老房子從往昔的時光里拉回來了。雖然早已不復當年的青春容顏,但經他的手一打理,那些因時光的流逝而侵蝕的部分,又煥然一新。
晴好的日子里,從屋頂縫隙處透進來的金色太陽光斑,那明晃晃的影子隨著太陽的運動,也在屋子里四處走動,四季里還留下不同的行走軌跡。一只小貓時常把影子當作活物撲騰過去,撲了個空,又樂此不疲地繼續下去,想要捉住它,又不厭倦它似乎總在捉弄自己。
但到了有暴風雨的夜晚,一切都變了模樣了。那雨起先還小心翼翼地試探,很快便找到了房子的脆弱破綻處,幾滴雨水打了頭陣,察覺出了破綻處的不堪一擊,便把別處的雨水,甚至那些本該流下屋檐的雨水一同喊來,告訴它們此處有捷徑。雨水們聽從了召喚,一涌而來,很快的,那晴日里篩下生動陽光的地方,便在這樣的雨夜里,篩下苦澀的雨水來。噼里啪啦,一陣響過一陣,起先還似跳傘一般一個接著一個地墜落,很快,那些圍攏聚集過來的雨水,便結成了一股繩,拉下長長的雨線來,只在快接近地面處,才在地球的引力下扯斷了連綴著的雨線。坐在空中的老天爺玩興越來越大了,再不滿足于瓢潑雨水,他像是醉了酒一般的瘋狂,高興得拍手跺腳,一跺腳,天便多一處窟窿,天空塌陷,暴雨再無承載的依托,全世界所有的雨水,都洶涌而來,攢足了胸中的憋悶,長長地舒緩心中的塊壘,下吧,下吧,下吧,任誰也止不住天空狂歡的夜晚。
風和雨像竊賊一樣守在破損處,不待一聲哨響,便乘虛而入,那屋外暴風吹奏的嗚咽聲中,又在我家里平添了一種怪異的曲調。那是暴風吹過墻縫發出的獨特呼哨,像晴空中突然扯起的往高亢處攀升的鳴響,到了高處,便一跟頭跌落下來,但又一聲連著一聲,撕扯著夜晚的沉沉睡眠,撕扯著干澀的眼眶,像夜游的孤魂一般在狹小局促的一室之內逡巡,專找你的耳朵鉆進去。那一聲連著的一聲,像千足蟲的一條條顫動的腿腳,在你耳朵里翻江倒海。這樣暴風驟雨的夜晚,當然不止屋外的風吹雨淋聲,也不止風穿過墻縫的呼哨聲。這一間年久失修、縫補亦不堪大用的房子,它早已是千瘡百孔,早已是遍體鱗傷。
二
人間遇雨的夜晚,世間所有的雨水都到了我家,那駭人的風聲早已叫醒了所有人,雨水像是澆灌干涸焦渴的河床那樣,澆灌著我家屋里的土地。它一進來,便要四處橫流,想把巴掌大的屋子變成澤國,想把我們安臥的木床變做一艘在風雨飄搖中的小船,至于要將我們載向哪里,全看它的心思了。外面是濃墨般風雨飄搖的世界,大風吹過所有的樹,大雨淋濕所有的樹,沾染了雨水的樹葉在大風的鼓吹下,拍起了更加響亮清脆的巴掌,風嗚嗚叫,雨嘩嘩響,大風大雨下的樹葉癲狂一般拍著巴掌,像是冥冥中有神武之人降臨世間,需要這樣一場撼人心魄的暴風驟雨來迎接。
那細電線繞著墻頭和房梁扯上去的燈泡,懷著內心明亮的電流瑟瑟發抖。每天夜里,房梁上都有吱吱叫喚的老鼠逡巡,咯吱咯吱地啃咬著什么,甚至直接在房梁上嬉鬧、廝打,一個跟頭從房梁上跌落下來的情況也時常發生,“噗咕”一聲,一包肥碩的肉團從天而降,在地面上砸出一股沉悶柔軟的聲響。摔下房梁的老鼠只一個翻身,就吱叫著迅速消失了,房梁上的老鼠也吱叫著。像做錯事一樣消失了。但過不了多久,它們又順著房梁、墻角、桌椅攀爬往復,夜色給它們披上最好的偽裝,給它們打上強心針,仿佛這間破舊的房子到了夜晚就不再是我們的家了,而是成了這群老鼠的家,它們在夜色里如此招搖,毫無顧忌,像是我爸的許久不見的老朋友,風塵仆仆地從遠方趕來,不打招呼,無需禮道,只管帶著一身風塵推門而入,如入無人之境,拿起筷子就吃肉,端起杯子就喝酒。在夜色中,這群主人似的老鼠,拿所有可見的吃食填飽肚子,拿所有可啃的硬物磨牙齒,糧食口袋上縫綴著一塊又一塊破布,那都是它們偷盜啃咬的結果。它們小小的腸胃,任它們偷吃吧,也吃不窮盡我家的糧食,可最讓全家痛恨的,是它們磨牙齒的啃咬,新打就的座椅板凳,還泛著清新的油漆味,這是屬于新生事物的氣味,聞起來都讓人有一種新生的喜悅。這些新家當進了家門就被這群家伙循著氣味啃咬成東一塊西一塊的了,板凳腿上,椅子腳上,處處都是啃咬的缺口,新油漆下裸露出新木頭的傷口,看起來像是身體上的傷口那般觸目驚心。
我媽氣不打一處來,轉身出去往朱西街走,要去買一包老鼠藥,那種無色無味卻最烈最要命的毒鼠強。我媽的眼前晃動著那些新鮮木頭的傷口,可是她還沒走到朱西街,就停住了,她腦子里出現了一個前不久發生的熟悉的場景。
三
我媽走到半道,像光腳踩在烈日炙烤過的路面上那樣把腳步縮回來了,她想起村里曾有一對姐弟,把家里墻角灑落的毒鼠強當糖精吃下而喪命的場景,孩子的爸媽在地上嚎啕大哭的聲音還嗡嗡地吵著她的耳朵。
我媽孤零零地坐在屋子里,瞧著被老鼠啃壞的桌椅板凳,瞧著屋頂上被雨水浸得朽爛的屋笆,黃泥早已灰黑,雨水就是從那個地方肆意流淌進來的。瞧著四面墻壁上閃電一樣的裂縫,風從那里吹進來,夜深人靜的時候,鬼一樣吹響的呼哨聲,攪得她頭皮發麻,早上醒來,腦袋像一塊木頭,又沉又飄。鉆進廚屋,一頓飯下來,像打了一場硝煙彌漫的仗,油煙和落灰裹住了燈泡,即使深夜那燈泡也只像油盞一樣,發著暈黃微弱的光,擦了又擦,那光亮也未見增強多少。我媽坐在堂屋里,瞧著那殘破的桌子腿,抹起了眼淚。
沒有毒鼠強的家,四面漏風漏雨的家,暴風驟雨的夜晚,不請自來。黃昏來臨時,風把天上的流云迅疾地吹動,天空變了顏色,像一個黑沉的鍋蓋扣在頭頂,云層低得幾乎要垂落下來,把我們家那間矮小的房子壓迫得更顯矮小了。我媽早早地做了飯,吃完飯就躺下了,趁著暴風驟雨還沒到來,她能多睡一會,等到風吹雨落,再想睡踏實,那等于是異想天開了。我媽也早就備好了各樣的盆,那些慣常落雨的位置,她不需抬頭瞧著屋笆尋找,像熟悉自己的掌紋那樣,就在地上把盆擺好了,只等著雨落下來,雨水從屋頂上滲漏下來,一串串地滴落在盆里,地上的盆像道行深厚的術士那樣,捉住那些滴落的鬼魅雨水。各樣的盆里先是空空蕩蕩,那雨水滴落的聲音就是金屬、瓷器、塑料的聲音,空洞而喧響。待雨水漸漸聚集,又成了雨水和雨水的奏鳴,隨著盆里的雨水水位漸次升高,聲音也漸漸不同。夜色中,眼睛閉上了,耳朵卻張開了,耳聽也為實了,雨水落在洗菜的鋁盆里,聲音清脆,余音縈繞;落在洗臉的瓷盆里,聲音更脆,像攔腰折斷一根剛剛摘下來的新鮮黃瓜;落在洗腳的塑料盆里,聲音沉悶,像一灘爛泥遠遠地砸在墻上;落在洗衣的木盆里,聲音旋即消失,像是木頭有了吸力,那聲音被吞進海綿一樣的木盆里。我媽像一個下棋的圣手,每一枚棋子都清清楚楚地落在心里,那盆擺放的位置,和各處雨水滲漏的速率有關。最大的洗衣木盆放在滲漏最嚴重的地方,依次是洗腳的塑料盆、洗臉的瓷盆、洗菜的鋁盆,甚至那些盛菜的盆也來補位。屋外風急雨驟,屋內的滴漏之聲連綿不絕,隨著雨勢漸大,滴漏的雨水像是鼓槌敲擊著鼓面那般,鼓手敲擊到了高潮處,那起落的鼓槌沒有一絲松懈,一下趕著一下,將鼓聲敲成了一張密不透風的簾子,再敏銳的耳朵也聽不出那滴漏的縫隙之處了。
盆里的雨水漸多,由先前的生硬之聲變得綿軟黏稠了,噗咕噗咕,都是雨水咬合雨水的聲音,卻又因盆里雨水的水位高低而各有不同。木盆大,滲漏得快,半天只覆蓋住了盆底;菜盆小,滲漏得慢,只不多會,就將要滿溢了。我媽在黑暗中,眼睛全然瞧不見,耳朵卻靈得很。她也不敢拉亮燈泡,那些在房梁上廝打的老鼠們,不曉得哪一只黑悶了心,把尖利的牙齒磨到電線上了,雖沒有咬斷電線,可也許皮子已經咬破了,晴天還好,這樣滲漏雨水的雨天,不曉得破皮處有無浸到雨水,一拉燈繩,漏電也是可能的。所以逢上暴風雨之夜,拉亮電燈是我家的忌諱,耳聞目睹過不少被電殺死的人。電,這樣一種無影無形的東西,竟能像人捏一只螞蟻那樣,輕易殺死一個人,不留半點痕跡,這太過可怖,誰也不敢去冒險。在這樣的家里,我媽早就練就了屬于黑夜的眼睛和耳朵,任屋內漆黑如鴉,瞧不見一絲光亮,卻也不需要一絲光亮,兩只腳準確地在黑暗中找到兩只拖鞋,兩只耳朵又準確找到那個快要滿溢的菜盆,一手捉過去,像抓住菜板上已經拔干凈毛的雞,穩穩當當地抓在手里。她將菜盆里的水準確地倒進洗衣的大木盆里,再準確地將菜盆放回原處,動作熟練迅速,沒有絲毫拖泥帶水,待她又躺到床上時,那個又重又空蕩的菜盆的響聲再次變得脆硬起來。就這樣,在這個漫長夜晚的暴風雨中,我媽時不時地起身,抓起那些已經盛滿水的盆,將雨水倒入大木盆里。雨水就是時間的滴漏,有時大,有時小,有時快,有時慢。我媽在這起身的間隙里,還能閉上眼,稍稍睡會兒,那迷頓的瞬間,也并不妨礙她隨時起身,把那將要滿溢的盆倒空。如此這般,漫漫長夜就在傾倒雨水中過去了。
四
隨著夜色的濃稠漸漸化開,暴風一夜的嘯叫聲漸漸止息了,急驟的雨水敲打屋瓦的聲音,也漸漸止息了。遠遠的,公雞開始鳴叫,此起彼落,一聲聲的雞鳴縫綴著被暴風雨摧殘著的破舊的村莊,仔細聽去,那雞鳴聲中也有一絲絲的顫抖,人都無一處遮風避雨的安適的家,更不要說一群雞了。多少人家徹夜不眠,在雞鳴聲中,睜開惺忪的睡眼,耳朵里吵了一整夜的雨水滴漏聲,讓他們的腦袋像一截被大水浮起的木頭,迷迷糊糊,漂蕩于大水中。
但太陽照常升起了,一夜的暴風雨之后的清晨,世界更顯清亮了。一座村莊被風雨摧殘,可村莊各處站立的樹木,各處生長的植物,各處茍且的雜草,卻比往日更加鮮活,更透出勃勃生機,雨水被輸送到樹木的頂梢,每一片葉子都喝得飽飽的,身體里充滿了水,讓一棵樹渾身滿溢的勁兒,仿佛要離地飛奔而去;每一片葉子上的積灰都被沖洗干凈,上面的雨水還未蒸騰干凈,陽光照上去,光彩奪目,遠遠望去,一棵大樹上布滿了陽光的碎金子。雨水累積著,又層層滴落,在清晨的陽光里,一棵樹繼續下著碎金子般的雨。
一棵經歷徹夜暴風驟雨的樹,在清晨醒來的時候,是靜默的,渾身的勁兒在枝干枝葉里竄動。樹不像一夜未眠的村人,它的靜默里竄動著生機,卻把渾身的力道按捺下去,沉潛下去,只是滋潤它的枝干、枝葉生長就好,只是滋潤它體內的年輪潛滋暗長就好,它沉默地接受搖撼它的暴風,曉得伴隨著暴風的便是暴雨,搖撼它筋骨的,也必將滋潤它,它坦然接受這搖撼與滋潤。陽光此刻透著蜜糖一樣的亮,是一汪蜜糖里點上了一盞燈,燈光和蜜光交相輝映,這樣的陽光潑灑向一棵靜默的樹。你無法不凝視一棵樹身上,它渾身靜默的葉子,葉子上靜默的雨水,把蜜一樣的光收納起來,那光也隨同雨水一道聚集,懸在葉尖上,如一盞小燈,點亮了每一片葉尖。若陡然跌落了,墜向另一片葉子,則像一場起義一般,一滴墜落的雨水的燈盞,召喚起了千百滴雨水的燈盞。這樣一棵陽光里靜默的樹,動與靜的和諧,構成了暴風雨之夜后最動人的清晨景象。
各處的莊稼和野草,被一夜風雨吹打得倒伏下去,可它們全然沒有失去精氣神,仿佛是常日的站立,需要這樣一場風雨來讓它們彎下腰,歇一個漫長黑夜,以倒伏的姿態,來向暴風雨致敬,向生養它的大地致敬。黎明來臨,太陽灑下萬道金光的偉與力,你看吧,不要多時,幾乎你一轉身,這一片莊稼和野草,就又都立起身了。
陽光遍灑,你用內心諦聽著千畝良田和萬畝野草,那是一聲聲酣暢的“啊”,讓它們回想起先前盼雨憶苦的日子。焦渴的身體疲軟地抓緊腳下的土地,日光強烈的正午,它們時常覺得,腳下的根須有一瞬間的松懈,仿佛攥緊太久的拳頭,再也無力為繼,渾身散了架,整株身體像被烈日抽走了游魂,根須走了那么漆黑那么遙遠的路,尋得的水不解燃眉之急,根須泄了氣,周身也便跟著泄了氣。你躺在夏日的屋檐或大槐樹下,瞇縫著焦渴但難捱的睡眼,望向遠處的植物,無一不是蔫頭耷腦,連遠遠響徹的蟬鳴也顯出嗓子眼里的焦躁了,柳樹汁液也吸不出更多的甘甜了。
一切莊稼和野草,一切往上伸展腰肢的樹木,都把一棵身子化成鼻腔,嗅聞著空氣中的潮氣,希望從那潮氣的蒸騰中嗅聞出雨意來,雨意的觸角小心翼翼,在烈日的眼色里,潛滋暗長。
五
村莊里那棵最高大的國槐,當然是最先嗅聞到雨意的;家里最先嗅聞到雨意的,是我的爺爺。雨意最早像空氣中飄忽不定的游絲,只有對農事最敏銳的眼睛和嗅覺,才能察覺。
我爺爺說,怕是要下雨了,要下大雨了,莊稼都等得發焦了。
我爺爺吩咐家人,把晾曬的糧食收好,把漏雨的屋子補好,把曬干的衣服疊好,別讓一場雨壞了事兒,他慌得不成樣子,沒個人形。吩咐完,他就扛起一把鐵鍬下地去了,雨當然會來,嗅聞著空氣中若有若無的雨意,我爺爺曉得這必定是一場了不起的雨,恐怕要下一整夜。他掐算著指頭,已經月余未曾有點滴雨水落下了,人、土地、莊稼、一切活物都是焦干的,風一吹,都是在空洞洞地響。只有一回,瞧著天黑得穹頂貼到地面,直通通地壓在人的頭頂上,村里人都像雨前螞蟻似的忙碌著,唯有我爺爺站立不動,似成竹在胸,又似無動于衷。任誰都覺得雨定是要下來了,云壓得這樣低,天黑濃得似一杯糖水,濃稠得再攪拌也化不開,雨不落下,云自個兒都承受不住,村里人瞧著自家的莊稼地,都欣喜地拍起了巴掌,為老天爺的開眼喝彩。
我爺爺還是站在開闊的場院里,毫無動靜,只把一根又一根煙點燃了,不斷地抽。我爺爺又點燃了一根煙,并不抽它,而是把它平直地遙指蒼天,那煙氣從煙頭一生出來,就仿佛吐絲的蠶蛹,一刻不停地往外抽絲,那絲只往上升騰的一小截,就又箭矢一樣地平飄過去了,一根煙,不到一分鐘的時間,就被風抽完了,像一只吐盡了絲的蠶,干癟下去,瞬間蒼老。我爺爺把煙蒂丟到地上,右腳踩上去,細細地碾幾下。我爺爺把一口濃痰射到遠遠的地上,抖抖披掛在身上的衣裳,轉身進了堂屋,不一會兒,就掇條凳子坐在了屋檐下,手里抱著一個蓋著蓋的大搪瓷缸子,里頭泡了苦澀大葉子的釅茶,喝一口比喝藥也不差幾分,我爺爺倒喝得怡然,一邊抽煙,一邊喝茶,有無限的享受在里面。
此刻,我爺爺就端坐在屋檐下,瞧著場院里忙碌的人,瞧著雞鴨涌進院子,扯著嗓子叫;瞧著牛被拴回牛棚,臥在稻草鋪就的地上,瞇縫著眼睛反芻;瞧著風把墻角花池里的月季、梔子吹刮得彎折到一邊,幾乎要傾倒下去,掛在門楣上的去年的粽葉,像砂紙一樣摩擦著墻面;風一個勁地吹,萬物都在風的吹動下,彎折下來,傾倒下來,聲響碰撞著聲響,鐵器的聲響,木器的聲響,鐵鍬摔倒磕碰在磚地上。這會子,各人忙各人的,目光被引過去了,卻并不過去把鐵鍬扶起來,倒下去就倒下去,被攥在手里干活累,被豎立在墻根站直了也累,索性就讓它躺下去吧,也算歇息歇息。我爺爺瞧著開闊的院落,村人收拾完了東西,有的回到屋里,有的立在屋檐下,嬸子們回到廚屋去了,天還壓得那么低,黑洞洞的廚屋里一切已經皆不可見,卻沒人拉亮電燈。離著晚飯時間還遠,蒸饃的面團醒在面盆里,擇菜不要光,手指熟悉它們,黑暗里照樣一根根擇得干凈。雞鴨在吃食,牛在反芻,月季、梔子在傾倒,四輪車靜靜爬著,車廂里空蕩蕩的,只有細小沉默的鐵銹在緩緩生長,大風奈何不得它一分,細粉似的鐵銹卻有著宏大的野心。方才忙碌的家人,此刻都各自做各自的事了。
我爺爺也不言語,只一根根地抽煙,一口口喝下苦澀的釅茶,把大風一遍遍地看過,也把大風吹過的物件一遍遍看過。爺爺端端坐著,瞧著家人為暴雨來臨做的準備,那些龐大的物件,在風中巋然不動,就像此刻神態淡定的爺爺。那些細小的事物,在風中簌簌抖動著,更加細小的事物,則全部在空中化成風的形狀。落下枝頭的葉子,隨著風吹旋作一團,直到被風吹旋到角落里才安定下來,時而還抽搐般地抖動一下。搭在屋棚或者菜籽堆上的雨布,被風鼓脹起來,根腳卻被幾塊沉重的石頭拽住了,風奈何不得石頭,就只管悶頭往雨布里扎,把雨布鼓脹得像要離地飛升。塑料袋還很少的年代,瞧著風中飛起一朵紅色或者白色的塑料袋云朵時,孩子們是最興奮的,追著塑料袋,瞧著它插上翅膀一般高高低低地飛翔著,似乎要俯沖下來,被孩子們捉住,卻又一個筋斗,直直地翻騰上去,孩子們再蹦跳,也觸手不及。那風似乎給了塑料袋眼睛,它們一挨近樹杈,幾乎被樹杈伸手抓住,卻又像精靈似的輕巧地兜轉開去。孩子們追著塑料袋,瞧著這朵紅色或者白色的云朵,像電視中的章魚那般,變化出不同的形狀,距離也時遠時近。但那大風跟孩子們玩了不多會,就厭倦了,塑料袋飄飄蕩蕩地朝著山坎飛去了,輕松地越過山坎里最高的那棵國槐樹,一頭扎進山坎那邊那一片傲然挺立的楊樹林里了,扎進去又掙出來,遠遠地朝著淮河飄過去,朝著對岸的外省飄過去,那里有廣闊的平原和一望無際的菜地。它可以盡情飛翔了,再不必擔心有哪一棵大樹給它一座囚牢,在那座囚牢里日曬雨淋直到朽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