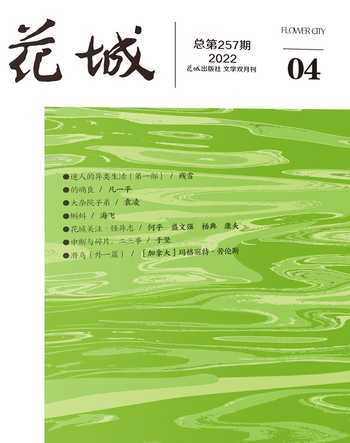無限集(十二首)
谷禾
無限(01)
光影變幻,穿透鋪展、聚散、游蕩的浮云,
從高處繪出虎背的斑紋,那刻上
我們臉頰和身體的,也落向遠山近水——
有一剎那,所有屋頂和墳墓一起從大地上消失了
無限(12)
蟋蟀的叫聲,再次把你帶回
灰色童年。在無數個清晨,露水
的河流浸漫鐮刀,光芒沿刃口滑過
扎緊的草捆把你的瘦弱肩膀越壓越低
日落之后,暮色沿一片瓦楞漫開
你獨自坐在曠野上,被黑暗包圍
等待浩瀚星空升上頭頂,蟋蟀們
并無停頓下來的意思,叫聲
更加恣肆——沿著叫聲走去
你將抵達一片陌生的墓地。
仿佛神秘的引誘者,蟋蟀密集的
叫聲分明來自墳墓深處,你想
找到那秘密通道時,大野突然靜下來,
而后是長久的寂靜。你從記憶中
抬起頭來,去看那來路和去路
它已消失無蹤,唯一城燈火
交織著光芒,更多蟋蟀的叫聲,
從燈火深處隱隱傳來。
無限(18)
思想者坐在午后的街心公園,光影
落上他的鑄鐵之驅,還有斑駁的
銹跡、埃塵、鳥糞,但只要坐那兒,
他就不停止思想。他低首,眉頭緊鎖,
以手托腮,始終如一。他在想什么呢?
一個思想者,即使從地獄之門,漂泊
來到破舊街心公園,即使他是一個贗品,
也不改思想的形象——他到底在想
什么呢?而時辰已經來臨,從遠方
駛來的轟隆隆的鏟車,越來越近了。
無限(35)
死去的死去了,活著的人
塵埃遮臉,繼續走在赴死的途中。
這是被反復篡改的命,
這是一代代人的過往與白頭。
像一滴墨,從紙上洇開。
像枯柳迎風,斷枝奏出青銅的獅吼。
無限(39)
我在同一時辰遇見死者出殯嬰兒落草。
我遇見童年的你和晚年的你手挽著手,
摘下的落果回到樹上,花朵退向花蕾,
射出的子彈回歸槍膛,人類因此不再殺戮,
愁苦的烏云散開,老人臉上生出孩童的天真。
這樣哦,我就可以把走過的路再走一遍,
把愛過的塵世再愛一次——在遇見你之前。
無限(48)
每一個心懷鄉愁的人,他要返回的
并非度過童年的地方,而是童年本身,
他因此只能做永遠的流亡者。返鄉
是一種基本人權。內心的流亡
是另一種返鄉的方式。“詩人的天職在于返鄉。”
而對于詩人來說,母語是他的唯一故鄉。
“……走向異鄉的盡頭,世界的另一端。”
無限(50)
費爾南多·佩索阿一生用近百個不同的身份
寫作,其中有詩人、哲學家、批評家、牧羊人、
翻譯家、記者、心理學家、占星家、神父等,
他們各有師承、風格、觀念、完整的體系,
經常會面、寫信、討論和批評。他把自己
分成了無數碎片,撒在世界的各個角落,
讓后來者無從抵達,或者用截然不同的作品
建起了一座佩索阿城堡。沒人說得清佩索阿
究竟是誰,或者,這些真實存在的寫作者,
共同虛構了這個叫費爾南多·佩索阿的瘋子。
無限(51)
那些永恒的事物都在消逝——
村莊、墳丘、蟲鳴,荒草。
月亮沉在淤泥里,你喊出
自己的乳名,只有風在回響。
道路上走著新人。幾個老人
圍坐在場院里,平靜地談論
身后事,像談論晚餐吃什么。
無限(54)
我反對愛,無限寬囿的
我反對櫸樹,廢墟上的花
我反對光,為黑暗命名
我反對疾病,在死亡之前
我給予你:一個虛空的詞
像匕首,反復抽出我的肋骨
無限(61)
當望遠鏡成為一種普及之物,你透過它
看到的不再是血與火迸濺,成敗的秘密隧道
而是被放大的城市和原野,窗簾被焦距拉開
大地排闥而來,不同個體的生活成為庸常
作為自然事件,一片葉子飄落和一只蟲子墜地
同樣驚心動魄,隱匿的鳥巢在風中搖晃
麻雀的親昵隨樹枝一起暴露在鏡頭里,滿足了
你的窺伺欲望。遠山近水歷歷目前
被打開的另一個陌生世界,人在疾走,風在奔逐
老虎打盹,獅子念經禮佛,勤勞的蜜蜂
用語言之甜,創建了星空和教堂的建筑學
生和死的角力從不停歇,你看見了自然
那雙無所不在的手——它也操控著你
一步步陷入它設定的情境,而不能自拔
無限(65)
我們越來越多地談論衰老,衰老也在剝去我們身上的多余——生命誕生后附加的衣服、物欲、情欲,道路、風雨,以及越來越廣闊的活動空間,漸漸成為重負和累贅。衰老不動聲色,又不容置疑地,幫著我們扔掉,一點點回歸初始的赤裸狀態。它接著拿走我們的歡笑和啼哭,最后還拿走我們的皮肉和骨頭,讓靈魂無枝可依,成為看不見的“無”和無所在的“無”。現在,只剩下我們的談論,回響在談論者和衰老之間,空洞,又無依附之唇,如所有虛擬一樣,并不能減緩衰老的加速度,而且充滿了沮喪——我們卻沒有力量讓它停下來。
無限(77)
另一重現實:世界上也沒有完全相同的兩片樹皮,那些紋路和疤痕仿佛不同傷害的確證。但幾乎所有的樹,都有著一樣的孤獨——那朝向光照的一面。我相信突然飛起的鳥兒是另一種形式的葉子——它們從樹身的黑暗里汲取歌唱和飛行的泉水。
責任編輯 梁寶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