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探索“生前預囑”立法
張靜

7月5日,深圳遺囑庫一角
6月23日,深圳市第七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次會議表決通過了《深圳經濟特區醫療條例》修訂稿。該條例第七十八條在“臨終決定權”上做出規定,如病人遺囑要求“不要做無謂搶救”,醫院要尊重其意愿,讓病人平靜走完最后時光。
深圳由此成為全國第一個實現生前預囑立法的地區。
7月10日,深圳市生前預囑推廣協會召開第一屆第四次理事會議。會長李瑛組織理事討論了生前預囑在深圳立法后的落地實施。
李瑛表示,協會草擬了《深圳市生前預囑文本》,待完善后擬在成熟時機向社會發布,為2023年立法實施做準備。
“生前預囑寫入地方法規,對于不堪忍受有創搶救之苦的臨終患者是一個令人欣慰的消息,也為醫生依據生前預囑行醫提供了法律保護。”同濟大學法學院教授金澤剛說。
生前預囑立法,傳遞著自己生命自己做主的生命權價值導向。
什么是生前預囑
生前預囑是一份在患者本人清醒時自愿簽署的文件,通過這份文件簽署,患者可明確表達自己在生命末期希望使用何種醫療照護,包括是否使用生命支持系統,比如切開氣管、人工呼吸機、心臟電擊等積極的有創搶救,以及如何在臨終時盡量保持尊嚴。
“生前預囑絕不是放棄治療。”李瑛說。
據李瑛介紹,執行生前預囑文件,必須是在不可治愈的傷病末期,需要有嚴格的醫學準入標準,由2位或2位以上的專科醫生和安寧療護醫生,根據生存期預估表,認定無論采用什么樣的醫療措施,都不可挽回患者生命即將走向終點的結局,才能按照患者的愿望來進行安寧緩和醫療。
1976年8月,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議會通過了《自然死亡法案》,成為全世界第一個建立生前預囑相關法律并將其合法化的國家。1996年新加坡制定《預先醫療指示法令》,并于1997年7月實施。
目前,全球已有30個國家和地區允許在醫療護理過程中合法使用生前預囑以及功能相似的一系列文件。
生前預囑不同于安樂死,后者指通過注射藥物等措施幫助患者安詳地結束生命。對于是否承認安樂死,歷來為各國所爭論。目前僅荷蘭、日本、瑞士等國家或其部分地區將安樂死合法化,但也制定了嚴格的適用條件,規定不得濫用。
中華遺囑庫管委會主任陳凱對《瞭望東方周刊》表示,在臨終搶救的過程中,一系列搶救措施可能導致患者遭受更加嚴重的傷害和痛苦,使人失去尊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否繼續搶救,患者本人往往不能做主。預囑正式納入法規,患者就可以選擇做自己生命的掌控者。
陳凱認為,生前預囑不是一種積極求死的做法,而是一種以消極保守治療追求生命質量的做法,目的是提高生存質量,而非僅僅追求生命逝去時的尊嚴。
“生前預囑立法,傳遞著自己生命自己做主的生命權價值導向。從對于減輕家屬經濟負擔、節約社會醫療資源而言,也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金澤剛說,“深圳這次探索生前預囑立法,反映了社會文化、倫理道德和民眾權利義務觀念的發展變化,必將推動人們對生命的權利和意義的深入思考。”
率先嘗試
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下,病患家屬往往會選擇對處于生命末期的患者隱瞞病情,而患者也很少主動與醫護人員或者家屬談論死亡的話題。當生命終末期到來時,患者往往已不具備表達自己意愿的能力,只能由家屬做決定。
中南大學附屬湘雅醫院呼吸與重癥醫學科醫生江月(化名)表示,盡管在入院時,很多家屬都會簽字表示拒絕做有創血壓、中心靜脈置管、氣管插管等有創操作,但到了實際需要搶救時,患者家屬又會有所搖擺。
是否終止治療對家屬而言是巨大的心理壓力。“如果有生前預囑的存在,家屬和醫護人員事先就能了解患者的真實意愿,一定程度上減少或免除他們的道德責任,變為尊重患者的自主決定。”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人文學院副教授張迪說。
一旦生前預囑具有法律效力,就能最大化保護患者個人意愿。江蘇省老年病醫院血液腫瘤科主任樊衛飛介紹,南京多家醫院腫瘤科一直在推廣生前預囑,但患者想要簽署生前預囑,需要經過嚴格的專業評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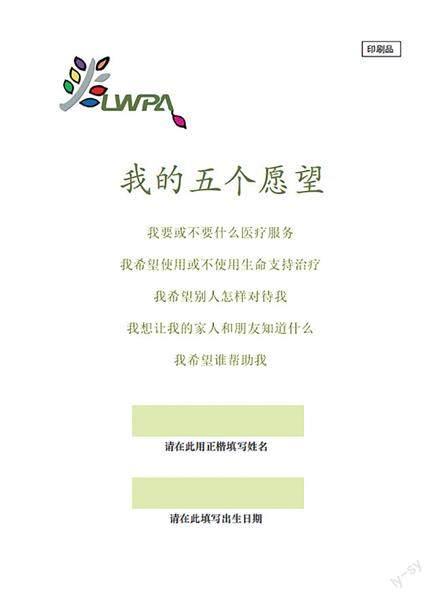
“生前預囑”示意圖( 圖片源自深圳市衛健委官網)

深圳市生前預囑推廣協會官網截圖
2021年1月,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在關于政協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關于推動安寧療護事業發展的提案》的提案答復函中表示,通過生前預囑等方式實施安寧療護,目前立法條件尚不成熟。接下來將進一步研究實施生前預囑和成立生前預囑注冊中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深圳成為第一個探索的城市。
2021年4月17日,深圳市生前預囑推廣協會揭牌成立,這是繼北京之后的第二家推廣生前預囑的社會團體。深圳市第二人民醫院老年科醫生李瑛擔任會長。
在深圳市衛健委安寧療護調研小組到深圳市第二人民醫院調研期間,李瑛提出建立深圳市生前預囑推廣協會,得到深圳市衛健委的肯定和支持。
有了深圳市衛健委做業務主管單位,審批一路綠燈。“協會正式成立之后,衛健委給我們提出的任務是,要朝著立法的方向推進,如果沒有立法,生前預囑簽署人的意愿就無法得到保障。”李瑛說。
2022年《深圳經濟特區醫療條例》修訂前,深圳衛健委組織了多次立法討論會,最后定稿由深圳市衛健委提交審批并順利通過。
李瑛說:“我們推廣生前預囑理念,就是為了宣傳安寧療護,讓大家都知道,到了生命末期也可以把生命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走得更有尊嚴。”
《深圳經濟特區醫療條例》修訂稿通過后,7月5日,第一份生前預囑公證書在廣東省深圳市深圳公證處出爐。當事人杜女士一早來到深圳公證處辦理生前預囑公證,提前約定了有關醫療救助的內容,在填寫了申請表,并進行了錄音、錄像等程序后,杜女士順利拿到生前預囑公證書。
仍需慎重
盡管深圳已成為全國第一個實現生前預囑立法的地區,但相關法律細則還沒有出臺,具體落地方面也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
陳凱認為,深圳雖然走在前列,但大范圍推廣還為時尚早。生前預囑涉及許多法律、醫學和倫理問題,在相關制度尚不成熟的背景下,需要慎重對待。“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生前預囑仍處于‘無支持、未禁止的狀態”。
陳凱表示,困難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對適用生前預囑狀況的判斷,是否達到了不必搶救的程度;二是家屬的態度。對于預囑的執行,條例只是要求醫療機構“尊重患者生前預囑的意思表示”,并沒有強制規定醫院或家屬必須執行或者不執行,在一定程度上,患者的預囑還是要依賴患者家屬和醫院共同配合才能實現。
目前,生前預囑在深圳推廣也存在一些阻礙。首先,國人對死亡的話題比較忌諱,如何讓民眾相對輕松地面對這個問題是推廣工作的重點;其次,公眾對生前預囑和安寧療護知曉率不高。
“在深圳市生前預囑推廣協會接待的咨詢者中,大多是40歲至60歲有相關需求的人。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對生前預囑表現出積極態度,而前來咨詢的高齡老人相對很少。”李瑛說。
國內目前還沒有供患者訂立生前預囑并進行公證的專業機構。一旦患者陷入昏迷,醫療機構難以判斷家屬提交的生前預囑是否具有合法性,是否代表患者本人意愿。因此,制度保障還要進一步完善,既要更好地保護患者本人的權益,也要降低醫療從業者面臨的風險。
陳凱認為,生前預囑的及時和準確傳遞,直接關系到其能否得以真正執行。“立法更加細化是有必要的,在當前的情況下,我們建議找第三方具備公信力的機構來訂立預囑并委托保管和傳遞預囑,這是較為穩妥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