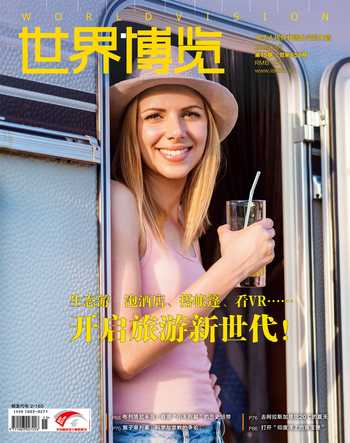讓溝通變得更“美”
邱瑞

溝通包括傳送者和接收者,傳送者進行編碼,接收者進行解碼。雙方在溝通的過程中互為傳送者和接收者,但是編碼和解碼的是兩個不同的程序系統,這使得溝通的過程會出現偏差—— 也就是交流誤解。
腓特烈二世是德國歷史上的一位皇帝,是歐洲開明專制和啟蒙運動的支持者,被后世尊稱為腓特烈大帝。這位皇帝在位期間為普魯士做了許多貢獻,由于他的各項開明的舉措,普魯士一躍成為歐洲的大國。根據歷史學家的描述,這位皇帝曾經做過一個有些殘忍的實驗。他為了了解嬰兒在沒有和人接觸之前會最先說出哪種語言,就找來幾個嬰兒,他讓保姆和護士喂養幾個嬰兒,但是卻不準這些人和嬰兒說話。最后的結果十分悲慘,他不僅沒有得到問題的答案,幾個嬰兒也都死亡了。這些不會說話的嬰兒,在缺乏與養育者溝通的情況下都失去了生命,這個實驗讓我們明白了人類溝通的重要性。
溝通首先是一種生理需求,溝通與生理健康之間有著必然的聯系。研究表明,缺乏人際溝通或者是不良的人際溝通會提高危害身體健康的風險。同時,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認為人最基本的需求是生理需求以及安全需求,而在這之上的需求就是社交需求,這無疑需要溝通來實現。在社交需求之上的自尊的需求、自我實現的需求等都離不開溝通。
我們真的會溝通嗎?
說起溝通,好像人人都會,但我們的溝通是否有效呢?溝通包括傳送者和接收者,傳送者進行編碼,接收者進行解碼,雙方在溝通的過程中互為傳送者和接收者。但是編碼和解碼的是兩個不同的程序系統,溝通的過程就會出現偏差——也就是交流誤解。
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做了一項研究,他們讓被試先和他們認識的人配對進行溝通,再和陌生人進行配對溝通。結果發現,和熟悉的人溝通的效率并不比和陌生人的效率高。我們總是高估自己對對方的了解,而且在我們和對方熟悉了之后,會產生一種類似于偏見的固有印象,這就會導致誤解的產生,溝通的效率可能就會隨之下降。不僅僅是聽話者會因為熟悉的對象而在理解時產生偏差,說話者也會由于認為對方很了解自己而在表達的時候省略很多內容。其實,我們以為的了解可能只是我們內心的偏見。
丹·格林伯格在《讓自己過上悲慘生活》一書中指出:“如果你真的想過上悲慘的生活,就去和他人做比較。”很多人際關系發展并不順利的人,總是生活在和他人的比較中。這種比較不僅僅存在于心理活動中,更容易體現在語言上。許多比較在溝通中出現的時候并不是顯性的,而是隱藏在語言背后的。類似下面的對話,想必大家都很熟悉。
邁克剛和一個朋友從電影院出來,兩個人開始聊剛剛看過的電影。從演員到劇情再到配樂,兩個人聊得正開心,邁克突然說:“這部電影畫面不太好看,韋斯·安德森對電影畫面的把控堪稱一絕。”朋友其實對電影導演并不是很了解,便問道:“韋斯·安德森是誰?”邁克突然睜大眼睛,驚恐地看著朋友,好像見到了外星人:“韋斯·安德森你都不知道?天啊!你沒看過《布達佩斯大飯店》嗎?”朋友的表情瞬間變了,聊天沒辦法再進行下去。
邁克驚訝的是什么呢?是朋友連這么著名的導演都不知道,邁克認為這應該是一個常識。然而我們深究這個對話背后的內容,其實能看出一些端倪。邁克的驚訝是在表達朋友是一個無知的人,是想要通過這樣的驚訝來表現自己了解朋友不了解的東西,從而在兩個人的交談中占據上風。也就是通過這樣的對話,邁克發起了和朋友的比較,他提出了一個對方并不是很了解的內容,并且在對方表達出自己不了解時發出了驚訝的反饋,這種驚訝其實包含著嘲笑的意味,邁克在這場比較中“勝出”。這樣的“勝出”是否有助于溝通,或者說是否有助于維持人際關系呢?在職場中又能否幫助你解決問題呢?答案是否定的。
再從另一個角度分析,邁克的這種比較和炫耀式的語言實際上是一種自我缺失的暴露。一個人內心不夠強大、內核不夠穩定的時候,會想要試圖通過一些外在的元素來增添自身價值。這其實是一種自我欺騙行為,是在虛榮心的驅使下渴望向別人表現出自己并不具備的氣質。其實這背后的道理很簡單,物理學教授不會炫耀自己知道什么是重力波,生物學家不會炫耀自己在研究水熊蟲,航空航天專家不會炫耀自己了解飛行動力裝置。當然,我們會聽到這些人向大眾科普自己的專業知識,但科普和炫耀的區別我們是能夠在語言中感受到的。邁克和朋友的對話,其實可以算是一次失敗的、不和諧的溝通。不僅邁克沒有在朋友那兒得到認可和佩服,朋友也沒有在邁克處獲取新的知識和信息,甚至因為這樣的對話,朋友心中對邁克的印象打了折扣。
評價性言語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們不僅在和朋友、同事之間溝通時會犯錯誤,在親密關系、親子關系之間的溝通中也會出現錯誤。所謂的錯誤并不是指道德意義上的對錯,而是那樣的溝通并不能幫助我們達到目的。
我們在和愛人或者孩子溝通的時候,經常會用到評價性的語言——“你為什么這么不尊重我”“我老公從來不關心我”“你怎么這么沒禮貌”,等等。我們說出這樣的評價性內容的時候實際上里面暗含著我們的內在需要,我們希望得到對方的尊重,希望老公能更關心自己,希望對方能表現得有禮貌。
我們使用這種語言的時候,是希望對方能夠接受批評,認識到自己的問題,并且做出讓步從而滿足自己的內在需要。我們作為說話人的時候,認為這樣的話語應該奏效,但是當我們轉換身份變成聽話人的時候,聽到對方說出這樣的話,就更不會按照對方的要求去做了。因為這樣的語言是一種居高臨下的判斷,是站在道德高點上對對方進行的譴責。
這時候受到譴責的一方,有可能會因為恐懼或者內疚而屈服進而去迎合對方,但是長此以往他們的內心會產生深深的厭惡,并且越來越不愿意滿足對方的需求。這種情況也不是只有溝通的一方受害,雙方會因為無效的溝通而同時對對方展開評價,形成惡性循環。這種評價式的溝通內容還帶有一些副詞的修飾,比如“從來”“從不”“總是”“只會”等,這些副詞不止是在描述事實,也是在發泄情緒。對方聽到這樣的詞后,也會覺得你在否定他的所有行為,溝通自然沒辦法進行了。
我們在溝通時會使用“雖然”“但是”“就算”這類的詞,這些詞在語言邏輯中是必要的,然而在與他人的溝通交流中,這些詞到底發揮著什么樣的作用呢?“你雖然腿疼,但是我也走了一天了,我也很累。”“就算我有錯,但是你做得就都對嗎?”“我知道你很難過,但是你也不能沖著我發脾氣吧!”我們在用這些詞的時候,其實目的都是在淡化對方的立場,強調自己的觀點。我們都明白換位思考的重要性,我們以為這樣的話都是已經在體諒對方了,實際上我們是在輕描淡寫地肯定對方,然后來個180度的大轉折。看似自己是在理解對方的前提下提出了觀點,實際上是把重點轉移到自己的立場上。這樣的溝通雙方都很委屈,一面認為對方不體諒自己,一面又覺得自己已經很努力地站在對方的角度考慮了。
提出建議和解決方案的意義
我們不僅僅在“表達”的時候會出現問題,有時候我們也不會“傾聽”。法國思想家西蒙娜·薇依說:“傾聽一個處于痛苦之中的人,不僅十分罕見,而且非常困難。那簡直是奇跡,那就是奇跡。有些人認為他們可以做到,實際上,絕大部分的人都還不具備這種能力。”我們經常會遇到別人的傾訴或者抱怨,作為傾聽者的我們總是想聽完事情的經過之后,給出一個自己的建議或者解決方案。
瑪麗有個結了婚的好朋友,好朋友經常會在婚姻出現問題的時候來向瑪麗抱怨。瑪麗每次聽朋友的抱怨,都會跟她說:“離婚吧!這個男人不適合你,他實在太壞了。這是原則問題,根本不可原諒。”朋友抱怨了一通之后,沒幾天又在社交媒體上秀恩愛。這讓瑪麗非常費解:好友明明那么生氣,為什么還是原諒了她的丈夫呢?
其實好友來抱怨,并不是希望瑪麗給她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案,這個時候好友想要的只是情緒上的共鳴,她渴望的就是有人傾聽。我們也經常會在別人生氣的時候說“別生氣了”,在別人難過的時候說“別難過了”,在別人郁悶的時候說“別郁悶了”。有時候我們給出建議或者解決方案是想要盡快結束這段對話,讓對方停止負面情緒的輸出。

馬歇爾·盧森堡博士和他的著作《非暴力溝通》。

“內省”的能力可以更好地在孩子早期溝通的過程中建立起來。
聽起來,我們好像一直以來都在用錯誤的方法溝通。人本主義心理學家、國際非暴力溝通中心創始人、全球首位非暴力溝通專家馬歇爾·盧森堡博士認為,提到暴力我們總是會想到肢體上的傷害,但是語言也會給他人帶來痛苦。他創造了一種非暴力溝通方式,不僅在人際關系的和諧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甚至還幫助解決了世界范圍內的爭端和沖突。他將自己的非暴力溝通方法和理論寫成了書,名為《非暴力溝通》。
書中教我們審視自己的語言,思考語言背后的內容,并且提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溝通方法。溝通時出現的很多問題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們不夠愛自己,不夠接納自己。我們因為覺得自己不夠完美、不夠優秀而想要去通過和別人的比較來獲得優越感,我們因為內心空虛所以要用強硬的語言來偽裝自己,我們不愿意承認自己的錯誤而想方設法地把問題歸結到別人身上。
想要做到非暴力溝通,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接納自己,學會自我寬恕。知道自己并不那么優秀,明白其實自己不需要那么優秀,同時接納那個并不優秀的自己。馬歇爾博士提出,非暴力溝通的4個要素就是觀察、感受、需要和請求。可以套用這樣的公式——“我觀察到了……我的感受是……是因為我想要……我希望你能……”非暴力溝通希望我們能表達感激和贊揚,哪怕是生活中的小事,哪怕是你習以為常的東西,感激和贊揚的力量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和別人建立良好的溝通關系。
良好溝通的道理可能我們都懂,仔細思考的話我們都能發掘出語言背后的東西,內省的能力也能讓我們發現我們表達的目的是什么。但是,理論經常走在實踐的前面,許多有道理的方法在事情發生的當下可能就會被我們拋到九霄云外,但這不能成為我們拒絕成長的理由。可能在表達的當下我們沒有多余的空間思考,但是在表達過后我們可以反思,可以想一想怎么說會更好,怎么說才能在不傷害到對方的前提下達到自己的目的。給溝通裝一面鏡子吧,去清洗和整理它,總有一天它會越來越美。
(責編:南名俊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