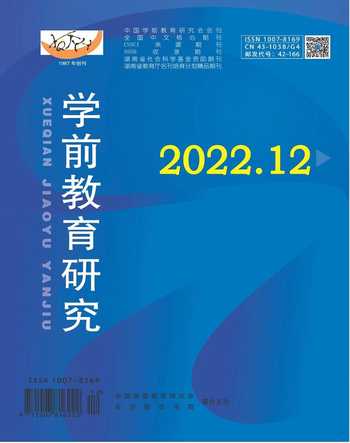以社區為教育實踐基地:家園社協同育人模式的創新之路
韓鳳梅
[摘 要] 幼兒園主動引領、家庭切實履責、社區積極協同是家庭、幼兒園、社區三者協同共育的基本定位。然而長期以來,幼兒園強調了與家庭合作,而沒有充分挖掘社區的教育功能。通過建立信任激勵、行動協同、資源共享、評估反饋的三方聯動機制,社區可以成為穩定的教育實踐基地,不僅為幼兒在園學習提供豐富的材料和信息,而且為家庭育兒提供直接支持與廣闊的教育空間。在此基礎上,家、園、社三方可以進一步共建共育課程,共同確定能夠持續激發幼兒探索興趣的活動主題,為幼兒提供多樣化的活動形式,促進幼兒主動學習與發展。
[關鍵詞] 協同育人;家園社合作;社區教育
幼兒園、家庭、社區三者共同構成了幼兒成長的微觀環境。它們各自蘊含著豐富的教育資源,承擔著相互補充且不可替代的教育功能。當前,幼兒園、家庭和社區的教育協同在認識上還處于單向協同發展階段,社區的參與和卷入程度低,主體關系尚未從合作走向協同。以上種種問題都影響了三者協同育人的效果。[1][2][3]在傳統的家園合作或者園社合作中,幼兒園一直處于主導地位,它通過自身的專業角色在合作中起著支配作用,因而與其他教育主體的合作也表現出單向性。支持學前兒童全面有效發展是全體社會的共同責任,應實現幼兒園教育的專業性、家庭教育的親密性、社區教育的滲透性三者的融合統一。
一、家園社協同育人新模式中的主體關系
幼兒園、家庭和社區協同育人的共同愿景是在發揮各自力量的基礎上為幼兒構建良好的發展環境,因而其合作模式的建構與創新就應該淡化傳統支配與被支配、主導與配合的二元思維所帶來的束縛,將對教育協同主體關系的認識從線性化推向扁平化。幼兒園、家庭和社區在建構幼兒教育共同體的過程中,一直未解決好主體分工不清,責任邊界模糊以及角色的缺位、越位或者錯位等問題。[4]將家園社協同育人的視點從幼兒園轉移到社區的過程中,要使新的機制更好地發揮作用,首先就必須解決好主體之間的關系問題。
在新的協同育人模式中,幼兒園、家庭和社區之間的主體關系應該從“各司其職,優勢互補;權責清晰,動態調整;園所引領,互為支撐”這三個方面入手,最大限度地調動不同主體的積極性,發揮各自的資源優勢。首先,幼兒園、家庭和社區在協同共育中應各司其職,優勢互補。在幼兒的成長過程中,不同的主體肩負著不同的教育職責,其所占有的教育資源和采取的教育模式都不相同,且相互之間不可替代。在全面發展幼兒這一核心目標的引領下,幼兒園、家庭和社區必須在明確各自職責的基礎上發揮自身的教育優勢,將不同主體之間的異質性轉化為功能上的互補,進而實現育人過程中的協同。其次,幼兒園、家庭和社區之間的協同育人應堅持權責平等,動態互補。不同的主體享有相應的兒童教育權利,但所能擔負的責任也是存在限度的,且在不同的場合中權責的發生也各有側重,但對幼兒的教育以其中某一方為主時,其他主體就應該扮演好積極配合的角色。最后,基于兒童教育的專業性特征,幼兒園、家庭和社區的教育協同應該建構起幼兒園主動引領、家庭切實履責、社區積極協同的三角支撐關系。[5]其中幼兒園要積極發揮專業引領和示范作用,將幼兒教育的科學理念、知識和方法擴散到其他群體當中,[6]要切實發揮專業自信和教育自信,以引導其他主體實現在幼兒教育價值上的共同理解和共同信念。
二、以社區教育實踐基地為依托建構家園社共育平臺
創新幼兒園、家庭和社區協同育人模式的重要突破口在于對社區進行賦能,通過社區教育實踐基地的建構來搭建協同育人的有效平臺。[7]以社區為中心的幼兒教育活動應著力解決以下問題:一是教育活動應該圍繞幼兒的學習與發展來展開,而不是著眼于對既有資源的有限利用或者形成教育特色;二是將對幼兒的協同教育轉化為穩定且有效的制度,而不是為滿足一方的教育需要而臨時尋求其他主體的支持;三是將社區中的觀摩活動轉變為深度學習,而不是停留于表面的熱鬧和形式的豐富。社區教育實踐基地正是瞄準上述問題而進行建構的,它在發揮幼兒園專業引領作用的基礎上,將幼兒教育的時空環境從幼兒園轉換到了社區,社區成了連接幼兒園和家庭的重要平臺。社區教育實踐基地的建構始于幼兒園對社區教育資源的評估與整合,經由與優質教育資源所在機構建立穩定的合作關系,最終為豐富教育資源、調動教育主體積極性奠定先行基礎。[8]社區教育實踐基地具有拓展幼兒學習空間、豐富幼兒教育資源、拉近幼兒園與家庭及社區之間關系、營造完整育人環境等價值,并表現出以幼兒發展為核心追求、整合教育資源等特征。社區教育實踐基地的建構一般應通過幼兒園主動引領、爭取行政支持、形成協同育人共識、簽訂共建協議、制訂共育方案五個不同的環節來實現,它基于社區的優質資源而直接將教育空間搭建在資源現場。社區教育實踐基地的建構途徑應包含搭建資源平臺、組建導師與志愿者團隊、設置形式多樣的研學活動等,為幼兒的主動探索和深度學習提供豐富的材料和信息刺激源。此外,共育成果的展示與交流對基地建設的反哺也應成為深化家園社協同育人的重要手段。[9]
家庭是與社區聯系非常緊密的育人主體。雖然家庭對協同共育有著非常強烈的意愿,但是與社區的共育意識并不強,優質的社區教育資源也難以進入到家庭中來;家園共育目標不精準且內容發生偏移,導致家園共育演變為教育家長和處理家庭教育問題。[10]此類問題都是傳統家園社共育過程中經常發生的,協同育人的路徑沒有被打通。在以社區為核心的協同教育體系中,除建構專門的社區教育實踐基地外,還應在更寬泛的意義上理解社區與家庭之間的教育協同關系。一方面,社區應該主動向家庭開放教育資源,為家庭育兒活動提供知識、方法、場地、材料以及人力等方面的支持,開辦各種形式的親子論壇、研學平臺和學習小組;另一方面,社區還應該營造良好的環境和文化氛圍,鼓勵家長將幼兒帶到更廣闊的空間去開展活動,引導他們積極表達自身的教育訴求以及交流在幼兒教養方面的經驗或困惑,形成全員共育的幼兒教育氛圍。
三、以共育課程為載體推進家園社協同育人深入開展
在搭建協同育人平臺的基礎上,家園社的協同育人就必須進一步打破時空限制,探索協同育人的多維互動課程模式。[11]幼兒園、家庭和社區協同育人的課程建構聚焦于幼兒的學習與發展這一核心目標,并將教師、家庭和社區的協同發展作為其功能性目標,這一課程應該指向幼兒與教師、家庭和社區的共同發展。共育課程的核心目標和功能目標是相互促進、相互支持的,幼兒的發展依托于教師、家庭和社區的共同支持,而對幼兒的教育反過來又促使上述三者在實踐過程中不斷優化自身的教育理念和提升自身的教育能力。兩者在不斷的互動和反哺中實現螺旋式的上升。
幼兒園、家庭和社區協同育人涉及的內容十分廣泛,并且也有著扎實的課程資源基礎。共育課程的內容建構需要本著安全、優質、多元的原則,不僅要在形式上下功夫,還要在功能的深入挖掘和重組上下功夫。具體來說,共育課程必須選擇那些貼近幼兒生活、接近幼兒發展水平、富有教育意義及生動形象的內容,讓幼兒對這些內容能夠保持持久的興趣。因此,那些以主題呈現的課程如自然探索、生活安全、文化體驗等就應該成為共育課程的主要表現形式。因為這些課程不僅在內容上具有綜合性,它們涉及的內容也非常廣泛,同時這些課程不是發生于任何一個封閉的空間,它們不是抽象的邏輯知識,而是具體的經驗。如自然探索課程,它必須基于真正的自然情境才能讓幼兒真切地了解和認識自然。此時的共享自然探索活動就需要由幼兒園設置活動的目標,家庭為幼兒的興趣引導、經驗準備、安全防護等方面提供支持,社區則要提供場地及安全等方面的支持。缺乏任何一方的支持,自然探索活動都可能是不完備的,其價值的實踐水平就有可能僅停留于書面設計上。
在選定內容的基礎上,共享課程還需要有具體的承載平臺。對于幼兒的學習與發展來說,除了以幼兒園為依托開展各種園內活動外,家園社協同育人的平臺還包含社區探索、基地體驗、場館暢游、親子論壇等多種形式。共育課程及其實施平臺的建構也是在幼兒園、家庭和社區三方的協作下完成的,經由對資源和課程進行審議后,[12][13]需要三方共同來完成共育課程的頂層設計。共育課程的實施同樣需秉持開放的原則,應致力于通過提升幼兒的活動體驗感來拓展課程的實施范疇,完善課程的實踐方式。對課程實踐的評價也應采用諸如學習故事、成長檔案、行為觀察等方式來將重點聚焦于幼兒的活動過程,促使教育對象與育人主體實現共同成長。[14]
四、以聯動機制建構為條件保障家園社協同育人模式有效運轉
幼兒園、家庭和社區協同育人在目標上通過資源的共建共享來促進幼兒的全面有效發展,其根本旨趣就是使原本分散的各類教育資源實現增值。以社區教育實踐基地為平臺,以共育課程為育人載體,這種新型協同育人模式的有效運轉需要以信任激勵、行動協同、資源共享和評估反饋四個方面的聯動為機制保障。
信任激勵機制是指共育主體通過培育以信任為基礎的價值觀,為不同利益相關者協調彼此的戰略目標和主體關系提供行為準則,它包含調動系統內部成員積極性的一系列原則、制度和方法。信任和激勵是幼兒園、家庭和社區協同共育模式發揮作用的基礎性因素,是協同育人創新行為發生的基礎。信任激勵機制的建構應在建設寬松氛圍以及一致的文化價值取向的基礎上,以促進幼兒的全面有效發展為紐帶,引導幼兒園、家庭和社區樹立共同的教育愿景,增強共育主體彼此之間的信賴感,使家園社協同育人具備良好的心理和價值觀基礎。
行動協同機制強調系統內部各組織之間關系的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它致力于在明確主體責任的基礎上推動主體之間在行為層面的協同,因而它是促進幼兒園、家庭和社區協同育人模式發揮作用的核心和關鍵。[15]行動協同機制應該致力解決的問題是明確和維持共育各方的共同目標與責任,采取規范的程序、科學的方法來提升協同育人的質量。因此,它的建構就必須明確不同主體的權責,要確保信任激勵機制能夠有效地驅動不同主體根據自身的角色定位忠實地履行角色賦予自身的教育職責,并且在某一主體出現能力不足時能夠給予有效的支持。
資源共享機制是深化協同育人效果的重要舉措,它必須在盤活既有資源的基礎上通過二次開發來實現資源的增值。幼兒園、家庭和社區三者都具有不同類型和數量的資源,這些資源也有不同的應用方式。例如,以某一節慶活動為載體開展協同育人活動,如果幼兒園將活動現場搬進社區,那么幼兒園與家庭、社區就可以通過分工的方式擴大節慶活動的氛圍,讓幼兒實現對活動的深度參與。這種深度合作和有機融合可以最大限度地放大協同育人的效果,促使幼兒在對活動的深度浸潤中內化觀念和發展行為。
評估反饋機制是對協同育人模式進行矯正和優化的重要環節,其目的是對整個育人模式的全方面、全過程進行檢視,看其在何種程度上實現了協同育人的目標以及存在哪些方面的不足。除此以外,評估反饋機制的另外一個重要作用是可以密切不同教育主體之間的關系,它通過引導不同主體真實表達自己的看法來打破彼此之間的認識或思想隔閡,促使不同主體在更為坦誠的環境和氛圍下堅定對幼兒的共育觀念,并為尋求更優越的共育方法發揮集體智慧。
參考文獻:
[1]李曉巍,劉倩倩,郭媛芳.改革開放40年我國幼兒園、家庭、社區協同共育的發展與展望[J].學前教育研究,2019(02):12-20.
[2][4]王秋霞.家、園、社區協同教育的現狀、影響因素與發展路徑[J].學前教育研究,2014(05):64-66.
[3]徐東,彭晶,程輕霞.幼兒園—社區協同共育的研究綜述:基于2006—2020年CNKI的數據分析[J].高等繼續教育學報,2021(04):55-60+80.
[5]朱鈺.幼兒園、家庭和社區協同教育的調查及對策研究[D].安慶:安慶師范大學,2019:1.
[6][8]吳冬梅.幼兒園、家庭、社區協同共育[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0:15,19.
[7]趙純.以資源整合為導向的“家園社”共育研究[J].求知導刊,2021(52):17-19.
[9]韓鳳梅,李冬梅.幼兒園社區教育實踐基地建設與運行:協同共育模式的探索[J].廣東教育(綜合版),2022(07):61-62.
[10]張韻.幼兒園家園合作現狀研究:以重慶市主城區幼兒園為例[D].重慶:西南大學,2009:40-41.
[11]吳冬梅.“社區+”幼兒園發展模式探究[J].學前教育研究,2019(02):93-96.
[12]秦紅.堅守兒童立場的幼兒園課程資源審議[J].學前教育研究,2022(03):87-90.
[13]汪秋萍,趙琴.幼兒園課程方案在審議中優化[J].安徽教育科研,2022(25):1-3.
[14]原晉霞.我國幼兒園課程質量現狀探索與提升建議[J].學前教育研究,2021(01):43-56.
[15]侯麗.幼兒園與家庭合作關系的重構[J].學前教育研究,2020(10):89-92.
Innovating KindergartenFamilyCommunity Cooperative Education
HAN Fengmei
(The Kindergarten Affiliated to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Kindergarten, family and community play different but irreplaceable roles in the process of childrens growth. Kindergarten has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cooperation with family, but still ignores the effects of community. To innovate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l of the three parties is to reset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m, and especially make community become another stable education platform for childrens learning that can provide not only curriculum resource but practice field and approaches for children to explore based on their interests and abilities.
Key words: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kindergartenfamilycommunity cooperation, community edu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