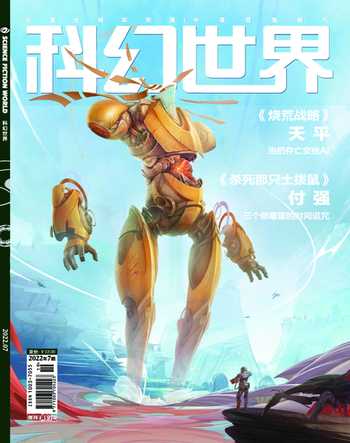“亡我之心不死”
索何夫
科幻史中,“外星人的威脅”是最常見的題材之一。異星球的牛鬼蛇神只要一有機會,就會從宇宙深空中鉆出來,把我們這小小藍色星球蹂躪一番,甚至根本無需理由。
比如首款此題材的電子游戲——1978年的《太空侵略者》,及之后由雅達利等公司批量生產的跟風游戲,玩家只需知道“外星人亡我之心不死”,再按下按鈕,朝著畫面上代表它們的小點開火就行。《樂一通》系列動畫片里的“火星侵略者馬文”也只需告訴觀眾,他相當憎恨地球,解釋理由?毫無必要。但還有不少作品不能如此草率交代。在不同時代、不同創作者和受眾的構想中,“外星入侵者”被賦予了千差萬別的形象、行為模式和行動理由,而這一切或多或少是當時社會意識的某種投影。
并不始于威爾斯……
赫伯特·喬治·威爾斯的《世界大戰》有深遠影響,“外星人”這一概念被認為是由他首提。但這錯得有些過頭,自伽利略用天文望遠鏡觀測開始,“在其他天體上可能有人”的想法就已出現。光學儀器進步后,人們逐漸確認火星有與地球一樣的固態地表,甚至發現了“運河”(雖然后來被證偽),于是這些想法更被廣泛接受。到18世紀時,更有甚者提出,在地球的溫帶利用作物排出千米級尺度的圖案或“標語”,來引起“外星友人”的注意。

沒錯,在啟蒙時代,《三體》宇宙那套“黑暗森林”宇宙觀壓根不會有市場。第一次產生“理性主義”概念的人們認定,任何具備智慧與理性的生物都可以交流并與人類共情。“暴露自己”在那個時代從不是問題(20世紀下半葉也如此)。由于對宇宙的尺度、生命誕生條件的苛刻性缺乏認識,在剛剛將地球踢下“宇宙中心”神壇的近代人們的想象中,其他世界上不但“可能”,而且“一定”會有智慧生命,且和人類相似。
基于此,19世紀,“外星人”的科幻小故事出現。有趣的是,由于維多利亞時代和“鍍金時代”歐美社會對“文明開化”的普遍自負,以“祖輩”出現、與主角敵對的外星人形象往往被呈現為相對弱勢的一方。作為最早被影視化改編的小說之一,凡爾納《環繞月球》的描寫重點雖和外星人關系不大,但喬治·梅里埃拍攝的改編電影卻借鑒了更晚的威爾斯的《月球上的第一批人》中的情節,加入大段“大戰月球人”的橋段。這批最早的異星敵人丑陋、原始、揮舞著粗陋可笑的長矛,完全是18、19世紀歐洲版畫上那些“遙遠大陸上食人生番”模樣。20世紀初“科幻冒險”小說代表的《火星公主》也有相似的思想內核,火星人骨子里是一群封建社會的人類,是“異域的、被征服的”文明。而主角(原南部邦聯軍官)也確實對他們進行了“征服”,勝利后得到了公主。

同時代威爾斯筆下的火星人則是異類,《世界大戰》的最大創新,是成功地描寫了一個“不通人性”的敵對種族。火星人與“人”全無共通之處,是一群充滿徹底敵意與侵略性的“猛獸”——他們依靠“吸血”生存,“非人化”顯而易見。而火星人在登陸后大量使用化學武器無差別消滅人類、摧毀一切的行為,也顯然像“無法理解與溝通”的“天災”。
這種“外星威脅”是變形的“自然災害”:不能對抗、無從避免、充滿惡意,最終的消失也非人力干涉所致。這種文化形象在之后早期克蘇魯神話中得到完善——克蘇魯與“古老者”“飛水螅”“修格斯”“星之彩”“夏蓋蟲族”等,都被設定為“從遙遠的外星球飛來”。“非人化”、不可交流、充滿惡意(“伊斯之偉大種族”是例外),無法以人類的技術手段進行對抗。最典型也最有創意的是“星之彩”。這些純粹以能量而非一般意義上的物質形態存在的外星來客以隕石形態的“卵”穿越星際空間,根植于被其入侵的土地,將土地上的一切生命視為“獵物”,一視同仁地予以扭曲與吞食,甚至干涉當地居民的思維,阻止其逃離“捕食”。

這反映了那個時代的人們——至少是較為發達的國家和地區的人們——的精神狀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他們深信自己的“優越”,對落后的地區和社會有“俯瞰”情緒,但驟然現代化帶來的新威脅與新挑戰(比如各種傳染病)也使他們不安。當這些情緒被投射到“外在”時,就是如此觀感。
“文明人”“猛獸”與“內鬼”
兩次世界大戰重塑了人類的社會面貌和思想意識。一戰之前,世界上的國家數量不多,歐亞大陸被幾個強大帝國分別統治,第三世界大多是殖民地、委任統治地、自治領和保護國,主權國家寥寥無幾,發達社會成員的優越感很強。20世紀下半葉,世界上已經有近兩百個獨立國家和地區,至少在法理上和共識上,各民族、人種已經確定了平等的地位。
20世紀末的科幻作品自然也反映了這一劇烈變化,“蠻荒土著”“天災”樣的異星來客,逐漸變得與人類平等起來。除《基地》系列“銀河中僅有人類存在”的特殊設定之外,大多數作品中,外星侵略者已有現代化國家和政權,甚至與人類文明有外交。
異星怪物們的行為動機與邏輯也逐漸“正常”:20世紀下半葉逐漸流行的太空歌劇作品中,外星人的行為越發與人相似。且不提《星球大戰》這類由眾多非人類智慧物種與人類共同建立星系級政權的作品,在大多數科幻作品中,外星人至少變得“可以談判、接觸”了。
因此,對許多外星文明,可以以某種人類文明模板進行描述,尤其是他們入侵地球的動機。許多是“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地球殺場》中,異星來客的目的是“殺人奪地”、開采資源,和19世紀帝國主義列強無異;游戲《命令與征服》系列中的“思金人”是一個“星際采礦公司”;《異星歧途》里的“外星侵略者”則是一群“太空中的西班牙征服者”,在只發展出前膛炮和方陣步兵的時代就僥幸點出躍遷引擎科技,誤打誤撞地讓陷入瓶頸的地球人得到天賜良機;《銀河系漫游指南》里的沃貢人活脫脫一副唯利是圖地產商加腐敗官僚模樣。還有不少異星人文明則索性雜糅了古地球上的軍事貴族、狩獵部落和斯巴達式軍國主義政體的特征,純粹為挑戰與榮耀而戰,以便充當人類主角的難纏對手——經典的有“鐵血戰士”,《光暈》系列中的“精英戰士”一族,以及替代他們的“鬼面獸”,乃至因“克林貢語”這門杜撰語言而廣為人知的“克林貢人”。

許多“太空壯劇”里人類和地球已微不足道,成為星際文明“萬國”里相當普通的一支。弗洛·文奇的《天淵》《深淵上的火》,約翰·斯卡爾齊的《垂暮之戰》系列中,諸多外星文明完全是20世紀末國際社會的“太空版本”。迥異的文明形態、社會結構及對人類開戰的理由,從宗教、經濟、地緣(星際)政治分析,都可以在人類歷史中找到對應。大衛·布林的《提升之戰》系列,人類甚至“淪落”到與受到“提升”的黑猩猩和海豚并列智慧生物行列——這是20世紀末多元化思潮影響文藝層面的反映。極致表現是“黑衣人”系列:大批穿著皮套的外星人直接合法移居地球生活,以身作則地履行星際級別的“種族多元化”。
不過,并非所有外星人都變得“善解人意”,科幻黃金時代“驚險故事”留下的影響從未消失,另一些異星來客仍然“不可交流與理解”。只不過,它們不再那么類似“天災”,更趨近兼具致命與智慧的猛獸。
最初代表是科幻小說《黑色毀滅者》中的怪物“科爾”。高度智能具有貓科動物外表的掠食者混上偶然抵達當地的人類飛船后,為奪取鉀元素大開殺戒,極具破壞力和敏捷性,險些葬送整支科考隊的性命。
之后數十年里,這樣的套路被反復運用,包括:“有智慧的猛獸”——異星生物兇猛、強大、智慧,不會被小伎倆或陷阱輕松困住,甚至可以反過來用這類招數對付人類;“入侵人類空間”——通常包括城鎮、移民點、飛船、科研基地等,具“人類日常生活”與“封閉”兩個特征,破壞力強且人類“無處可逃”,極具恐懼感與壓迫感。
這一題材相當適合影視化,最著名的形象出現于驚悚或恐怖片中,比如《異形》(Alian)、《怪形》(The?thing)和《異種》(Species)。值得一提的是,它們又具備“潛伏與取代”人類的能力——“異形”這位“元老”隱遁藏身的本事自然不必說,它們的生命周期也高度依賴對人類的寄生。從卵中孵化后,抱臉蟲必須盡快發現人類宿主,并將異形胚胎注入目標體內,之后誕生的異形則會整合對方的一些DNA,繼承部分人類身體特征(比如肢體比例和雙足步態等),同時也有人類的智慧,從而可以滲透逃生艙(《異形1》)、切斷電源(《異形2》),或者直接在出口設伏(《異形4》)。從南極洲冰蓋下醒來的“怪形”雖戰斗力略遜一籌,但卻可以完全融入并讓人難以察覺,人與動物可都被神不知鬼不覺地消滅、取代。而作為人類—外星生物混合體的“異種”則更是危險,具備人類的智慧、強悍的身體和幾乎完美的潛伏能力,極難被發現和攔截,還可以輕易地四處滲透。

這些經典形象之所以普遍與“潛伏與取代”人類有關,很大程度上是冷戰時代的歷史烙印。正如核武器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在科幻中刻下深深的“核末日”痕跡一樣,當整整一代人都習慣于“保密防諜”時,“被敵人滲透”自然也成了最深的夢魘。
蟲子、神靈與難民
另外一個長期流行的概念“蟲族”,也是在冷戰時代逐漸定型的。雖然大多數“路人”接觸到這個概念始于現象級大熱作品RTS游戲《星際爭霸》,或者由海因萊因的《星船傘兵》改編的背離原著的電影《星河戰隊》,但對科幻愛好者而言,早在“太空中的魔獸爭霸”(人們對早期《星際爭霸》的稱呼)出現之前,他們就很熟悉這個概念了。
對于“真社會性生物文明”蟲族的描寫,是在太空歌劇或太空壯劇逐步繁榮的過程中普及的,畢竟外星人“擬人類化”之后,這類題材原本的“異質”感就不那么充足了。而冷戰導致的對立世界體系,使“國際社會”在文藝工作者眼中一分為二:多元、互動、有競爭也有合作;一元、缺乏互動、競爭與挑戰激烈——且這樣的刻板印象很難抹除。
同時,二戰后生命科學發展,人們的認知提升,“鐵板一塊”“非人類”的對手順理成章地被套上“蟲族”的模板。冷戰中雙方的隔閡過深,導致“不明白對方想做什么”成為常態,在一定程度上喚醒了人類物種記憶中“被捕食”的最原始恐懼,科幻作品中“蟲子們唯一的目的就是吞噬”,面對無腦、簡單、不可接觸的敵人,人類唯一的反應自然也只能是堅決回擊。

相較之下,另一類外星人“高深莫測”多了。在許多20世紀末或者本世紀的作品中,常見“遠古超級文明”這個設定,比如《光暈》系列里的“先驅”和“先行者”,《戰錘40000》的“古圣”,《星際爭霸》中的“薩爾那加人”,或者《質量效應》中建立“神堡”的“普洛仙人”。這些“超文明種族”作為反派,對后續文明種族不信任乃至鄙視,往往出于期望改變宇宙秩序的目的而行動,其動機更接近古典神話里喜怒無常、動輒降下天譴的神靈。
當然,這種設定的大量出現和宗教關系不大,當時宗教崇拜已衰退,但在流行文化方面有跡可循:20世紀后期,偽科學理論“眾神戰車”曾風靡一時,并帶動大批所謂“史前超文明”“古代人類文明”的“研究”。這套學說認為,人類文明可能是地球之外“先進文明”的饋贈,而大量古文明的遺物,比如埃及和瑪雅的金字塔、納斯卡巨畫、兩河流域的城市遺址等,都被牽強附會為“遠古超文明”造物,而傳說中的“大洪水”和其他遠古災難,則被說成是“外星人的天譴”。這雖最終普遍被學術界所證偽,但在流行文化中頗具影響,并最終因文化市場的“消費者需求”在科幻作品中登堂入室。
除此之外,20世紀末外星人的“造訪”還有一種動機——“逃難”。環境危機不但催生了大量諸如《后天》《未來水世界》這樣的作品,也讓許多外星人成為“反面典型”。這些因破壞了自己家園而被迫背井離鄉的家伙要么直接殺人奪地,要么像《第九區》里的“大蝦”們一樣蹲難民營茍延殘喘——雖然后者真正要描寫的,遠不是那群“難民”本身。
總之,“我們在宇宙中并不孤單”雖仍沒被事實證明,但也已是相當多人潛意識中默認的“事實”。無疑,在遇到貨真價實的外星人之前,人們會繼續將所生活的客觀現實及所造成的思考投射到對這個“他者”形象的構筑之中,讓它們繼續以各種理由和動機與文藝作品中的人類展開沖突。某種意義上,這種沖突是對我們自身認知沖突的寫照,既是與人類的,也是與自然的。
【責任編輯?: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