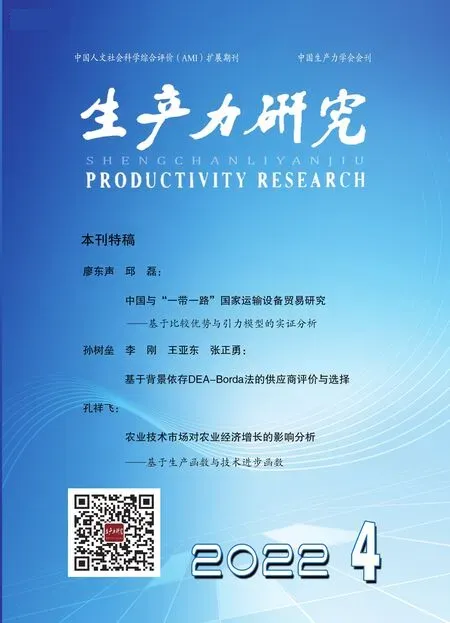“節能減碳”政策對企業經營績效的影響
秦炳濤,賈雪萍,葛力銘
(1.上海理工大學 管理學院,上海 200093;2.上海財經大學 城市與區域科學學院,上海 200433)
一、引言
全球變暖的問題引發世界各地加強對環境問題的重視,而“二氧化碳”的排放是全球變暖的原因中重要的組成部分。碳排放來源中,化石燃料發電產生的能耗巨大。中國是世界上能源消費最大的國家,貢獻超過3/4 的能耗增長,也是碳排放和煤炭消耗最大的國家。短時間內,煤炭仍然是中國能源結構的主體部分,目前碳排放來源有90%來自煤炭。
由于煤炭是碳排放的主要源頭,若要實現減少碳排放、改善環境質量的目標,中國采取降低經濟發展過程中煤炭等能源的消耗量的方法是可行的(林伯強等,2010)[1]。因此,2011 年國家發布了《萬家企業節能低碳行動實施方案》(下文簡稱“節能減碳”政策),目的在于激勵重點排放單位重視減碳,提升管理質量,最終達到降低能源排放,降低環境污染的目的。該政策對各個省份年綜合能源消費量超過1 萬噸標準煤的主要耗能單位指定硬性煤炭消耗量指標,從而限制碳排放量。據估計,2010 年上述名單內企業能源消耗達全國消耗量的60%。“節能減碳”政策覆蓋范圍廣,制定指標硬,是目前我國較大型,較有代表性的環境規制政策。中國政府實施如此大規模的“節能減碳”政策是否會影響企業的經營績效,實現企業層面的環境與經營績效的雙贏?這是本文要探討的問題。
現有研究成果從多方面探究了環境規制與企業經營績效之間的關系,然而現有文獻仍然有不足之處,本文將對該領域的研究做出如下補充。從研究層面的選取上,現有研究以地區和行業為主,少數選取企業層面,容易遺漏或誤判環境規制對企業的真實影響。有鑒于此,本文數據選取時,采用工業企業數據庫中的微觀數據。另外,在現有研究中,環境規制變量選取大多為排污費、污染治理支出以及排放達標率等指標,具有明顯的行業差異,且與企業主營業務關聯度較高,很難反映企業在政府環境規制下的主動行為。基于此,本文選取具體的政策變量,將“節能減碳”政策作為本研究的政策變量。
二、實證設計
(一)模型設計
本文將“節能減碳”政策的實施視為一項“準自然實驗”,并采用雙重差分法評估“節能減碳”政策對企業經營績效的影響。其中,將工業企業數據庫中列入“節能減碳”政策萬家企業名單內的企業作為處理組,把數據庫中未列入名單的企業列為對照組。設定雙重差分基準回歸模型,如模型(1)所示。

模型(1)中,ROAit表示企業i在年份t的企業經營績效;didit是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若企業i在年份t屬于“萬家企業”則等于1,否則等于0;Zit是影響企業經營績效的變量;μi為企業固定效應,δt是年份固定效應,εit是隨機擾動項。系數α1表示環境規制與企業經營績效的影響,若在控制了其他可能影響因變量的變量之后,α1顯著為正,則表明環境規制能夠提高企業經營績效。
(二)變量說明與數據來源
1.被解釋變量:企業經營績效(ROA)。參考涂正革等(2019)[2]等現有多數文獻的做法,用資產收益率(ROA)來衡量企業的經營績效。
2.核心解釋變量:環境規制(did)。通過考察年份內是否屬于“萬家企業”名單生成虛擬變量。參考康志勇等(2018)[3]的做法,由于“節能減碳”政策名單由地方節能主管部門統計并上報,并且實施時間2011 年為“十二五”的開局之年,從統計名單到發布和實施有一定時滯作用。因此,在統計上報后到實施前,“萬家企業”可能已經做出反應,因此本文將時間節點設立為2010 年,以企業是否在2010 年后屬于“萬家企業”來確定核心解釋變量的值。
3.控制變量:借鑒余偉等(2017)[4]、張愛美等(2020)[5]文獻中關于企業經營績效影響因素的研究成果,本文選擇基本包含會對企業經營績效產生顯著影響的一些因素,主要是工業企業自身的一些特征:企業規模(size);資產負債率(lev);企業成長性(growth);公司年齡(age);成本費用利用率(cost)。總共將五個控制變量添加到模型中,以減少由于缺少變量引起的估計偏差。
本文計算變量的原始數據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2006—2013 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財務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但由于數據庫體量龐大,有些企業數據存在異常值。因此參考張濤等(2016)[6]的方法對不合邏輯數值進行處理,第二部分是《萬家企業節能低碳行動實施方案》企業名單。本文將名單內“萬家企業”數據匹配到工業企業數據庫中。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基于前文設計的計量模型,為避免回歸過程中可能的多重共線性問題,本文進行了相關檢驗。檢驗結果顯示,相關系數值均小于0.5,方差膨脹因子小于1.14,表明各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回歸模型的選擇通過Hausman 檢驗,選擇固定效應模型。
(一)萬家企業減碳政策與企業經營績效
表1 報告了模型(1)的回歸結果。從第(1)列結果可以看出,當不加控制變量時,“節能減碳”政策對萬家企業經營績效的回歸系數為0.019,且在1%的置信水平下非常顯著,說明該政策對萬家企業的經營績效是正向效應。為降低可能存在的遺漏變量誤差,本文在第(2)列~(6)列的回歸中逐步引入影響企業經營績效的重要變量。在控制變量加入后,核心解釋變量環境規制的系數仍然為正,且顯著性未發生較大變化,而其絕對值呈逐漸減小的趨勢,表明控制變量的加入有效地緩解了遺漏變量偏誤,實證結果具有可靠性。在引入控制變量后,環境規制變量的系數仍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為正,因此我們可以首先得出環境規制政策與萬家企業經營績效存在正向顯著相關的關系。

表1 基本回歸結果
接下來進行控制變量的分析:企業規模(size)系數為負,規模較大的企業得到政府和公眾的關注相對更多,企業會更加注重環境的保護以樹立良好的形象,同時能夠形成規模效應降低治污成本,承擔環境保護的責任與義務。小企業由于缺少規模效應可能會導致治理污染的成本較高(許東彥等,2020)[7]。本文猜測,企業的規模效應沒有達到,環境規制導致成本上升,使經營績效下降。資產負債率(lev)系數為負,企業資金周轉能夠有效進行,出現無法清償債務的概率就更小。在這樣的情況下,企業更能有充足的時間和資金去提高環境,而保持經營績效的提高;公司年齡(age)系數為正,公司年齡大,發展歷程長的企業在環境規制政策的影響下,對于企業經營績效的促進能力更大;企業成長性(growth)系數為正,何玉等(2017)[8]文中提到,企業的銷售收入增長率數值較大,表明企業具有較大的發展潛力。具有良好發展前景的企業愿意在環境保護上投入更多的人力與資本,以此提升公司形象以及創造更多的利潤。成本費用利用率(cost)系數為正,成本費用率指標高的企業具有更好的成本控制能力和管理水平,企業組織管理可以通過有效的手段節省成本,提高運營質量。
(二)平行趨勢檢驗與動態效應分析
雙重差分模型估計有效性的前提之一就是實驗組和控制組在政策實施之前滿足同趨勢假設。即在實施該政策之前,處理組和控制組的變化趨勢是否基本一致,在政策制定后才出現明顯差別,以確保估計結果是由于政策本身導致的,而非時間點之前的某些因素。為了驗證本文DID 模型的適用性,考察“節能減碳”政策實施之前,這種效應是否就已經存在,本文進行了同趨勢檢驗。
此外,為彌補基準回歸模型無法反映不同時點政策的影響差別,本文參考任勝鋼等(2019)[9]的研究,采用事件研究法,構建以下動態效應模型分析該政策的時點差異:

其中,以政策實施前的2010 年作為基準年,其系數表示2006—2013 年的一系列估計值。其他變量定義與回歸模型(1)相同。
圖1繪制了βt的估計結果及其90%的置信區間可以發現,βt的估計值在2010 年政策實施之前均不顯著,這說明萬家企業和非萬家的變化趨勢在政策實施之前并無明顯差異,說明滿足平行趨勢假設。

圖1 共同趨勢檢驗
進一步分析發現,βt的估計值從2010 年才開始顯著,且2010 年回歸系數產生峰值,說明政策實施當年,對企業經營績效的促進效應很大。由此可見,“節能減碳”政策能在短期內產生極大的效果,企業對于該政策反應速度較快,政策基本無滯后性,具有立竿見影的效果。
在政策實施當年過后第一年,系數呈現斷崖式的跌落,表明“節能減碳”政策在實施過后有比較明顯的冷卻,企業對政策的反應熱情降低。政策實施后第二年的系數相較于第一年有逐漸增大的趨勢,且上升幅度大于實施前,說明政策對于企業經營績效產生了一定的效果,政策實施對萬家企業經營績效的影響逐年增大。但需要注意的是,政策實施過后的第三年企業的績效又出現了降低。由此可見,環境規制倒逼企業增加創新投入,可能的效果都在短期得以實現,兩年后政府對政策反應熱情疲軟。
(三)穩健性檢驗
1.處理樣本選擇偏誤。地方政府的政策選擇可能具有非隨機性,會對本文的估計造成內生性偏誤。為此,本文參照王班班等(2020)[10]采用的方法,用傾向得分匹配法(PSM)來緩解樣本選擇偏差。具體做法為:根據控制變量從非萬家企業中尋找對照組企業,保留所有匹配成功的企業作為下一步DID 模型的樣本。經過PSM 匹配后得到的雙重差分結果如表2所示,處理后的樣本得出的回歸結果和主回歸結果一致。采取逐步加入控制變量的方法,結果依然穩健。

表2 穩健性檢驗回歸結果
2.數據偏差處理。考慮到本文采用的數據較多,數據可能存在偏差,為了緩解這種偏差對結果造成潛在不利影響,本文采用兩種處理方法。首先,對各連續變量進行了10%分位數以下和90%分位數以上的縮尾處理,并進行回歸,回歸結果顯示在表3的(1)列,可知顯著性及符號方向均未發生變化。其次,采用了控制標準誤的方法,對模型進行聚類標準誤處理,結果顯示在表3 的(2)列,結果同樣與基準回歸差別不大。說明“節能減碳”政策有助于促進企業經營績效,結果具有穩健性。

表3 縮尾與標準誤
四、技術創新機制分析
根據前文的理論分析,本文認為萬家企業節能減碳政策通過技術創新改善企業經營績效。為了檢驗這一傳導機制是否成立,本文選取能直接衡量自主創新能力(寇宗來和劉學悅,2020)[11]的專利數據作為企業技術創新的代理指標。基于數據的可得性,本文使用專利數作為技術創新指標,而不是與環境規制更貼切的綠色專利數據。這是基于涂正革等(2019)[3]的文章采取的方法,通過比較每個省份的綠色專利總數和發明專利總數,發現兩者之間相關系數高達0.98,且在各省份之間的排名幾乎一致,近似可以互相代替。
為估計環境規制的企業創新效應,設定雙重差分回歸模型,如模型(3)所示。

patentit表示企業i在t年的專利申請數,具體有4 個變量,即發明專利數、實用新型發明專利數、外觀設計數以及這三種專利的總和。表4 報告了相應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對于這三種專利數或是專利的加總,回歸系數都顯著為正,即萬家企業節能減碳政策能夠增加企業的專利申請數量。萬家企業節能減碳政策促進企業加大創新投入,進而間接降低生產成本,最終增加企業經營績效。因此,萬家企業節能減碳政策通過技術創新途徑影響企業經營績效得到有效驗證。

表4 機制分析回歸結果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基于工業企業數據庫,實證研究了“節能減碳”政策與企業經營績效之間的關系。實證結論發現:總體來說,“節能減碳”政策對企業經營績效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該政策在促進保護環境的同時,能夠以技術創新作為間接傳導機制,促進企業經營績效的提升,進一步實現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兼顧。
本文分別從政府、企業兩個層面提出環境規制政策實施的建議。
第一,企業要積極應對環境規制,充分發揮環境規制的作用。從本文的結論來看,“節能減碳”政策對企業經營績效有顯著的促進作用。然而根據傳統觀點,環境規制直接增加了企業的成本,最終導致企業的經營績效減少,因此本文的結論為企業積極主動應對環境規制提供了依據。工業企業必須要脫離傳統觀念,通過實施環境規制政策積極尋找新的發展機會,在完成環境規制指標的情況下,同時實現企業內部調整升級,使環境規制成為公司發展的機遇。并且積極配合有關環保部門的監督管理工作,保障環境規制政策切實有效。
第二,企業提高技術創新水平,充分發揮技術創新的機制作用。企業必須轉變企業生產方式,推進綠色技術創新研發。利用環境規制政策倒逼企業技術創新,提高企業自身的技術創新水平,促使企業長期可持續發展。企業需要注意人才開發,并在科研方面投入更多的資金,并且制定相關規定引導科研人員致力于綠色技術創新研發。同時也要加強監管,使綠色技術創新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從而通過鼓勵綠色技術創新,在完成環境規制政策指標的前提下,實現企業的轉型和升級,使得環境規制影響將是可持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