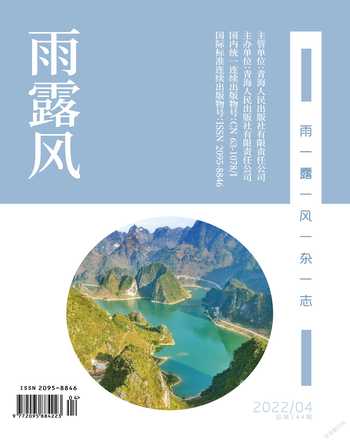侗族作家楊仕芳小說《望川》的“水”文化審美意蘊

摘要:侗族作家楊仕芳的中篇小說《望川》講述了一位少數民族地區孩子的成長經歷,對人性、人生以及命運的迷惘進行探索。小說在“水”文化審美意蘊的建構上可謂獨樹一幟。在小說中,水是萬物之源,具有生命佑護之美;水之靈性,成就了“我”對萬物的思辨之美;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具有辯證的哲理之美。小說展示了“水”文化多重深厚的審美意蘊,給人以唯美愉悅的審美感受。
關鍵詞:楊仕芳;望川;“水”文化;意蘊美
楊仕芳,廣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縣人,是一位在風雨橋和鼓樓中走過自己青春歲月的70后侗族作家。侗族人民用木頭建構起高聳的鼓樓,而楊仕芳也在致力于用文字來建構自己的文學“鼓樓”。
楊仕芳先后在《山花》《花城》《民族文學》等數十家刊物發表作品,部分作品被《新華文摘》《小說選刊》《小說月報》等刊物轉載,著有《陽光穿過我們的村莊》《而黎明將至》《白天黑夜》等5部小說集,曾經獲得2007年、2008年、2009年《廣西文學》青年文學獎,2016年《民族文學》年度文學獎,2018年《廣西文學》年度優秀作品獎,第四屆廣西少數民族創作“花山”獎,第九屆廣西文藝創作銅鼓獎等獎項。
一、萬物源頭之“水”——生命佑護之美
小說題目名為“望川”,具有一定的象征意義。望川:眺望生命之川,探索生命之源,思考生命的意義。《管子·水地篇》說:“水者,何也?萬物之本源也。”水為萬物之源,水象征著生命的流逝與生生不息,正如《論語》所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有評論者指出:“小說題為《望川》,川的具象是傷疤河,抽象就是生命的哲學意象,‘望川’其實就是望命運之河,思生之走向。”[1]
小說對“我”的身世的描寫就與水有關,“我”的出現可以說充滿了傳奇和神話色彩。小說中寫到,“我”是一個棄兒,出生后就被親生母親放在一只木盆里隨水漂流,是養父一大早在河邊發現了“我”,把“我”帶回家中,養母、哥哥和姐姐都把“我”視為一家人。
父親在河邊發現“我”,把“我”帶回家。一家人都很好奇地圍著木盆,不相信這是真的,還懷疑“我”是父親在外和別的女人偷情生下的私生子。盡管父親一個勁地解釋:“我真的是從河里把這孩子撈上來的,木盆里還有一封信和玉鐲嘛。”父親還叫黑狗過來證明。一家人還是將信將疑,母親堅持把“我”留下來,并用甘甜的乳汁哺育了我。在這個情節中,作者寫到了“我”被遺棄的地方是在一條河流上,被父親發現,不幸中的萬幸。作者選取“水”作為主人公再生的載體,體現了對“水”的尊敬與崇拜之情。
“那條河叫傷疤河,在逐漸明白自己身世以后,我時常獨自坐在河岸上,長久地凝望著流水,以及水底的水草和游魚,恍惚覺得心間也存在一條傷疤。”[2]“我”經常坐在河邊,與河流對話,訴說著自己的苦悶與憂思。
從“我”的身世敘述中,我們仿佛看到了很多與之相類似的關于水生的神話原型。楊仕芳正是利用這些神話原型為自己的小說添加了一筆精彩的濃墨,化神奇為精華,使小說趣味盎然、引人入勝,增加了小說的審美文化意蘊。正如中國作協創研部原主任、研究員胡平對楊仕芳小說所評論的那樣,“他的作品里有一種原型意識,這種原型也許比較久遠,也許和神話同源,但是很寶貴,是民族的文化基因,現代小說里很稀缺。”[3]
人類通過對自然現象的觀察和描寫,寓情于景,賦予自然界中的事物各種文化內涵。“水”作為一種自然現象,具有多重哲學與美學的內涵,在文學作品中被賦予了深刻的思想文化意蘊。水之屬性可以令人生發出種種的聯想,比如歲月的蹉跎、歷史的變遷、年華的易逝、青春的短暫、人生的無常,以及純潔、溫順、清麗、柔韌的德性等,這些都成為中國文學中常見的重要母題之一。
中國古代就有嬰兒漂流被人收養的故事。例如,小說《西游記》中講到唐僧的身世就很凄慘,父親在赴任途中遇害,母親被惡人霸占,唐僧出生后,母親擔心他會遭遇不測,就把他放在江中木板之上,順水漂流,后來被金山寺長老救起,取名江流,長大后他虔誠向佛,法名玄奘。人們一提起唐僧,就說他是“江流兒”。濟寧學院副教授王振星以為,“江流兒”的原型應來自異生神話“漂流嬰兒”伊尹。[4]《呂氏春秋·本味》記述伊尹異生神話。伊尹在大水之中浮桑木而存活,其母為保護兒子化作了桑木。神話傳說中的“漂流嬰兒”被賦予了神奇性,“漂流嬰兒”的神話內核在于生命意志的堅毅和頑強。伊尹從一個奴隸成為商湯的輔佐,其間經過了種種磨難;唐僧西天取經經歷了九九八十一難,修成正果,成為圣僧。“我”被生母拋棄于河流之中,被養父救起并撫養長大,歷經艱辛與坎坷,最終長大成人。
中國有“漂流嬰兒”的傳說,國外也有類似的神話故事。在《圣經》中“水”象征著生命的創造與繁衍,如摩西的出世就與水有著密切的聯系。《舊約·出埃及記》中有記敘,以色列英雄摩西在出生后被放在一只抹了石漆和石油的蒲草箱里,箱子被放置在河邊的蘆荻中,后來被埃及公主發現救起來,箱子里的孩子被起名為摩西,意思是“從水里拉出來的”。《望川》中的“我”也是被生母放在一只木盆里順水漂流,最終被養父救起,與《圣經》中摩西的出世有相似之處。“我”雖然沒有成為摩西那樣的英雄,但是在父親的養育之下,也成就了自己的平凡人生。
二、水之靈性,成就了“我”對萬物的思辨之美
楊仕芳之所以嫻熟自如地把這些神話傳說運用到他的小說里,可以說對“水”的神話原型是很熟悉的。他把小說的主人公身世寫成了一個類似“江流兒”的故事:“我”不幸被親生母親放入江流中,又幸運地被養父發現并收養,吸吮著養母的乳汁,獲得了重生。“水”賦予我生命, 也賦予我多愁善感、尋根究底的性格,“我”一直對河流、對親生父母、對自己的命運充滿了好奇、思考與探索。
“我”常常來到河邊,想像著母親當年拋棄“我”之時的萬般不舍與無奈之情。在多少個夜晚,“我”一直在夢中夢見這條傷疤河、夢見“我”和母親相見的情景,夢見夢幻般的、無助的生母—— “一個披頭散發的女人”向我招手:水、河流、河邊夢幻般的霧氣、“我”和母親,營造了一個迷離朦朧的意境,構成了一幅夢幻的圖景,如此的唯美卻令人心酸。
小說還寫到,因為河流發過洪水,“我”對它既喜歡又觸景生情。“我在河流里學會思考,也在河流里學會了游泳”,還不滿十歲已經可以來去自如地在水里抓魚。每當“我”受到委屈時,總喜歡靜靜地躺在河水里,“看到陽光從天而降,落在石塊上,閃出一道道細碎的熒光,小魚靜默不動。”“那是一個奇妙的世界。那條河流給我留下的記憶,多半是美好的。”[2]在這里,作者親水、習水,把水當成了自己靈魂的寄托,表達了對水佑護生命的一種禮贊。這里把水寫活了,寫得富有人性,寫出了水的奇妙、水的情韻、水的靈性,寫出了“我”對水的一種依戀之情。
三、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具有辯證的哲理之美
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在作者筆下,水有時候是溫柔平靜的,有時候卻充滿了惡的肆虐。
小說描寫,“我”的再生得益于水,平靜的傷疤河拯救了“我”,也撫慰了我。 “我”被生母拋棄于河水之中,又得到養父的呈救與撫養。“水”佑護了我,使“我”對之充滿了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感激之情。我學會了游泳,在水里自由自在地“翱翔”。“我”也學會了與“水”對話,每當“我”感到孤獨煩悶時,就到河邊,向河水傾訴。河水撫平了我的心靈,“水”成了我內心甜蜜的溫柔鄉。
在很多民族的神話中,水可以是生命的源泉,也可以是毀滅的惡魔,水的兩面性體現了神的兩面性,神可以賜予人類水和生命,也可以用水毀滅人類。在《圣經·創世紀》中就有人類作惡,上帝發洪水毀滅人類的故事。我國各民族中也都流傳有洪水神話。作者在《望川》中,也描述了河水的兩面性。小說對河水的描寫既寫出其美好的一面,也寫出了它丑惡的一面,具有一定的辯證法理念。
水有發怒和失態的時候,那就是洪水的到來。傷疤河發大水的時候,“它粗野、蠻橫和殘暴”“河水渾濁而洶涌”,而且河水還差點吞噬了父親的生命。
連續下了幾天的雨,小河漲水,從上游沖下來很多東西,父親在用鋤頭想撈起水面大木頭的時候,突然被木頭帶走,墜落水中。“我”憑著出色的水性,躍入水中,和驚濤駭浪勇敢搏斗,最后和哥哥楊樹根一起在兇猛的洪水里把父親救上了岸。父親當年在水里救了“我”,如今我也從水里拯救了父親的生命。天地仿佛是一個輪回,父親的善良終于得到了回報。
正如云南大學的張俊福教授所言,“水是一個符號,更是一個坐標,指向人類文明的歷史深處,有待我們去不斷地發掘和探索”[5]。正因為對“水”文化意蘊的解構,楊仕芳在小說中多次運用了水的文化內涵來解讀人生的真諦,寫出了水之頑強、水之毅力、水之美好對主人公“我”的影響,完成了對“我”從出生到成長的心路歷程的探索。“我”在水中再生,在水中探求生命的奧秘。“我”在與水的親近與挑戰中,更加理解了生命的意義,完成了自己人格的升華。
四、結語
水的審美意蘊可以說是一種豐富的文化內涵,從上古神話的洪水故事,到《論語》的“子在川上曰”對水的追問,一直到唐僧出身“江流兒”的傳說,水文化意蘊可謂源遠流長。楊仕芳的小說,就是繼承了傳統的水文化意蘊,通過主人公“我”的人生體驗與感悟,賦予了水多重審美文化內涵。從“我”的出生與重生的過程,賦予了水的護佑生命之美;從“我”對水的靈性的體驗之中,賦予了水與萬物的思辨之美;從“我”對水的溫柔平靜與肆虐泛濫兩面性的思考之中,賦予了水具有的辯證哲理之美。萬物皆有靈,人與萬物和諧共處,物我合一。作家創作師法自然,師法萬物,探索人從萬物中得到的感悟與啟迪,楊仕芳小說《望川》對水文化內涵的探索亦是如此。這種獨特的敘事視角,使作品形成一種唯美的風格,頗有創意,令人耳目一新,愿作家在未來的創作道路上不斷探索,再創更多佳作。
基金項目:桂林師范高等專科學校科研項目“多元文化背景下侗族作家文學創作研究”(項目編號:KYA201801)。
作者簡介:劉麗瓊(1966—),女,壯族,廣西南寧人,文學碩士,桂林師范高等專科學校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為外國文學、地方文化教學及研究。
參考文獻:
〔1〕陸梅華、徐小雅.憂郁的詩意敘事——評楊仕芳小說《望川》[J].文學評論,2019:(5)59.
〔2〕楊仕芳.而黎明將至[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 125-139.
〔3〕三江侗族作家楊仕芳小說集《而黎明將至》出版!全國文學大伽好評如潮![J/OL].https://www.sohu.com/a/252354554_201405.
〔4〕王振星.唐僧“江流兒”身世的原型與流變[J].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3):62.
〔5〕張俊福.水的神話意象研究綜述[J].民族論壇,2015 (1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