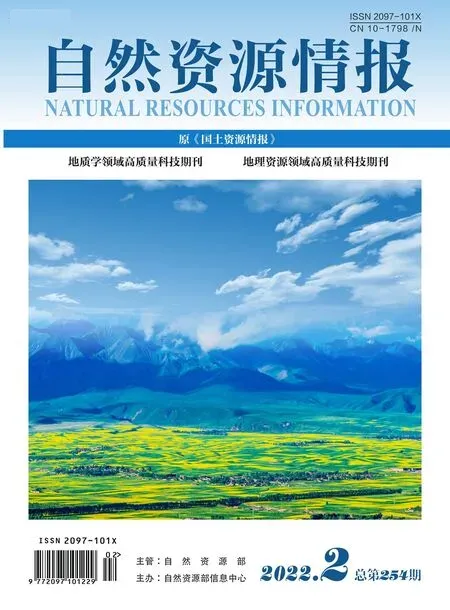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體系
王 晨,闕 翔
(1.福建省地質測繪院,福建 福州 350001;2.福建農林大學 生態與資源統計重點實驗室,福建 福州 350002)
產權是經濟所有制關系的法律表現形式[1],產權制度是自然資源開發利用的基礎性制度[2]。自然資源資產產權是自然資源資產的所有權、用益物權、擔保物權、債權、特許經營權等一系列權利的總稱。目前,我國自然資源資產產權管理依據的法律法規各異、形式多樣化、豐富程度不同[3],同時存在權利體系不完善、權利交叉、公權力與私權利難以平衡等一系列問題。2019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統籌推進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體系和權能,完善自然資源資產產權法律體系”[4]。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體系,是平等保護各類自然資源資產產權主體合法權益的基礎,也是更好地發揮產權制度在生態文明建設中激勵約束作用的關鍵內容。因此,進一步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體系,同時加強實踐,保證能用、可用、管用,成為自然資源產權制度改革的關鍵。
1 自然資源產權體系存在的問題
1.1 自然資源產權立法體系不完善
目前,我國關于自然資源產權的法律體系不夠健全。在土地、海洋、礦產、水、森林等單行法中,雖然分別規定了產權的相關內容,但是沒有統一的自然資源法,且對于濕地產權方面的立法尚存在空白。例如,我國僅對濕地系統內某些資源的權屬進行了規定,且這些規定大多分散于其他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中,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以下簡稱《森林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以下簡稱《野生動物保護法》)、《自然保護區條例》、《水土保持法實施條例》,而未將濕地獨立進行整體性的權屬規定,也未將濕地產權相關內容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下簡稱《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等基本法律中。
在《憲法》《民法典》等上位法中,對于自然資源產權的規定過于概括。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草原法》《森林法》《野生動物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域使用管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島保護法》等自然資源單行法,則側重于自然資源的保護和用途管制。
自然資源相關法律法規之間的概念、邏輯體系與具體規定并不統一。例如,《森林法實施條例》第二條規定:“森林資源,包括森林、林木、林地以及依托森林、林木、林地生存的里生動物、植物和微生物。”這一界定比較寬泛,其與《森林法》第二條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從事森林、林木的保護、培育、利用和森林、林木、林地的經營管理活動,適用本法”的規定不一致。
1.2 現有自然資源產權權能交疊和沖突
由于過去我國長期實行自然資源分部門管理、分門類立法,產生權利交叉重疊、缺位遺漏等問題,導致部分自然資源權利體系不完善、使用權權能不完整或者法律地位不明。例如,土地權利體系中缺少國有農用地使用權等法定權利;探礦權,草原資源的所有權、使用權和承包經營權等是否可以進行抵押在法律上未明確界定。
部分自然資源權利客體復雜,權利之間容易存在交叉重疊。例如水域灘涂養殖的權利與海域使用權、土地承包經營權,取水權與地下水、地熱水、礦泉水采礦權等存在權利交叉等現象。自然資源與一般物不同,部分資源具有重要的生態或其他功能使其同時具有社會公共資源的屬性,一定程度上也屬于公益性財產。但現實中一些自然資源可能在公權與私權之間存在沖突和矛盾。例如,濕地資源、自然保護地等。一方面,濕地生態空間中的灘涂、森林等資源以及自然保護地中的礦產資源等作為私權的客體,權利人有權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對其進行利用或商業化開發,從而實現資源的經濟價值。另一方面,基于公共利益的考慮,需要強調濕地資源等的社會公共資源屬性,維護其固有生態功能,從而實現生態價值。因此,濕地資源或自然保護地的使用權往往受到較大的限制,維護公共利益和尊重私人權利之間難以平衡。另外,自然資源的國家所有權有時也會出現落實不到位,存在“產權虛置”現象,不利于資源保護與合理利用[5]。
2 產權體系構建的建議及相關對策
2.1 健全自然資源產權立法
推動《自然資源法》的立法工作,將濕地資源等生態功能重要的自然資源納入法律保護體系,同時明確產權關系,制定統一的監管保護機制,例如設立管護點,明確管護責任人;構建以自然資源、水利、林業、環保等相關部門為主體的聯合執法機制;加強原始生態保護和生態修復工作等。適時啟動《森林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等法律修改,明確部門之間設定自然資源物權權利邊界,加強部門聯動機制建設,補充完善各類自然資源關于物權方面的規定,不斷豐富用益物權。
2.2 逐步構建自然資源資產產權物權體系
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中,物權分為自物權(所有權)和他物權[6]。自物權,指所有權人對自己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所有權人有權在自己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上設立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自然資源有一定的使用價值,可被人類開發利用,因此,自然資源可納入物權范圍,具有法定性和排他性等物權特征。按照以上思路,將自然資源物權也分為自物權和他物權(表1)。其中,自物權可包括土地所有權、礦產資源所有權以及水流、海域等其他自然資源的所有權。而他物權中的用益物權可包括土地承包經營權、建設用地使用權、探礦權、采礦權等,其擔保物權主要是抵押權。

表1 自然資源資產物權體系
2.3 擴充權利并豐富權能
針對不同的自然資源管理需求,可以相應地通過擴充權利、豐富權能等方式來健全和優化產權體系(表2)。土地資源方面,一是通過落實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農戶的承包權、土地經營權“三權分置”,深入推進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三權分置”[7],及“兩權”抵押試點工作,逐步釋放集體土地上的使用權權能,賦予農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和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融資功能。二是拓展地下空間建設用地使用權,鼓勵各類經營性項目通過招標、拍賣、掛牌等有償使用方式取得地下建設用地使用權,促進空間合理開發利用。礦產資源方面,可將油氣資源的探礦權和采礦權兩權合一,并同時完善采礦權抵押權能。海洋資源方面,構建無居民海島產權體系,豐富無居民海島使用權轉讓、出租等權能及海島使用權抵押權能,豐富海洋資源資產產權類型。水資源方面,需要豐富水能資源開發使用權權能。水能資源開發使用權可以通過有償出讓方式獲得,明確水能資源開發使用權流轉、擔保等法律規定,另外,需要進一步明確養殖權抵押權能。

表2 各類自然資源資產產權體系
2.4 針對生態功能性資源設立地役權
針對在維護公共利益和尊重私人權利之間如何實現平衡的問題上(例如,濕地資源的生態公益性與私人利益性沖突),可通過設立地役權,對土地權利人某些權利進行限制或承擔“容忍”的義務,以實現特定的公共利益,服務于特殊的目的[8]。設置地役權立足于生態功能性資源的私權屬性與生態公益性雙重屬性,堅持公共利益與私權保護并重的原則,在對生態功能性資源權利人給予合理補償的前提下,對其權利及其行使進行必要的限制,將其管理權通過決議和合同形式授權給統一的管理主體,以實現生態功能性資源的生態價值和自然資源的統一高效管理[9]。地役權的設立可有效解決公私利益的沖突,使兩種利益并存。例如,在武夷山國家公園,一是制定生態修復區范圍的集體商品林贖買制度,擴大國有林地面積,實行統一管護;二是在傳統利用區通過協議方式流轉,吸引民營工商資本進行特許經營。除經濟補償措施外,國家公園還可吸收原林權所有者參與保護工作,增加收入,調動保護積極性。
3 結論
綜上所述,構建分類科學合理的自然資源資產產權體系是我國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重要任務,也是促進自然資源在具有清晰完備產權條件下轉換為自然資源資產,實現生態產品價值的基礎。面對目前我國自然資源產權體系不夠健全、用益物權不完整等現象和問題,需要以堅持自然資源資產市場化方向為改革目標,探索所有者權益多種實現方式,促進我國自然資源資產向產權明晰、配置高效等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