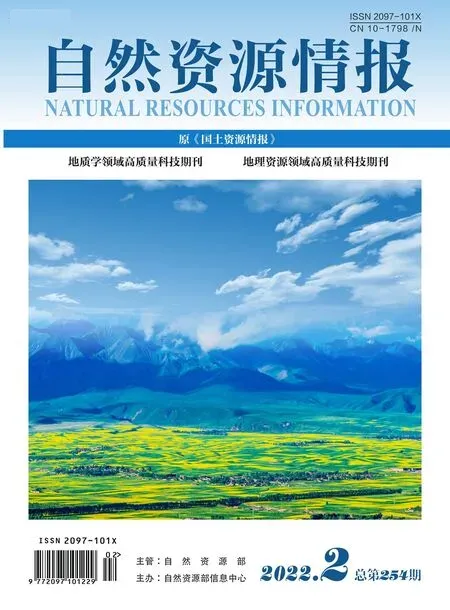黔西南州新型城鎮化發展時空分異
孫紅梅,劉書劍
(1.興義民族師范學院,貴州 興義 562400;2.黔西南州林業局,貴州 興義 562400)
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是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的關鍵舉措。2020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布《2020年新型城鎮化建設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指出,加快實施以促進人的城鎮化為核心、提高質量為導向的新型城鎮化戰略;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新型城鎮化建設,推進城鄉融合發展。如何根據不同地區的實際狀況加以落實,在未來發展中科學實施,是各地區新型城鎮化發展中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對區域的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及時空差異進行分析,有助于掌握其發展進程及存在的問題,有針對性地進行改進。
近年來,學術界對于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及時空分異的研究有以下方面:①從不同空間尺度(國家級、省級、市縣級)對區域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進行評價,探討發展策略[1-4];②對新型城鎮化質量的空間分異及動力機制進行研究,探尋發展路徑[5-6];③從時間序列上,對新型城鎮化系統與其他系統的協調發展、新型城鎮化內部子系統的協調發展的研究[7-8]。從研究的地域范圍來看,經濟區、省級城市群、市域和縣域地區均有涉及,但仍不具有時空普適性的研究方法和策略。本文選取國際山地旅游大會的永久會址和舉辦地貴州省黔西南州為研究對象,從生產、生活、生態三個與城鎮生活密切相關的方面構建新型城鎮化評價指標體系,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分析其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差異,分析其發展特點及存在的問題,為進一步優化新型城鎮化發展策略提供參考。
1 數據與方法
1.1 數據來源
本研究以黔西南州及其下轄的8縣市作為新型城鎮化發展時空分異研究的對象,數據來源于貴州省人民政府網提供的《貴州統計年鑒(2012—2018年)》、貴州省宏觀經濟數據庫、《黔西南州統計年鑒(2012—2018年)》、2018年縣(市)統計年鑒綜合數據、黔西南州及各縣市的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黔西南州人民政府及各職能部門網站。部分缺失數據通過臨近年份指標值擬合、加權平均等方法進行插值補充。
1.2 研究方法
頻度統計法:參考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貴州省新型城鎮化規劃等專項規劃的主要考核指標,以及相關研究成果中的重要指標,利用頻度統計法得出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評價的常用指標集,在此基礎上結合黔西南州實際情況選取評價指標。
熵值法和專家打分法:依據2012—2018年黔西南州各項統計數據,利用熵值法確定指標體系中的各項指標權重,從生產、生活、生態三個維度進行分析,建立黔西南州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對于各縣市的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評價,考慮到各縣市數據的獲取和可比性問題,對縣(市)級指標體系進行進一步調整,并綜合利用熵值法和專家打分法進行權重確定。
對比分析法:分別計算黔西南州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綜合評價值和“生產”“生活”“生態”三個子系統的耦合協調度,從時間維度對比分析不同年份新型城鎮化的發展水平及其子系統的耦合協調情況;以州內各縣市作為橫向對比單元,測度同時期各縣市的新型城鎮化綜合評價值,分析州內新型城鎮化的空間差異和演變格局。
2 結果與分析
2.1 指標體系的構建
新型城鎮化是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是以城鄉統籌、城鄉一體、產業互動、生態宜居、和諧發展為基本特征的城鎮化[9]。本文參考生產、生活、生態“三生”融合理念,結合黔西南州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實際情況,在前期研究與分析的基礎上,對初選的常用指標進行進一步篩選優化,從生產、生活、生態三個關乎“城鎮人”的重要指示系統進行指標選取,利用熵值法確定各項指標權重,建立黔西南州新型城鎮化的評價體系(表1)。

表1 黔西南州州級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

續表
對于各縣市的評價沿用生產、生活、生態的評價系統,考慮數據的可比性及數據的可獲取性,對以上指標體系進行進一步調整,結合熵值法和專家打分法確定各項指標的權重,最終縣市級的評價指標體系如表2所示。

表2 黔西南州縣(市)級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
2.2 新型城鎮化發展時序演變特征
2.2.1 新型城鎮化水平發展
根據以上確定的指標體系計算出黔西南州2012—2018年新型城鎮化綜合指數值,并與同時期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及其子系統的綜合評價值進行對比分析。
從圖1可以看出,2012—2018年黔西南州新型城鎮化整體發展水平雖然較低,但在不斷提高。綜合評價值從2012年的0.0366穩步上升至2018年的0.278,7年間增長了約6.6倍,表明黔西南州新型城鎮化發展狀況良好。其中,2014—2015年綜合水平增幅較大,主要是在《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實施的大背景下,黔西南州啟動了以經常居住地登記為基本形式的“零門檻”城鎮落戶政策,2015年人口城鎮化率有顯著提升(12.76%~40.45%),新型城鎮化綜合指數也隨之上升。

圖1 2012—2018年黔西南州新型城鎮化時序變化
新型城鎮化各子系統的發展態勢不盡相同:生產子系統與生態子系統的整體發展狀態較為相似,生產子系統的綜合指數在2012—2018年保持勻速增長,表明黔西南州的社會經濟發展穩定(圖2)。《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出臺,提出把生態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鎮化進程的發展原則;以達成生態環境明顯改善,空氣質量逐步好轉,飲用水安全得到保障的發展目標。2017年,國務院批復同意《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行動方案》明確強化城市污染治理,推進城市生態修復和綠色建筑、綠色能源的應用為新型城鎮化工作的重點任務。因此,生態子系統的綜合指數在2014—2015、2017—2018年增幅較大,其余時段增長較為平穩。生活子系統的綜合指數在2014—2015年波動較大,主要原因是系統中權重最大的指標(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在2015年增幅較大,帶動生活子系統的綜合指數上升,2016年各項指標增長速度趨于平緩,城鎮人口增長率指標值嚴重下降,生活子系統的綜合指數值也隨之下降。

圖2 2012—2018年黔西南州新型城鎮化各子系統發展時序變化
2.2.2 子系統耦合協調演變
(1)耦合度
耦合度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程度,本文用以度量新型城鎮化系統中生產、生活、生態三個子系統之間的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程度。根據以上黔西南州新型城鎮化的指標體系,其子系統的耦合模型如下:

式中C為系統間的耦合度,P為新型城鎮化的生產子系統綜合水平,L為生活子系統綜合水平,E為生態子系統綜合水平。C的取值范圍為[0,1],C值越接近0,表示系統間的耦合度越低,新型城鎮化各子系統之間趨于無序的影響狀況;C值越接近1,表示各系統間的耦合度越高,各子系統之間越趨于有序的相互作用。借鑒耦合階段的劃分標準[7-8],本文將新型城鎮化各子系統的耦合度大小(即相互作用的大小程度)劃分為無序(C=0)、低水平耦合階段(C∈(0,0.3])、拮抗階段(C∈(0.3,0.5])、磨合階段(C∈(0.5,0.8])、高水平磨合階段(C∈(0.8,1.0))、有序(C=1)6個階段。
(2)耦合協調度
由于耦合度C僅表示新型城鎮化子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強弱,不能反映子系統之間作用的優劣、利弊[8,10]。因此,當新型城鎮化子系統的發展水平同時處于較低水平或者較高水平,均可能出現較高的耦合度[8]。為了避免對低發展水平高耦合狀態的不當評價,特引入耦合協調度模型。協調度是指相互作用中良性耦合程度的大小,體現了協調狀況好壞,可以表征各子系統間是在高水平上相互促進還是低水平上相互制約。其模型為:

式中D為各系統之間的耦合協調度,C為系統間的耦合度,T為耦合協調發展水平的綜合評價指數,α、β、γ取各子系統的綜合權重,即α=0.31,β=0.45,γ=0.24。P為新型城鎮化的生產子系統綜合水平,L為生活子系統綜合水平,E為生態子系統綜合水平。D的取值范圍為[0,1],為了分層分級表示新型城鎮化各子系統間的耦合協調度,參考相關研究成果[11-12],結合各子系統的分析數據,采用等值分隔法來劃分耦合協調度的區間和等級,共分為3大類10個等級(表3)。

表3 耦合協調等級及類型劃分
(3)耦合協調度水平
根據公式1~3計算2012—2018年黔西南州新型城鎮化三個子系統的耦合度及耦合協調度,結果如表4所示。①2012—2018年黔西南州新型城鎮化評價的耦合度值均大于0.9,處于高水平磨合階段,說明各年度各子系統之間的影響程度均較大,呈現強相關狀態。②子系統之間的耦合協調度較低,協調發展水平不高,反映出黔西南州這一時期均處于低發展水平高耦合狀態的偽有序狀態。2012—2014年,耦合協調值均小于0.2,屬于嚴重失調階段;2015—2017年,耦合協調值位于[0.2,0.3)區間,屬于中度失調階段;2018年,為輕度失調。因此,雖然這時期黔西南州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不高,協調水平較低,但是耦合協調度一直穩步升高,各子系統之前的協調水平逐步提升,與新型城鎮化整體水平的發展趨勢一致。

表4 黔西南州新型城鎮化耦合度及耦合協調度時序變化
2.3 新型城鎮化發展空間差異分析
為了更好地揭示出黔西南州各縣(市)新型城鎮化的空間差異和演變格局,本研究將黔西南州下轄的8縣市作為橫向對比單元,通過上述方法得出各縣(市)在2018年的新型城鎮化綜合評價值。為了能夠更為直觀地對比分析新型城鎮化水平的高低層次,本研究將黔西南州各縣(市)的新型城鎮化水平綜合得分,運用自然斷點法(Jenks)劃分為5類(極低、較低、中等、較高、高)。
黔西南州各縣(市)的新型城鎮化水平存在較大差異,興義市作為黔西南州州府所在地,具有地域優勢,其新型城鎮化的水平為全州最高;興義市人均GDP、人均公共財政預算收入、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普通中學在校學生數、居民儲蓄存款余額等反映生產、生活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均為同期全州最高,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比較低,反映出城鄉協調發展狀況良好,其生態環境水平也名列前茅,各子系統間耦合協調水平較高,整體發展態勢較好。其次是興仁市和貞豐縣,興仁市的土地產出率為同時期全州第一,城鎮常住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全州第二,人均GDP為全州第三;貞豐縣第二產業產值占比最高,土地產出率為全州第二,城鄉發展較為協調。普安縣經濟發展、生態環境、人口城鎮化率等均處于中等水平;冊亨縣、望謨縣、晴隆縣處于較低的發展水平,主要是受地理環境的影響,經濟發展受限。根據測評,綜合指數最低的為安龍縣,安龍縣雖然經濟發展水平排名靠前,二三產業從業人員占比為全州最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全州第二,在人口城鎮化方面發展較好;但是其人均GDP、土地產出率、人均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城鄉養老保險參保率等均處于州內較低水平,反映出經濟水平、生活質量、城鄉協調等均還有待進一步提高。
3 結論與討論
根據前期調研發現,黔西南州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較低,且州內差異較大。因此,本文在前期研究的基礎上,對黔西南州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進一步優化,從生產、生活、生態三個方面選取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評價指標,綜合運用熵值法和專家打分法確定各項指標的權重;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測定2012—2018年黔西南州新型城鎮化水平的演變分異。得出以下結論:①2012—2018年黔西南州新型城鎮化整體發展水平在不斷提高。綜合評價值從2012年的0.0366穩步上升至2018年的0.278,7年間增長了約6.6倍,但依然處于較低水平。②新型城鎮化各子系統的發展態勢不盡相同,子系統間耦合度高,耦合協調度較低,協調發展水平不高,但在逐步提升中。③黔西南州各縣(市)的新型城鎮化水平存在較大差異,興義市作為黔西南州州府所在地,具有地域優勢,其新型城鎮化的水平為全州最高;興仁市和貞豐縣發展水平次之;冊亨縣、望謨縣、晴隆縣處于較低的發展水平;安龍縣綜合發展水平最低,發展不均衡,發展效率較低。在后續的新型城鎮化建設中,要進一步發揮好興義在全州城鎮化推進中的龍頭作用,強化興仁、貞豐、安龍城鎮群的體系建設,加快冊亨、望漠、普安、晴隆的互動發展,注重城鄉統籌,促進黔西南州山地特色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的有序發展。
本文雖然對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評價的指標進行了頻度統計分析,從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要求出發,選擇與之息息相關的生產、生活、生態三個方面來進行指標體系的構建。但是,新型城鎮化內涵豐富,不同區域的發展側重不同,且受到數據獲取的限制,本研究沒有將義龍新區作為單獨的橫向對比單元;選取的指標體系依然具有一定的主觀性,尤其是縣(市)級評價指標項選擇較少;利用熵值法確定各項指標的權重與所采樣的指標數據值密切相關,本文選取的是2012—2018年的數據,時間跨度較小,且部分缺失數據通過臨近年份指標值擬合、加權平均等方法進行插值補充,數據呈現的規律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此,評價結果具有一定的時空局限性,對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的評價還有待進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