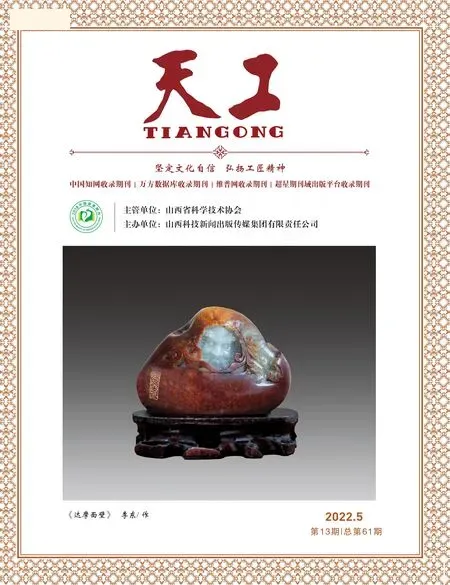唐代善業泥考略及其與藏地擦擦的關系
段立瓊
太原師范學院
一
善業泥又被稱為善業佛,是用模具壓印泥團而成的小泥佛像,是一種佛教藝術珍品。目前對善業泥的研究涉及著錄、考古發現、收藏、制作方式等諸多方面。對善業泥的著錄,最早是由于清代金石學興盛,劉墉之孫劉燕庭在西安慈恩寺偶然得見后被同代學者鮑昌熙摹入《金石屑》一書。據說當時也有善業泥考,可惜后來稿本無存。近人黃浚(字伯川)《尊古齋陶佛留真》一書著錄3品:北魏孝昌元年(525)一品,為方形坐龕式小泥佛;西魏大統八年(542)一品,為扈鄭興所造龕式三佛并坐小泥佛;隋仁壽二年(602)一品,為豎長方形小泥佛,背范文字3行,文曰:“仁壽二年,興福寺造,少陵園下,眇行者一。”1953年,咸陽張底灣北周獨孤信墓出土小泥佛一件。上述諸品,皆有年代,有的還有出土地點。①牛達生:《漢地小泥佛、小泥塔名稱考——兼論“擦擦”名稱》,《尋根》2008年第1期,第89頁。近代對善業泥的研究應當是從陳直開始的。陳直先生在《唐代三泥佛像》一文中指出其認為最常見的三類泥像,并進行一一考釋,“善業泥像”為這三類之中的一類。文中稱:“個人所見唐代泥佛像,不下千余品,而以比丘法律、蘇常侍、善業泥三種泥像,最為代表品。”可知,唐代小泥佛造像大致有三種,第一種為善業泥佛像,大多是用僧人的骨灰和泥壓制而成,為尖拱形,大小不一。正面圖案各不相同,背面都刻有“大唐善業泥,壓得真如妙色身”字樣(如圖1)。陳直先生依字體判斷其年代為初唐時期。第二種為比丘法律泥造像,背面有陽文題記“大唐國至相寺北/比丘律,從永徽元年/已來”(如圖2)。第三種為蘇常侍泥造像,背面刻有陽文題記“印度佛像,大唐/蘇常侍、普同等共作”等字樣(如圖3),這種泥像母本來自印度,可能是玄奘從印度歸來時帶回,因此多有鮮明的印度造像特征。

圖1 唐代善業泥像(正面、背面)

圖2 比丘法律泥造像(正面、背面)

圖3 蘇常侍造印度佛像(正面、背面)
二
目前學界大都把凡是唐代所造的中原地區的小泥佛像全部稱為善業泥。這種稱法并不妥當,是種誤讀。陳直先生最早在《唐代三泥佛像》一文中的說法很嚴謹,當時只是把這些具有代表性的唐代小泥佛進行分類。善業泥指的是那類銘文中有“善業泥”三個字的小泥佛。后來又說:“唐代曾有習俗,僧人圓寂之后,火葬者以骨灰和泥,模制印像,藏之塔中,此即所謂善業泥佛者。”②陳直:《唐代三泥佛像》,《文物》1959年第8期,第86-89頁。金申先生認為因其背后有“善業泥”字樣而得名,所以凡是這種小泥佛像都可被稱為善業泥像。《吉林大學藏善業泥造像及其題讠永冊》③于閏儀:《吉林大學藏善業泥造像及其題讠永冊》,《文博》1990年第1期,第87-89頁。一文介紹吉林大學文物陳列室有一方清代鮑康觀古閣舊藏的善業泥像,鮑康得到這枚造像后,曾精心拓制,請當時的眾多名流題寫詩文。可貴的是該文轉錄了當時題寫的這些詩文,通過考證認為該枚造像與首次被著錄在鮑昌熙《金石屑》中的為同一枚。從各家題詩可以看到在當時人眼中善業泥不再局限于有這三字銘文的小泥佛像,更多是善之作業。其中蔣湘南曰:“七宮善女生天否,大書惟恐泥痕淺。”雁塔是七宮亡者的錢財建的,所以叫善業泥,也是善之作業之意。總之,一種看法是只有背后有“善業泥”銘文的才能被稱為善業泥,另一種是唐代的這一類小泥佛像都可被稱為善業泥像。
造成這種誤讀的原因,筆者認為存在兩種可能:一是因為讀起來順口,這類泥佛更為有名,慢慢地人們就以為善業泥是那一類小泥佛的稱呼,是一種約定俗成的稱謂。二是要從它本身的含義來考慮。“善業”指善之作業,與惡業是相對的,是能帶來美好的一種行為。《瑜伽師地論》卷九十中記:“善業之建立,系依如理作意,如實了知所緣之境,并明其結果。反之,惡業即依邪執著之心,于所緣之境不能如實了知所致。”①參見《佛光大辭典》“善業”條目的解釋。因此,“善業”應是指人的修為,多做善事、積功德。可能有一小類表達同樣意愿的小泥佛,這樣類型的稱之為善業泥也是可以的。但是全部的都用善業泥來命名就不準確了。再從善業泥佛像的銘文來看,“大唐善業泥,壓得真如妙色身”中“真如”指的是永恒的本體或真理。在《大唐西域記》中“妙色身”是指為了撫慰竭誠信佛的人們而現身的觀自在菩薩的身形。在《瑜伽師地論》卷八二中有“妙色身謂三十二大丈夫相八十隨好”②《大正藏經》33-755c。。據此可知,“妙色身”應為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的佛陀優美姿態。因此善業泥應該主要是佛教徒通過善業來修行的一種方式。
三
以下筆者把所有這種形制的佛像稱為小泥佛像或擦擦。其實在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時代,這種小泥佛有不同的叫法。比如在藏地稱其為“擦擦”(如圖4)。關于“擦擦”這一名稱,李翎考證認為其原意應該單指泥做的小塔,不包括泥做的小佛像。最早對擦擦進行系統研究的意大利藏學家圖齊認為tsha-tsha一詞源自梵文,它的意思是完美的形象或復制③[意]圖齊:《梵天佛地(第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33頁。。《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④彭金章、王建軍:《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文物出版社,2004。考古調查清理報告中對其中248個窟的清理情況做了詳細介紹,其中也出土大量小泥佛。在《敦煌卷子》中稱之為“脫佛”“脫塔”。而以外來名稱記載的就更多了,早期大多見于唐代佛教文獻。如“小窣堵婆”“泥制底”“拓模泥像”等,印度稱其為“佛牌”。總之,不論何種叫法其實都是一種物體的不同稱謂。除了制作方法等類似之外,各類小泥佛塔也有很大的不同。

圖4 大安寺沙門空造像(正面、背面)國家博物館/藏
這種小泥佛的制作隨著佛教的東傳流入我國,其在漢地的制作是要比文獻記載早的,應該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期,慢慢引起人們關注才去記錄。“從有關資料看,小泥佛的制作,最早開始于北朝。至唐代脫佛之風日熾,乃是因為唐代初期缺銅,政府實施銅禁,銅料盡用以鑄錢,自六朝以來盛行的銅造像,皆代之以泥質。”⑤陳直:《唐代三泥佛像》,《文物》1959年第8期,第86-89頁。也就是說,最早在6世紀時就有制作小泥佛。這只是我們能看到的,這種泥制佛塔易損壞、難保存,所以應該更早。在義凈《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中云:“歸東印度,到三摩明吒國,國王每于日造拓模泥像十萬軀。”可見印度有制作泥佛的歷史,并且這種做法在當時非常興盛。譚蟬雪在《印沙 脫佛 脫塔》⑥譚蟬雪:《印沙 脫佛 脫塔》,《敦煌研究》1998年第1期。一文中通過文獻結合遺跡非常詳細地考證了這類小的泥制佛像的制作、用途、來源、年代等。其在制作時可能有一定的儀軌,比如手持念珠、誦佛經等。唐代僧人義凈曾去印度求經,返回過程中撰《南海寄歸內法傳》一書記錄其在各地的見聞。據記,西國諸寺有制脫模泥像的傳統,泥像做好后的處理方法有三種:第一種是印于絹紙上,隨時隨地供養;第二種是積少成多后用磚壘起來,做成佛塔;第三種是放置于闊野中,任其消散。普通大眾要以一己之力開鑿佛龕、制造佛像來積功德顯然是比較難實現的,那么制作這樣的小泥佛像就比較容易實現,并且更便于隨時隨地禮拜。“擦擦”一詞最早見諸漢文史籍的是《元史·釋老傳》:“又有作擦擦者,以泥作小浮屠也,或十萬、二十萬以至三十萬。”⑦《元史(卷202)》,列傳第八十。其中的擦擦是從當時的藏語直接音譯過來的。
關于唐代的小泥佛像這種形制的來源,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九云:“印度之法,香沫為泥,作小堵婆,高五六寸,書寫經文,以置其中,謂之法舍利也。數漸盈,精建大堵婆,總聚于內,常修供養。”可以得出這種制作方式應來自印度。漢地小泥佛最早見于6世紀,與隋統一后曾下令復興佛法,天下大肆營造經像、修建佛寺有關。藏地7—9世紀為發祥期,是這類擦擦的初級階段,以佛塔和銘文為主,而早在6世紀的唐代已經跨越初級,直接造泥佛像擦擦,應該是由于玄奘從印度帶回的佛經、佛像可能成為當時人們膜拜的對象,漢族的工匠可能根據當時流行的佛像制作了泥佛模具,這種造像形式在他的感召下更為流行,體現了當時的宗派信仰對佛教的影響。傳播順序可能是佛教傳到漢地,擦擦這種形制隨著佛教的東漸在這里廣為流傳,當漢地擦擦興盛過后開始走向衰退,這時藏地佛教開始興盛,并與當地教派結合呈現出新的面貌,有時甚至能看到中原佛教對藏地的影響。
這些小泥佛從來源看,主要歸為藏傳佛教小泥佛塔和漢傳佛教小泥佛塔兩類,其中有很多不同。在時間上,藏傳擦擦比漢傳擦擦出現得要晚。漢地小泥佛最早出現在6世紀的北魏,而藏傳擦擦最早出現在7—9世紀的吐蕃,比漢地的小泥佛整整晚了一個多世紀。在題材上,藏傳擦擦題材豐富,造像奇特,風格奇異,有佛、菩薩(含度母、觀音)、佛母、護法、高僧大德等,多達數百種,而漢地的小泥佛,沒有超出佛和菩薩、弟子、力士的范圍,僅二三十種。佛教禮拜中最初是建塔供養,后來才有造像供養,藏傳擦擦即體現了這一發展規律,早期擦擦主要是佛塔,后來佛塔、佛像并存,再后來主要是以佛像為主。漢地擦擦則從一開始就主要是佛像為主。在銘文上,藏傳擦擦多寫梵文或藏文的咒語,而漢地擦擦則主要是漢字的發愿文。從造像系統來說,藏地主要流行的是密教,我們平時所說的佛教一般是漢傳佛教,也就是顯教。據李翎在《關于漢地擦擦圖像類型的研究》中考證,漢地擦擦只有一例是體現密教性質的圖像,其余都是顯教的。“藏地擦擦從造型風格上均可品味到西北印度斯瓦特、東北印度帕拉、克什米爾、吉爾吉特當年風格的影子,有些擦擦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原漢地藝術的深刻影響和作用。”①劉棟:《擦擦藏傳佛教模制泥佛像》,天津美術出版社,2000。藏地擦擦多密教造像系統,種類繁多,起初多以佛塔和銘文結合,后來多各類金剛菩薩像和觀音像。而漢地擦擦多表現為佛和菩薩的組合,或者佛、菩薩單尊供養。制作方法上藏地擦擦邊緣都有溢出,而漢地擦擦較為規整,且多經過燒制。從形狀上看,藏地擦擦多為桃形、圓形,而漢地擦擦則是方形或者上圓下方。
擦擦作為佛教造像藝術中獨特的精品,是佛教思想視覺化的表現,是普通民眾傳播佛理和積修功德的寄托,表達了他們樸實的信仰。無論哪種形式都是佛教文化在傳播過程中留給我們的遺珍,具有歷史和審美的雙重價值,極具民俗文化的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