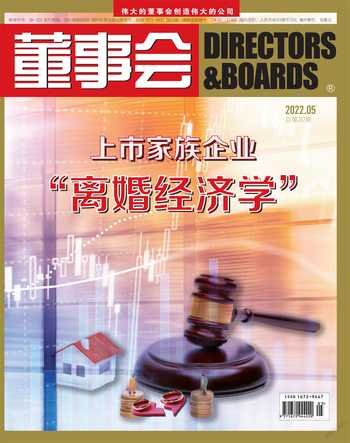變了味的董事會“限選條款”
鄭志剛
根源于西方交錯董事會條款,在中國獨特制度背景下調整變異的限選條款,成為一種加劇股東之間代理沖突,而非形成合理制衡結構的公司“負債”
由第一大股東出于防御目的設置,并對第一大股東的董事會席位形成“偏袒保護”的限選條款,將會強化第一大股東和其他大股東在董事會的權利分配不公,使第一大股東及其委派的董事盤踞在公司內部,獲得超過其責任承擔能力的超額權利成為可能。
起源:交錯董事會制度
在公司治理實踐中,我們通常把上市公司在公司章程中所設置的對董事改選比例或數量做出一定限制的條款稱為“限制董事改選條款”,簡稱為“限選條款”。隨著投資者就法律對投資者權益保護意識的不斷提升,作為“公司憲法”的公司章程自治空間呈現逐步擴大的趨勢。目前,我國上市公司修改公司章程已十分常見,而限選條款的引入是其中最為典型的形式之一。根據我和團隊檢索的公司章程中是否設置了限選條款的結果顯示,在2011年—2019年間,設置限選條款的上市公司樣本數量約占樣本總數的5.55%。
在公司治理制度起源上,限選條款源自在英美等成熟市場經濟國家中上市公司普遍采用的交錯董事會制度。早在1998年,美國就有59%的上市公司設置交錯董事會。交錯董事會的制度設計初衷是維護公司治理穩定性和管理連續性,但在資本市場收購浪潮中逐漸演變為一種常用的反收購機制。通過董事任期交錯設置,交錯董事會使得收購方難以在短時間內獲得充足的董事會席位,由此可以起到延遲甚至阻止控制權發生轉移的作用。
雖然限選條款不會像交錯董事會那樣,形成每年定期更換明確人選董事的嚴格交錯局面,但通過對董事改選施加一定條件的限制,限選條款會改變董事會的人員結構安排,從而直接影響公司股東在董事會的控制權分配。因而,公司股東出于自身在董事會利益的考慮,必然會主動干預(或支持或反對)限選條款的設置。
動機:防御外部接管威脅
上市公司對股東權益的保護,一方面體現在股東可以在股東大會上通過行使表決權,使符合自身利益訴求的議案通過;另一方面體現在股東可以在董事會組織中發揮影響力,使代表自身利益的董事進入董事會。相較其他大股東來說,第一大股東不僅在股東大會事項中享有最大的投票表決權,在公司董事會中一般也占據最多的董事席位而擁有最大的話語權。隨著我國控制權市場的不斷發展和功能完善,發生在資本市場的控制權爭奪事件越來越多,在與敵意收購方為代表的“潛在”股東的“外戰”中,第一大股東出于自身控制權利益的考慮往往成為反收購斗爭的中堅力量。
以深天地A(000023.SZ)為例。2013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新進股東深圳市寶安寶利來實業有限公司連續增持上市公司股份,到2013年年末持股比例達3.24%。雖然并未達到5%的舉牌線,但這對股權質押比例高達96%的第一大股東深圳市東部開發(集團)有限公司的控制權構成威脅。2014年4月召開的董事會會議,隨即通過了關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條款的議案,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增加了“董事會每年更換和改選的董事人數最多為董事會總人數的1/4”的限制董事改選條款。這一議案在隨后召開的該公司2013年年度股東大會上順利通過,第一大股東利用限選條款的植入來防御外部接管威脅的意圖明顯。
理論上,在上市公司設置限選條款之后,即使惡意收購方通過二級市場舉牌等方式實現了上市公司股權層面的控制,受1/3最大改選比例限制等條件的制約,也難以在短時間內對董事會做出實質性改組從而無法掌握董事會的控制權。基于我國上市公司的數據,我們的研究發現,當上市公司面臨的外部收購威脅更大,第一大股東的控制權穩定性更弱時,上市公司設置限選條款的可能性更大。這一定程度表明限選條款成為第一大股東防御外部收購威脅、加強控制權的工具。從實際效果來看,限選條款的設置確實能夠降低上市公司被收購的風險,保護第一大股東在股權層面和董事會層面的控制權。
變異:誘發主要股東“內斗”
限選條款的設置影響股東之間董事會席位的分配,這將反過來影響同樣謀求董事會席位的其他大股東對于第一大股東主導設置限選條款的態度。因而,圍繞限選條款的設置往往引發主要股東之間的“內斗”。
以南玻A(000012.SZ)為例。2015年4月1日,該公司發布公告稱董事會提出公司章程修訂的相關議案。其中,修訂的內容包括在公司章程中增加“董事會每年更換和改選的董事人數不得超過董事會總人數的1/5”這一限制董事改選條款。這一條款遭到了大股東“前海人壽”的強烈反對。前海人壽認為,該條款意味著即使公司董事怠于履職或嚴重損害了公司利益,公司股東也可能無法撤換董事,極端維護現有董事的董事地位以及董事會對公司的控制權,將導致公司股東無法正當行使股東權利、無法正當監督和管理公司的運營發展。最終,限制董事改選條款沒有在股東大會上通過。
由第一大股東出于加強自身控制的目的而在上市公司中主導設置的限選條款,如果處置不當,必將形成對大股東的“偏袒”,甚至導致內部人控制格局的出現。我們的研究發現,限選條款并不能像保護第一大股東及其關聯股東的董事席位那樣,給予其他大股東董事席位同等程度的保護,因而具有明顯的“偏袒保護”特征。在同樣設置了限選條款的情形下,其他大股東委派董事的離職概率是第一大股東及其關聯股東委派董事的兩倍左右。其他大股東往往對第一大股東主導設置的限選條款持反對態度,表現為當存在持股超過5%或10%的其他制衡大股東時,上市公司設置限選條款的可能性更小。
在那些設置“偏袒保護大股東”限選條款的上市公司,第一大股東及其委派的董事在董事會內部形成“盤踞效應”的可能性更大,將會從整體上帶來公司代理成本的增加,使外部分散股東的利益受到損害。
我們從董事的“顯性薪酬”和“隱性薪酬”兩個方面刻畫了限選條款所帶來的代理成本。從“顯性薪酬”的角度看,限選條款的設置使得公司董事獲得超過其應得薪酬的超額薪酬;從“隱性薪酬”的角度看,限選條款的設置導致上市公司在職消費水平顯著提升。“超額薪酬”和“在職消費”成為限選條款扭曲股東董事會席位分配下上市公司不得不承擔的兩種典型的代理成本。根源于西方交錯董事會條款,在中國獨特制度背景下調整變異的限選條款,成為一種加劇股東之間代理沖突,而非形成合理制衡結構的公司“負債”。
規范:遏制內部人控制
為盡可能避免限選條款帶來負面影響,我們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監管當局應規范上市公司限選條款的條款設計和實際運行,鼓勵上市公司提高植入限選條款的表決比例,嚴格植入流程。要嚴格把關限選條款植入流程的規范性,防止第一大股東在限選條款設置的過程中大搞“一言堂”,充分尊重其他股東在限選條款設置這一問題上的不同意見。對于植入限選條款的議案,應當提高通過的表決比例,以維護股東的權利公平,避免限選條款成為個別大股東追求個人私利的工具;
二是,公司內部要對限選條款設置可能引發公司內斗形成預期和警示,避免不必要的沖突。公司的第一大股東和管理層應該意識到,為防止敵意收購而設置的限選條款可能引發其他大股東的不滿,加劇股東之間的利益沖突,最終造成公司整體效率的下降。在運用限選條款防御外部收購威脅時,第一大股東以及管理層應在董事會會議和股東大會上對設置限選條款的目的進行充分說明,做到信息透明;
三是,營造任人唯賢的董事會文化,遏制內部人控制問題。限選條款之所以會強化股東之間的董事會控制權分配不公的局面,從根源上來說,是因為我國很多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內部人控制問題。監管當局應督促上市公司建立權利制衡的股權結構和董事會結構,逐步形成起任人唯賢的董事會文化,讓董事任免結果和董事會人員結構真正反映全體股東的利益訴求。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金融學教授,張浩對本文的寫作亦有貢獻09379C87-2122-40DD-844C-9C183688E4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