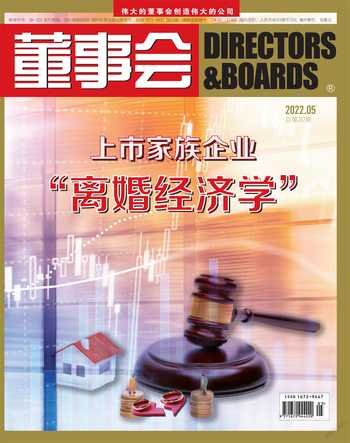謹防國企外部董事成為新“花瓶”
馬傳剛
在不少人眼里,獨立董事是花瓶,其既不獨立又不“懂事”,中看不中用,基本上是個擺設。獨立董事作為外部董事的一種,也可以稱之為外部非獨立董事,一般只設立于上市公司之中。在非上市公司特別是國有獨資、全資公司中,通常不設獨立董事,而是設立外部董事,由于外部董事多由出資人委派或聘請,可以稱之為外部非獨立董事。
早在2017年4月,有關部門就要求在國有獨資、全資公司中建立外部董事制度,體現在《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完善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指導意見》之中。《指導意見》明確提出,到2020年,國有獨資、全資公司全面建立外部董事占多數的董事會,建立完善外部董事選聘和管理制度,嚴格資格認定和考試考察程序,拓寬外部董事來源渠道,擴大專職外部董事隊伍,選聘一批現職國有企業負責人轉任專職外部董事。
然而,到了2020年,除了中央企業和部分省、市屬企業外,大多數國有企業不僅沒有完成《指導意見》布置的外部董事占多數的任務,甚至連外部董事制度都沒建立起來。所以,2020年6月有關部門在《國企改革三年行動方案(2020-2022年)》中再次強調,國有企業要建立“外大于內”的董事會,并要求在2022年底完成這一改革目標。
自2020年下半年開始,在全國各地國資系統中,外部董事制度建設速度加快。經過近兩年的推進,截至目前,不少地方宣布提前實現了“外大于內”的董事會改革目標。這當然是一件好事,外部董事制度的建立,對于完善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規范董事會運作以及防止內部人控制具有重大意義。
然而,從一些地方的實踐看,外部董事制度與獨立董事制度一樣,在具體實施過程中與制度制定時的初衷似有偏離,名不副實、貌合神離的現象較為突出,在有些地區和企業,外部董事越來越有點像獨立董事,漸有成為企業新花瓶的傾向。
近年來,一些地方和企業在選聘外部董事時,往往把人選范圍局限于較小區域、較小范圍內。
有的區縣把外部董事遴選范圍限制在本轄區內,比如淄博市的桓臺、高青、沂源、周村等區縣,在選聘外部董事公告里,明確規定只面向本區縣選聘,甚至要求報名時提供戶口本,以便“驗明正身”。
有的地市僅允許本市范圍內的人員報名,比如福州、淄博、泉州、河池等地,將人選征集范圍限制為市內的企事業單位、科研院所、中介機構等人員。
有的地方要求,只有國有企事業單位的人員才能參選,比如,宜昌市點軍區僅面向區內行政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遴選外部董事。
有的地方國資監管機構按照交叉任職的原則,將監管企業的一批財務總監分別委派到其它監管企業擔任外部董事,形成了甲企業的財務總監兼任乙企業的外部董事、乙企業的財務總監兼任丙企業的外部董事這種橫向任職的局面。
有的國有企業把人選范圍限制在本企業系統內,一般由母公司的管理人員擔任下屬出資企業的外部董事,形成了管理人員在母子公司縱向任職的現象。
外部性是外部董事的根本特征,外部董事來源于任職企業之外,這是最起碼的要求。若據此把外部董事人選限定于所任職企業之外的一個較小區域、較小系統范圍之內,其實是對外部董事外部性的誤解。這種誤解,不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部董事人選的數量和質量(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由于報名人數太少不得不取消選聘或延長報名期限),而且會導致許多優秀的外部董事人選無法參與其中,削弱了外部董事的外部性。
因此,對外部董事人選的征集最好能夠超越區域、系統限制,做到五湖四海、四面八方,不受區域、單位性質、職業的限制,只要其有能力、水平、時間和精力履職,就是優秀的人選,就可以選聘使用。
與獨立董事獨立于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相比,外部董事沒有獨立性,其與控股股東、出資人關系密切。外部董事履職時必須充分理解出資人意圖,維護出資人利益。但是,外部董事在行使董事表決權時,與獨立董事一樣,擁有獨立性,即獨立地行使表決權。
外部董事在董事會會議中的履職機制是:集體討論、獨立表決、個人擔責。集體討論就是與會董事在討論議案時,分別地、充分地發表個人意見;獨立表決就是董事基于個人判斷,對議案投出同意、反對或棄權票;個人擔責就是,董事個人對表決產生的結果承擔責任。
然而,有的國資監管機構或出資人要求,在董事會召開之前,外部董事必須把議案的審議意見、擬投同意、反對或棄權票的情況,事先報送出資人,由出資人審核無異議后,由外部董事在董事會上表達,若與出資人的意見相左,則須按出資人的意見辦理。這樣的要求,一方面妨礙了外部董事獨立行使表決權,侵害了董事權利;另一方面,當已表決事項在后來執行過程中出現了問題,需要問責的時候,由于外部董事的表決意見事先經過出資人同意,因而將會導致外部董事責任界限模糊、追責困難的問題,因為外部董事可以以該表決意見經過了出資人審核通過為由主張免責。
所以,出資人對外部董事在董事會上行使董事權利設置前置程序,破壞了外部董事在董事會會議中的履職機制,進而削弱了外部董事的表決權。
董事須對自己的履職行為承擔責任,且不以是否取得報酬或報酬高低作為前提,只要董事的履職行為給投資者或其他利益相關人造成了損失,就要承擔賠償責任。比如,針對康美藥業因虛假陳述侵害投資者利益事件,法院判決康美藥業時任董事、獨立董事承擔巨額賠償責任。
盡管如此,支付董事一定的履職報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對沖董事責任、提醒董事履行義務的作用。因此,出資人或任職企業一般都給董事支付一定的報酬。就上市公司而言,獨立董事基本上都能夠從上市公司獲取履職報酬,只不過報酬水平相對偏低,而未取得報酬的獨立董事少之又少。
國企外部董事與上市公司獨立董事有所不同,其類型多樣。從履職時間要求上來劃分,包括專職外部董事和兼職外部董事,兼職外部董事又包括市場化選聘的外部董事、橫向交叉任職的外部董事和縱向交叉任職的外部董事。
專職外部董事均能夠獲取董事履職薪酬,因為專職外部董事一部分來源于市場化選聘,若不支付報酬則選不到人,比如,湖南省國資委去年就高薪選聘了約10名專職外部董事;另一部分是現職領導人員轉崗,報酬也就隨著轉崗而轉過來了,比如,中央企業外部董事基本上就是這個模式。
兼職外部董事則不同,市場化選聘的外部董事一般都取得外部董事報酬,盡管報酬水平不高,一般是3萬-5萬元,也有部分地方支付的報酬水平高些。不過也有例外,比如內蒙古烏海市外部董事管理制度規定,兼職外部董事只領取會議津貼,不得在任職企業獲得任何形式的其他報酬。
橫向交叉任職的外部董事一般沒有履職報酬及會議津貼。比如,江蘇省鹽城市、遼寧省營口市均規定,橫向交叉任職的外部董事不領取任何履職報酬和會議津貼。
縱向交叉任職的外部董事一般也沒有履職報酬,即使有會議津貼,由于考慮到廉政建設的原因,外部董事一般也未領取。比如,國有獨資公司湖北聯投集團向控股上市公司東湖高新委派的兼職外部董事均未取得報酬;再比如,國有獨資公司湖北宏泰集團向控股上市公司萬潤科技委派的兼職外部董事既未取得報酬,也未領取按規定可以領取的會議津貼。
兼職外部董事報酬較低甚至沒有報酬,一方面違背了董事權責利相一致的基本原則,與董事職責和義務不相匹配,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外部董事對公司的忠實義務的履行。
綜合分析各地國資系統公開披露的信息,除極少數地方以市場化的方式選聘了專職外部董事外,專職外部董事的來源主要是現職轉崗。
國務院國資委公開披露的信息顯示,新任外部董事(含專職外部董事)之前的身份基本上是中央企業負責人。
比如,已經“出事”的中央企業原專職外部董事丁榮祥、姜林奎以及沈殿成等三人,他們在擔任專職外部董事之前,分別是南光集團副董事長、哈爾濱投資集團副總經理、中石油副總經理。再比如,今年3月,國務院國資委新聘任了6名外部董事,其中至少5名是從現職轉崗過來的。
現職轉崗方式不僅在中央企業比較普遍,在地方國企中同樣比較流行。
比如,2021年11月出事的專職外部董事段文泉,2022年4月7日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的陳文山,他倆都屬于現職轉崗。段文泉轉崗前擔任的職務是云南能源集團董事長,陳文山擔任外部董事之前的最后職務是云南建投集團董事長。再比如,內蒙古國資委披露的信息顯示,去年11月,國資委新聘任的11名外部董事絕大多數都是由區屬國企負責人轉崗而來。
因此可以說,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現職轉崗方式已成為外部董事人選的主要來源渠道。
不可否認,企業現職領導人員轉任外部董事時,年齡偏大,普遍接近60周歲的退休年齡上限。在外部董事崗位上,基本上是他們職業生涯的最后一站,多數人連一屆都沒干滿就被免職退休了。反之,由外部董事再轉崗到企業領導人員職位的人,非常少見。
現職轉崗的外部董事普遍沒有按照任期制進行履職。根據《公司法》的規定,董事任期由公司章程規定,但每屆任期不得超過三年,但通常都是三年一屆。實際上,外部董事的到任,與公司董事會換屆的時間節點基本上不同步,多是隨缺隨補,任期經常跨屆或未屆滿。另外,外部董事的離任與換屆也不同步,基本上是到齡就免職、退休。
企業負責人轉崗擔任外部董事,基本上是退休之前的過渡性安排,既然外部董事到齡退休的預期沒有變化,外部董事持有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心理也不難理解。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外部董事對公司的勤勉義務的履行。
關于外部董事的履職要求,無論任職于省屬、市屬還是區屬企業,無論任職于特大型、大型、中型還是小型企業,各個地方的國資監管機構規定的標準基本雷同,并且主要表現在履職總時間和出席董事會會議次數占比兩個方面。
綜合各地的管理制度發現,對于專職外部董事的履職要求一般是,一個工作年度內在同一任職企業履職時間不少于60個工作日,出席董事會會議的次數不少于總數的四分之三;對于兼職外部董事的履職要求一般是,一個工作年度內在同一任職企業履職時間不少于30個工作日,出席董事會會議的次數也是不少于總數的四分之三。
實際上,企業有大有小,有好有差,產業不同,行業有異。因此,應該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根據企業的實際情況來明確外部董事的履職要求,不能主觀地進行一刀切,否則,外部董事的履職很容易是走馬觀花,陷入形式主義。
總之,國有企業外部董事制度建設目前仍屬于探索發展階段。外部董事制度的執行應堅持市場化方向,從外部董事遴選、聘任、職責、薪酬、考核、評價、退出等各個方面不斷予以完善。要通過外部董事制度的實施,真正達到制衡內部人控制、規范董事會運作、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實現企業高質量發展的目的,從而使得外部董事制度真正成為推動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重要抓手。否則的話,在不少人眼里,外部董事可能就是繼獨立董事之后的又一個花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