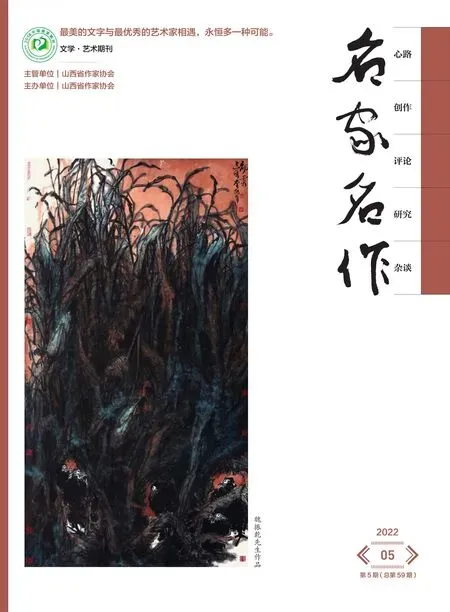遵義赤水“媲美羊碑”碑主考釋
郜 寧
碑刻作為一種無聲的文字載體,具有極高的歷史文化價值,通過對碑刻的釋讀,可以學到很多文化知識,而這一切都基于正確解讀碑刻內容。正確釋讀碑刻內容,必須嚴格遵守其客觀真實性,才能予以正確釋讀。在復雜的碑刻材料中,重要的是主碑內容,其是整個碑刻材料的頭腦,而碑主的身份信息更是重中之重,堪稱整個碑刻材料的靈魂。在貴州省遵義市赤水市大同鎮天橋村,矗立著一塊“媲美羊碑”,歷經歲月的侵蝕,字跡斑駁,通過可辨的、有限的文字信息,嘗試對其碑主身份進行考釋,以求證于諸位方家。
一、何謂“媲美羊碑”
“媲美羊碑”,顧名思義,就是可以跟羊碑相提并論,故首先應當知曉“羊碑”為何。“羊碑”全名“羊公碑”,又名“墮淚碑”,位于湖北省襄陽市的峴山上,是當地人民懷念西晉著名政治家、軍事家羊祜所建立的。碑文字里行間都對羊祜進行了歌頌和贊美,是為頌德碑無疑。
“媲美羊碑”位于貴州省遵義市赤水市大同鎮天橋村南,坐南朝北,其所立年代為清光緒十六年(1890),因其陰面碑額題有“媲美羊碑”而得名。碑2.5平方米見方,為三門四柱結構,碑寬2.68米、通高4.41米、厚0.43米,碑座長3.26米、寬0.72米、高0.26米。碑體整體由紅褐色砂石建成。碑兩面有字,陽面頂額題名“紫馬雙旌”,上部兩旁橫額分別為“邱泰”和“召棠”,內聯為“兩個好使君間歲蒲革便遠,一般賢太守何年竹馬遙迎”。主碑題道:“郡侯星閣劉鏡秋陳公大人去思碑”,外聯為“事業直參循吏傳,勛名無添大夫官”。陽面其余內容難以辨識。碑的陰面頂額題名為“媲美羊碑”,對聯為“閣郡自今蒙樂利,居民那復惜錙銖”。陰面其余內容難以辨識,碑文均用楷體,據可辨識內容,此石碑屬于頌德碑。
二、碑主考釋
此石碑在全國文物第二次普查中被首次發現,并被命名為“劉鏡秋碑”,而在全國文物第三次普查中被更名為“羊碑”,足見對于此石碑為誰所立并無定論,此石碑陰面題“媲美羊碑”,所以所頌之人當為德高望重之人,但是想要解開這個謎團,還要回到石碑本身上來。
主碑中間題“郡侯星閣劉鏡秋陳公大人去思碑”14個字,其中上方“郡侯”2個字為共享,右側“星閣劉”和左側“鏡秋陳”為并列對應,下方“公大人去思碑”6個字為共享。上方“郡侯”容易理解,“郡侯”為兩晉時期官員稱呼,相當于明清時期的太守一職,這也與對聯中的“賢太守”相呼應。分歧主要為右側“星閣劉”和左側“鏡秋陳”,如果與上面“郡侯”及下面“公大人去思碑”放一起解釋,則為“郡侯星閣劉鏡秋、陳公大人去思碑”,這樣會造成歧義。首先,“星閣”作何解釋?查閱相關資料,并無關于“星閣”的記載和解釋,即便“星閣”是未被記載或已經不用的地名,那么與上面的“郡侯”二字也并不銜接,故將“星閣”作為地名解釋并不合適。“星閣”二字是否可以解釋為“郡侯”下面的屬官呢?若如此,“星閣”與“鏡秋”便成了對應關系,即“星閣”與“鏡秋”屬性一致或相近,均為“郡侯”下面的屬官,但是查閱相關資料,并無“星閣”與“鏡秋”作為官職的解釋,即便有所未查,但是根據對聯中的“兩個好使君間歲蒲革便遠”,可知劉、陳二位大人離任時間為“間歲”,因此,不會出現“星閣”與“鏡秋”作為官職名稱在歷史變遷中發生變化的現象,故將“星閣”與“鏡秋”作為劉、陳二位大人官職的解釋也是行不通的。如若將劉姓大人的名字解讀為“劉鏡秋”,那么陳大人的名字直接消失,以“陳公”一筆帶過,而“公”本為共享,此時上承“劉鏡秋”也并不合適。
綜上,將“星閣”和“鏡秋”作為地名或者官職解釋均不合適,那么似乎將二者作為劉、陳二位大人的名字解釋就成了較為合理的解釋。將“星閣”和“鏡秋”與“劉、陳”倒過來解釋,“星閣”對應劉姓大人,而“鏡秋”對應陳姓大人,即劉、陳二位大人分別叫劉星閣和陳鏡秋。事實上,在古代碑刻中,將姓與名顛倒過來的現象并不少見,如位于貴州省六盤水市盤縣板橋鎮小海子村的“鄭廷翰誥封碑(清光緒二十一年〈1885〉)”,主碑題道:“皇清誥封恭人晉封宜人鄭母氏周”,將鄭廷翰的母親的姓氏顛倒過來,由“周氏”題為“氏周”,由此可見一斑。又位于貴州省遵義市赤水市長期鎮華陽村的“廖袁氏墓碑”中題道:“氏囗、氏囗、氏囗、氏囗”和“氏囗、氏陳、氏劉、氏囗”。再如,位于貴州省遵義市赤水市長期鎮華陽村的“楊奇椇墓碑(清光緒十三年〈1887〉)”中題道:“皇清例贈登仕郎故顯考諱奇椇楊公老大人之墓”和“氏囗、氏袁、氏胡、氏囗”。上述碑刻都是清朝時期遵義市的碑刻,與“媲美羊碑”存在時空重疊,可見在當時當地,將姓和氏顛倒過來的現象并不少見。故此石碑當為紀念劉星閣和陳鏡秋兩位大人所立。
然查閱正史、野史和方志等各類資料,并未找到有關劉星閣和陳鏡秋兩位大人的任何信息,作為“媲美羊碑”的兩位碑主,自當青史留名,緣何并無任何信息流傳下來?至此,一個大膽的假設在腦中出現:“星閣”和“鏡秋”并不是劉星閣和陳鏡秋大人的正式名字,而應當是兩位大人的字或者號。循著這個思路繼續查閱正史、野史和方志等資料,果然有所得:“劉啟瑞,字星閣,湖南湘潭甲子科舉人。光緒六年(1880)到任,八年(1882),調羅斛廳,九年(1883)二月復任,時廳中寒士入學,所需教官紅銀,廩保贄見,必先交關清楚乃得覆試。事后措辦多所困難,而教官廩保屢問無償,至于押追。星閣睹此情形,乃集三里首事商議,提撥各廟公款,又倡捐俸銀百兩,并募捐得千數百兩,置買田地,年租即作紅銀贄儀規費,至今寒士德之。”(《仁懷廳志》)又“陳沄,字鏡秋,四川筠連監生。光緒十四年(1888)署仁懷廳同知。到任,因見三里地方糧務,由書役專主作弊,或浮收,或勒派,以致良民受害。又或以厘毫小數積欠,限內故為寬縱,限滿請官差提籍以勒索,必償欲壑而后已。鏡秋察其弊,申明各憲,厘定章程,較前民間約輸一半,當時士民頌聲載道。又值買街房地基,興修考棚,兩廊暨鼓樓龍門等,規模始見完具,置備號棹,生章便之。”(《仁懷廳志》)“先任印江,惠政尤多,后升思南府。”(《印江冊報》)
由上述可知,劉啟瑞(字星閣)和陳沄(字鏡秋)的生平事跡諸多重疊,二人于光緒年間都在仁懷廳任職,整頓三里地方事務,資助寒門士子、減免百姓賦稅等,得到當地士子和百姓的擁護和愛戴,故當他們離任時,當地的士子和百姓出資為他們立功德碑。主碑中間緣何出現“有字無名姓在尾”的現象,需要進行進一步的考釋,方能自證其說。
三、“有字無名姓在尾”試析
縱觀此石碑主碑,可發現此石碑中間出現了“有字無名姓在尾”的現象,緣何造成這種現象需從主客觀層面進行分析。
(一)客觀原因:失誤說
碑刻被雕刻完成是一個純手工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失誤是無法避免的,因此,在不影響表意的前提下,雕刻者可能會將錯就錯。例如,遵義市盤縣的“鄭廷翰誥封碑”所題“皇清誥封恭人晉封宜人鄭母氏周”中的“氏周”可能是由失誤造成的,正確的就應該是“周氏”。但是在另外幾通碑中,卻否定了這種可能。在遵義市赤水市的“楊奇椇墓碑(清光緒十三年〈1887〉)”中題道:“氏囗、氏袁、氏胡、氏囗”,四個“氏某”接連出現,此時若還用失誤來解釋顯然是缺乏足夠的說服力的;再同樣位于遵義市赤水市的“廖袁氏墓碑”中題道:“氏囗、氏囗、氏囗、氏囗”和“氏囗、氏陳、氏劉、氏囗”,連續八個“氏某”的出現,直接就將失誤造成的這種說法推翻。另“楊奇椇墓碑(清光緒十三年〈1887〉)”中的“皇清例贈登仕郎故顯考諱奇椇楊公老大人之墓”與此石碑中的“郡侯星閣劉鏡秋陳公大人去思碑”有異曲同工之處:“皇清例贈登仕郎故顯考諱”交代了碑主的身份,這與此石碑中的“郡侯”的地位屬性是一致的,下面的“奇椇”與此石碑中的“星閣”和“鏡秋”的地位屬性是一致的,最后的“楊公老大人之墓”與“公大人去思碑”的地位屬性也是一致的。綜上,通過對兩通石碑主碑內容的解構分析和解讀可以得知,從客觀層面上用筆誤造成順序顛倒未免武斷,其主觀原因的影響不容忽視。
(二)主觀原因:中國古代稱謂禮制的影響
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中國以禮儀之邦享譽世界,中國古代的封建禮制更是影響深遠,關乎此石碑出現“有字無名姓在尾”現象主要與中國古代的稱謂禮制密切相關。
1.“有字無名”
上述考釋了此石碑上當為劉、陳二位大人的字,而非二者的名,緣何會出現“有字無名”的現象,此處認為原因有二。
其一,“字德名諱”的傳統影響。“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為孫氏。”作為世界禮儀之邦,中國古代的稱謂禮制也是一門學問,在中國古代,“名”是一個人的標志符號,經常和“諱”連用,就成了名諱,除了耳熟能詳的避(皇帝的)諱之外,在古代碑刻,尤其是在墓碑中較為常見,例如上文中提到的“楊奇椇墓碑”主碑題道:“皇清例贈登仕郎故顯考諱奇椇楊公老大人之墓”,其中的“諱”字包含著對逝者的尊重,這是中國古代死者為大觀念的產物。回到此碑刻上來,此石碑為去思碑,不同于墓碑,如果采用墓碑那套名諱的說法,明顯是對劉、陳二位大人的褻瀆,和感恩戴德就無半點干系,故此石碑不能如此。另外,“字以表德”正好滿足此石碑的應用目的,就是感念劉、陳二位大人的恩德,故此石碑采用“有字無名”的形式寄托了對劉、陳二位大人的感念。
其二,“字尊名卑”的主客體限制。“名者,己之所以事尊,尊者所以命己;字則己之所以接卑,卑者所以稱己。”劉、陳二位大人位居高官,相較于為他們立碑的士子和百姓而言,明顯屬于尊者,處于卑者地位的士子和百姓們為劉、陳二位大人豎立紀念碑,是為了表達對劉、陳二位大人的尊敬和愛戴,以劉、陳二位大人的字代替二位大人的名,是在刻意地表達對劉、陳二位大人的尊敬、愛戴和思念之情。如若換做二位大人的名諱,難免有輕薄之意。這也與中國稱謂傳統相互對應:“即敬稱、尊稱、下對上稱字,自稱、謙稱、上對下稱名。平輩之間一般都稱字,只有在很熟悉的朋友之間才稱名,否則‘指名道姓’‘直呼其名’,則是不尊重對方的無禮行為。”為劉、陳二位大人立碑本是為了歌頌兩位大人的事跡,斷然不會在稱謂禮制上出現問題,不會言及二位大人的名諱,以“字”代“名”無疑是兩全其美的選擇。
2.“姓在尾”
此石碑將劉、陳二位大人的“姓”置于“字”之后,造成了釋讀石碑的困難,“姓在尾”現象的出現應當是以下原因。
其一,“氏尊姓卑”的傳統使然。中國是禮儀之邦,對于姓氏文化也很重視,中國古代有“男人稱氏,女人稱姓”的傳統,《通志·氏族略序》:“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男人稱氏,女人稱姓,在古代男尊女卑的社會背景下,可知男人所稱的“氏”,比女人所稱的“姓”要高貴得多。“古代貴族標志宗族系統的稱號。上古時代,氏是姓的支系,用以區別子孫之所由出生。”從中可以看出,“氏”代表了尊貴的地位,而“姓”只是代表血統的一個參照物,“標志家族的字。如:姓名;貴姓。《說文·女部》:‘姓,人所生也。’《玉篇·女部》:‘姓,姓氏’。《詩·唐風·秋杜》:‘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毛傳:‘同姓,同祖也。’”從上述可以看出,“氏”是身份和地位尊貴的象征,這與古代社會男性為主導的事實相對應。而“姓”則象征屬于某個家族,有從屬的意味,這也與古代社會女性悲慘的身份境遇相對應。上面提到,“氏”比“姓”重要,那么出現將“某氏”改為“氏某”的現象便不難理解了,“氏”在“姓”前,可能就是為了突出女子相較于男子而言的從屬地位,這應該是雕刻者刻意為之。以此類推,在遵義赤水的“媲美羊碑”中的“郡侯星閣劉鏡秋陳公大人去思碑”,應該是當作“氏”的“星閣”二字放在了作為“姓”的“劉”字前面,正確解讀順序當為“劉星閣”;同理,“陳鏡秋”亦然。碑刻上出現順序顛倒,當為刻碑者有較強的男尊女卑意識使然。
其二,尊者為“某公”的俗稱。“公”是“對人(特指對老年男子)的尊稱”。相較于同樣可以表示尊貴的“大人”而言,“公”字更顯官方,更能突出人的尊貴地位。如若按照正常順序,則“公”上承“劉星閣”和“陳鏡秋”,成了“劉星閣公”和“陳鏡秋公”,這顯然不符合中國稱“某公”的歷史文化傳統,故顛倒正常順序,以達一舉兩得的目的。此外,“公”“后泛稱朝中職高掌權者”。劉、陳二位大人作為為官一任的地方大員,在當地士子和百姓眼中自然屬于朝廷中職高掌權者,因此被稱為“某公”也是合乎古代禮制的稱呼傳統。
四、小結
“媲美羊碑”的發現,說明中原文化對貴州地區的滲透,通過對其碑主進行考釋,可以彌補當地歷史研究的空白。作為出土文獻,借助傳世文獻進行考釋,是“二重證據法”的體現,也為碑刻的釋讀提供了新的思路。中國傳統的稱謂禮制,為考釋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撐,為研究中國古代稱謂禮制也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