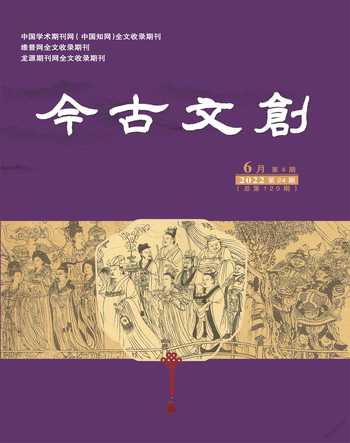孟子革命論再研究
【摘要】圍繞著孟子是否贊成人民擁有打倒暴君的革命權利,學術界一直有兩種不同的觀點。這是孟子革命論再研究的出發點。通過進一步的研究可知:盡管孟子十分同情暴政壓迫下的人民,也十分痛恨暴君污吏,但是他并不贊同人民發動革命,使用暴力反抗暴政。其主要原因在于他認為人民道德素質低下,沒有政治智慧,他們無法合理地使用暴力,難以保證革命的正義性,人民革命只會導致以暴易暴。孟子主張只有道德和智慧超越常人的圣人才有資格發動革命。不過,孟子并不主張人民一味地忍受暴政,他認為人民可以采取遷徙等非暴力的方式反抗暴政,使暴君陷入孤立之中。
【關鍵詞】孟子;反抗權;暴政;革命
【中圖分類號】B222?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2)24-0049-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24.015
基金項目:肇慶學院2018年科研基金項目“關于荀子革命觀爭論的研究”(項目編號:201837);肇慶學院2018年在線開放課程項目“中國哲學與文化”(項目編號:zlgc201811)。
一、孟子革命論再研究的必要性
學界在20世紀20年代以來的孟子革命論研究中形成了兩種不同的觀點。一些學者認為孟子主張人民在遭受暴君的統治時可以揭竿而起,通過暴力革命推翻暴君的統治。他們認為孟子主張人民擁有革命的權利,這是人民反抗暴政的利器。這種觀點可以稱為“孟子人民革命論”。梁啟超、馮友蘭等人持這種觀點。另外一些學者則認為孟子并不主張人民擁有打倒暴君的革命權利。在他們看來,孟子認為只有湯武那樣的圣人才有權利發動革命,利用武力鏟除暴君。人民在暴君統治下只能忍受,等待圣人的解救。這種觀點可以稱為“孟子圣人革命論”。蕭公權、張分田等人持此種觀點。這個分歧從民國時期一直延續至今,因此有必要進一步研究孟子革命論,厘清孟子的人民反抗權思想。
梁啟超在1922年寫出了《先秦政治思想史》,這本著作可以稱得上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開山之作。梁啟超在這本書中提出孟子等人“主張革命為人民正當權利” [1]。他的根據在于孟子等人都信奉民本思想。民本思想的核心觀點是立君為民,君主必須對人民負責,造福于民。否則,君主就將失去統治人民的資格和正當性。梁啟超據此推論,孟子等人自然會贊同人民有權利發動革命,打倒禍害人民的暴君。在書中,梁啟超當然沒有忘記引用孟子和齊宣王那段關于湯武革命的著名對話來佐證自己的觀點。這段對話的內容是:“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于傳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他認為這段對話明確無誤地宣示了孟子的革命觀。這就是“孟子人民革命論”的由來。后來主張“孟子人民革命論”的學者基本上沿襲了梁啟超的論證思路,那段對話也多次被用來證明孟子主張人民有革命的權利。他們大都對“孟子人民革命論”做出了積極的評價,認為這體現了孟子思想的民主性和人民性。例如,馮友蘭說:孟子“肯定了被統治者的革命權。這在后來的中國封建社會中,對統治者起了一定的制約作用。在革命中起鼓舞的作用。”[2]
蕭公權在20世紀40年代初寫出了《中國政治思想史》。在這本名著中他提出孟子主張“暴君必待天吏而后可誅,則人民除取不親上死長之消極抵抗以外,并無以革命傾暴政之權利。”[3]蕭公權認為孟子并不主張人民擁有革命的權利,暴君統治下的人民要等待“天吏”來解救。這對梁啟超的觀點構成了強有力的挑戰。蕭公權所說的“暴君必待天吏而后可誅”源自《孟子·公孫丑下》的一段對話。在這段對話中,孟子提出對于那些殘害人民的暴君“為天吏,則可以伐之。”(《孟子·公孫丑下》)討伐暴君,發動革命是“天吏”才能享有的權利。那么“天吏”究竟是什么樣的人?孟子說:“尊賢使能,俊杰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愿藏于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愿耕于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愿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于天下。無敵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公孫丑上》)“天吏”有著高尚的道德品質和卓越的政治才華,他們一方面能夠尊賢使能,使天下的士人都愿意為其效勞;另一方面能夠輕徭薄賦,使天下的民眾都擁戴他們。因此“天吏”絕不是普通的人民。孟子所說的“天吏”就是能讓天下的人民和士人都心悅誠服的圣人。儒家推崇的圣人有著超越常人的道德和智慧,這樣的人寥若晨星。因此在孟子思想中,革命的權利只能屬于圣人,不可能屬于一般人民。暴政之下受苦受難的人民只能期盼圣人來解救他們于水深火熱之中。這就是“孟子圣人革命論”的由來。后來主張“孟子圣人革命論”的一些學者在蕭公權論證的基礎上又增添了一些新的論據。他們對孟子革命論的評價自然和梁啟超等人不同。這里舉出一例,張分田說:孟子的革命論奪去了“蕓蕓眾生革命的權利。”[4]其最終目的是鞏固君主的統治。
蕭公權的“孟子圣人革命論”提出后,盡管得到了一些學者的認可,但還有一些學者贊同梁啟超的“孟子人民革命論”。不過,他們都沒有正面回應蕭公權等人的觀點。現在回過頭來看,“孟子人民革命論”是不能成立的。梁啟超等人的推論不嚴謹。孟子的確贊成以民為本和立君為民,但是這并不等于孟子贊成人民有權利打倒暴君。在他們論證的過程中,他們沒有找到孟子贊成人民革命的原話。這是一個致命的缺陷。梁啟超等人一再引用齊宣王和孟子關于湯武革命的那段對話來證明孟子主張人民擁有打倒暴君的權利。但是從那段對話中根本得不出孟子主張人民有革命權利的結論。在那段對話中齊宣王和孟子只談論了湯武桀紂四個人物,人民沒有出場。齊宣王認為湯武的舉動有悖君臣倫理,他們都以下犯上,周武王犯下了弒君之罪。面對齊宣王的質疑,孟子為湯武革命進行了辯護,他要證明湯流放桀和武王伐紂是合乎道義的。在孟子看來,桀紂是道德敗壞、禍國殃民的暴君,失去了做君主的資格。湯武則是道德和智慧超群的圣人,他們為救人民打倒桀紂是合乎正義的。湯武的舉動不應以一般的君臣倫理來衡量。周武王只是誅殺了一個失去君主資格的獨夫民賊,算不上弒君。孟子在為圣人革命辯護而不是為人民革命辯護。梁啟超等人的確誤讀了這段對話。他們引用的資料非但不能證明他們的觀點,反而可以作為“孟子圣人革命論”的依據。而蕭公權等人的“孟子圣人革命論”的確能在《孟子》中找到確鑿的依據。
雖然主張“孟子人民革命論”的學者確實誤解了《孟子》,但是主張“孟子圣人革命論”的學者沒有系統地回答如下問題:人民革命究竟存在什么樣的問題才使得孟子把革命的權利僅僅賦予了圣人?此外,孟子真的就主張暴政壓迫下的人民只能一邊忍受痛苦,一邊靜候圣人的到來?這是進一步研究孟子革命論時所要解決的問題。
二、孟子反對人民擁有革命權利的緣由
孟子反對人民使用暴力打倒暴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要的原因就在于孟子認為人民這個群體素質低下,人民突出的特征是道德水平低下,也無政治方面的才華。孟子的確十分熱愛人民,以民為本,提出了“民貴君輕”。但是孟子一再強調人民是個道德素質落后的群體,有待教化。孟子說:“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離婁下》)又說:“待文王而后興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孟子·盡心上》)他明確無誤地說從道德上講人民形同禽獸,只有赤裸裸的功利性,沒有德性可言。他們需要圣人和君子的教化。孟子同情暴君污吏壓迫下的人民,但他認為由于人民道德素質低下,一旦人民在暴政的壓迫下喪失了產業,沒有了活路,人民只會淪為違法亂紀的犯罪分子。他說過:“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孟子·梁惠王上》)在孟子看來暴君統治之下只會出“賊民”,他說:“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孟子·離婁上》)如果統治者不講禮義、道德敗壞,不對人民進行教化,人民就會做出各種違背道德法制的事情,淪為“賊民”。這源自儒家的德治理念。儒家向來認為統治者的道德水準決定被統治者的道德水準,孔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孟子亦說:“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孟子·離婁上》)在仁君治理下人民會成為良民,而在暴君統治下人民只會淪為暴民。因此孟子盡管憐憫被壓迫的人民,但是他同樣認為這些備受暴政折磨的人民是一群道德敗壞的“賊民”。在孟子看來,一伙“賊民”即便用暴力推翻了暴君,其后果只能是以暴易暴。政權掌握在一伙“賊民”手中,大多數人民依舊會生活在暴政之下。因為“賊民”不可能實行仁政。孟子曾說過:“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眾也。”(《孟子·離婁上》) “賊民”和暴君都不是仁者。因此政權無論是由“賊民”把持還是由暴君掌握都會危害國家和人民。孟子認為發動革命是為了救人民于水深火熱之中,把權力從惡人手中轉移到賢人那里。如果革命過后,仍舊由一幫道德敗壞的人當政,革命就失去了它應有的意義。孟子認為人民比起圣人最缺乏的就是圣人高尚的道德情操,人民革命不能保證革命之后出現一個賢君。被壓迫的人民和圣人一樣痛恨暴君,但是被壓迫的人民沒有圣人那種解救天下蒼生的高尚理想。孟子認為只有圣人領導革命才能保證革命的正義性,才能用仁君取代暴君,用仁政取代暴政,讓人民脫離苦海。
革命意味著使用暴力,在革命的過程中暴力一旦被濫用就會給人民的生命財產帶來嚴重的損失。因此孟子認為必須盡最大可能降低革命的代價,把暴力的使用限定在盡可能小的范圍內。圣人才能恰當地利用暴力。孟子認為圣人十分珍惜人民的生命財產,他們能夠做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孟子·公孫丑上》)孟子認為圣人在動用武力、鏟除暴君時能夠做到:“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吊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孟子·梁惠王下》)按照孟子的設想,圣人在革命時只把矛頭對準暴君,農工商等各階層的人們照常生活、生產,不會遭受任何損失。孟子認為只有圣人能把握好發動革命的時機,圣人只會在暴君眾叛親離成為孤家寡人時發動進攻,握有百分之百的勝算。他說過:“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孟子·公孫丑下》)孟子認為圣人領導的革命會受到暴君統治下的人民的熱烈歡迎。受到人民熱烈擁護的正義之師無需經過激烈長久的戰爭就可以打倒暴君。因此孟子不相信武王伐紂時會發生血流漂杵的戰斗,他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盡心下》)在他看來武王發動的革命戰爭應是很容易就取得了勝利,因為這是至善對至惡的戰爭。在湯武革命的問題上,我們可以看出孟子的理想主義風格。孟子認為只有圣人可以做到在最恰當的時機以最低的代價取得革命的勝利。這種智慧是普通的人民所不具備的。孟子認為:“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后知,使先覺覺后覺。”(《孟子·萬章下》)先知先覺的圣人是極少數,他們擁有超越凡人的大智慧,這是后知后覺的民眾所缺乏的。在孟子看來,人民發動的革命注定要給社會帶來諸多的破壞,生靈涂炭就在所難免。人民革命就算打到了暴君,代價也會很慘重。
孟子擔心一旦賦予人民革命的權利,人們就會濫用這一權利,社會上就會冒出很多亂臣賊子。如果認可人民有權利打倒暴君,那么很快就會產生一個問題:人們會把現實中很多君主當作暴君打倒。因為現實中讓所有人都滿意的君主幾乎不存在,因此那些表現一般的君主很可能被居心叵測之人隨意扣上暴君的帽子而被打倒。孟子知道在君主制下賢明如湯武的君主屈指可數,但暴虐如桀紂的君主也很少。大部分君主介于這兩者之間,他們既會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也會有一些危害人民之舉。孟子認為人們必須接受這類君主的統治,革命是針對桀紂那樣的暴君,他說:“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孟子·萬章上》)因此孟子反對濫用革命的名義推翻君主。孟子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下》)孟子把春秋以來殺死君主的人稱為亂臣,用“弒”這個字眼定義他們的行為。弒君在古代是十惡不赦的大罪。孟子只把革命的權利賦予極少數像湯武那樣的圣人,而不賦予數量龐大的人民,目的之一就是為了避免有人打著人民革命的旗幟起來弒君篡位。其實圣人革命論也難逃被濫用的命運。中國歷史上那些陰謀弒君篡權之輩大多喜歡以湯武自居,而把他們打倒的對象視為桀紂。
孟子是一個重視歷史經驗的思想家,他所贊同的湯武革命不是人民發動的革命,而是諸侯發動的革命。諸侯屬于貴族階層。因此湯武革命屬于貴族革命。歷史上湯武能夠成功完成改朝換代的革命,與他們的諸侯身份是分不開的。打倒暴君需要一定的實力作為基礎。孟子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他說:“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孟子·公孫丑上》)孟子指出推翻暴君、成就王業固然不需要特別雄厚的實力,但是也要一定的實力。湯本是夏朝的一個諸侯,奠定西周建國大業的周文王原是商朝的一個諸侯。這是湯武革命成功的重要保障。在孟子的歷史世界中沒有人民革命推翻舊王朝建立新王朝的事例。西周末年的國人暴動只是趕走了暴君周厲王,沒有建立仁君當政的新王朝。受制于歷史經驗,孟子認為人民革命是沒有出路的。平民階層出身的人領導革命、建立新王朝的事例要到孟子去世后才出現。孟子不賦予人民革命的權利符合他的歷史經驗。他認為建立新王朝的圣人應出自諸侯之中。
三、孟子認為人民應該采取非暴力的方式反抗暴政
蕭公權認為:孟子主張人民可以采取“不親上死長”的態度對待暴虐的統治者,可以不擁護暴君污吏,除此之外就只能等待“天吏”來解救他們。劉澤華說:“孟子猛烈地抨擊了時弊,尖銳地批評了當時的君主,斥責他們是率禽獸食人之輩。言詞盡管激烈,不過老百姓切不可動手動腳。孟子教導人民,等著吧,‘五百年必有王者興’!”[5]他的意思是孟子主張人民只能忍受暴政,等待圣人的解救。其實蕭公權和劉澤華都誤解了孟子。孟子固然不主張人民使用暴力反抗暴君,但他卻贊成人民采用遷徙等非暴力的方式反抗暴政,孤立暴君。
孟子主張人民一旦遭遇暴政,他們有權利遷徙到仁君統治的國家。孟子告訴急于招攬移民的梁惠王,如果他施行仁政,“斯天下之民至焉。”(《孟子·梁惠王上》)人民為了脫離苦海,遷徙到善待民眾、施行仁政的國家是合情合理的。可見孟子并不主張人民一味地忍受暴君的統治。在秦朝統一中國之前,中華大地上一直是諸國林立,人民可以通過遷徙逃避暴政。孟子不但主張人民采取遷徙的方式孤立暴君,大夫和士也可采取這種方式遠離暴政。孟子說:“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孟子·離婁下》)從理論上講,如果人民和士人都遷徙到國外,那么暴君就會煢煢孑立,其統治就會走向崩潰。
孟子認為人民擁有言論權,當人民遭遇暴政和不公時,他們有權利發出自己的呼聲,表達心中的不滿。孟子在給齊宣王講與民同樂的道理時說:“臣請為王言樂。今王鼓樂于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與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于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與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孟子·梁惠王下》)可見,孟子認為當國君只顧個人享樂,置人民的生死于不顧的時候,人民完全有權利發出譴責國君暴政的呼聲。孟子并不主張人民默默無聲地忍受暴政。孟子主張君主一定要尊重人民的言論權,在治理國家時要注意傾聽人民的意見,他說:“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后察之;見賢焉,然后用之。”(《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認為愛民如子的君主一定會在重要問題上征詢人民的意見。君主身邊的親信和大夫的意見沒有人民的意見重要,人民的呼聲是君主決策的最重要的依據。而暴君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一意孤行,根本不愿意傾聽民聲,甚至要打擊那些發出呼聲的民眾。孟子說:“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孟子·離婁上》)孟子在這里就提及了有名的暴君周厲王,他的暴政之一就是壓制人民的言論權,制造道路以目的恐怖氣氛。
孟子認為當圣人率領的正義之師攻打暴君時,被暴君壓迫的人民有權利歡迎正義之師,助其完成鏟除暴君的使命。他們不用為此背上叛國投敵的罪名。人民的福祉高于一切,人民只忠于善待自己的國君。他們根本沒有義務為暴君充當炮灰。孟子認為被暴君壓迫的人民對正義之師的期盼猶如“大旱之望云霓也。”(《孟子·梁惠王下》)圣人攻打暴君是為了“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孟子·滕文公下》) 因此當圣人率領的正義之師去攻打暴君統治下的國家時,該國家的人民肯定會“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認為被壓迫的人民熱烈歡迎吊民伐罪的隊伍是理所當然的。
綜上所述,孟子同情被暴君污吏欺壓的人民,但他認為人民的素質低下,難以恰當地利用暴力,人民革命的前途是以暴易暴。人民革命這面旗幟容易成為亂臣賊子的遮羞布。在孟子的歷史世界中無人民革命成功的事例。因此孟子不主張人民擁有革命的權利。孟子把利用暴力鏟除暴君的權利判給了道德和智慧超越常人的圣人。孟子堅信只有他們才能恰當地使用暴力,用仁政代替暴政,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受苦受難的人民應把希望寄托在這些極少數政治精英身上。被孟子理想化后的湯武革命實際上成為后世不可重復的樣板。孟子痛恨暴君污吏,他主張人民使用遷徙等非暴力的手段反抗暴政。他把人民的反抗權限定在非暴力的范圍內。孟子既不是一個擁抱絕對君權的御用學者也不是一個主張人民主權的民主主義者。他是一個關心民眾疾苦的精英主義思想家。這是孟子革命論再研究的結論。
參考文獻:
[1]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39.
[2]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59.
[3]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M].北京:新星出版社,
2010:63.
[4]張分田.中國帝王觀念[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380.
[5]劉澤華.中國政治思想史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66.
作者介紹:
高春海,男,河南南陽人,肇慶學院政法學院講師,歷史學博士,主要研究中國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