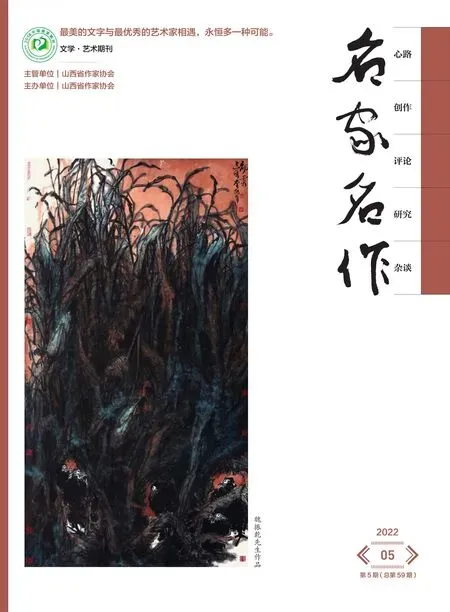“我要”“格倫-多-莫拉尼”(活下去):索爾·貝婁《雨王漢德森》的敘事倫理
彭 濤
敘事倫理是指敘事主體在敘事過程中對敘述內容及敘事形式的選擇所體現出的價值取向和情感態度。針對索爾·貝婁(Saul Bellow,1915—2005)的《雨王漢德森》()的敘事倫理,學者戈德曼明確指出:“貝婁通過圣經敘事來表達猶太倫理作為他的主題。”評論家丹尼爾·法克斯在論文《索爾·貝婁:視野與再展望》中也提出“貝婁的作品始終圍繞道德這根軸線展開”的論斷。這兩位評論家都認為貝婁以倫理道德為核心展開敘事。
針對敘事,學者約翰·克萊頓認為,“貝婁的小說中有一種十分一致的整體布局,每一部小說都出于同樣的需要,刻畫了相似的主人公,他們克服困難,經歷變故,最終得到救贖”。這種敘事上的布局若與《雨王漢德森》相關聯的話,還需要借用熱奈特的敘述分層的概念,即外敘事(extradiegetic)、內敘事(intradiegetic)和元敘事(metadiegetic)。根據熱奈特的敘事分層,這部小說中的故事外敘事指的是由貝婁敘事;內敘事指的是主人翁漢德森用過去時態描述他的非洲之行;元敘事指的是漢德森用過去時態表達其對生活的回憶和反思。本文參照熱奈特的敘事分層的概念,立足于《雨王漢德森》的文本,探討了三個敘事層是如何協作,共同演繹“我要”“格倫-多-莫拉尼”(活下去)的核心倫理觀的。
一、外敘事: “我要”“格倫-多-莫拉尼”(活下去)
“是什么促使我那次去非洲旅行的呢?”(7)小說開篇就采用第一人稱“我”且使用現在時態,表明主人翁準備解釋他非洲之行的原因。誠然,首次“我要”出現在漢德森的個人回憶和反思的元敘事中。在漢德森的第一次婚姻中,他邂逅了小他20歲的莉莉,他來到莉莉在紐約租住的公寓:“手上戴著黃色豬皮手套,心里有一個聲音在不停地呼喊:我要,我要,我要!”(18)這說明由于顯赫的漢德森家族和經濟狀況構成的“被認知的自我”強勢壓制由他個人的努力和奮斗構成的“進行認知的自我”,漢德森深受由此所帶來的后果而痛苦。
此外,“格倫-多-莫拉尼”是非洲阿內維部落的語言,意為“活下去”。它首次出現在漢德森描述非洲之行的內敘事的人物交談中。漢德森遠赴非洲,進入阿內維部落。為迎合其部落習俗,他兩次成功地將其國王伊特羅摔倒在地,獲得了自信。雖然他好心辦壞事,把唯一的水塘給炸毀了,但女王威拉塔莉鼓勵他要“格倫-多-莫拉尼”(98),他雇請的非洲黑人導游洛米拉尤幫他翻譯為“活下去”(98),漢德森不禁茅塞頓開,連忙說:“對,對,對啊!莫拉尼。我莫拉尼。……我不但要使自己活下去,也要每個人都活下去。”(99)
在小說的開篇,雖然“我要”“格倫-多-莫拉尼”(活下去)的字眼沒有出現,但是在主人翁開始準備長篇大論地講述自己為何開始非洲之行、如何去了非洲、在非洲經歷了什么、又是如何回到美國之前,他如此表示:“不管怎樣,這個我以為把我壓得透不過氣來的世界,如今已不再加怒于我了。可是要我向諸位說個明白當初我去非洲的原因,那我必須老老實實地尊重事實。我想我還是從金錢講起吧。”(7)如此這番表達表明漢德森已經活過來了,他準備心平氣和地描述自己的非洲之行和對生活的反思,所以,故事外敘事中的漢德森用自己冷靜且平和的心理狀態詮釋了他極力追求的“我要”“格倫-多-莫拉尼”(活下去)的結果。
二、內敘事: “我要”“格倫-多-莫拉尼”(活下去)
根據熱奈特的敘事分層,有兩點值得注意:“(1)在不同的敘事間有敘述本身表示的界限,有不同的層次;(2)敘述分層中第二個敘事(內敘事)的敘述者是第一個敘事(故事外敘事)中的人物了。”在進行了僅有一頁篇幅的故事外敘事后,貝婁在《雨王漢德森》中仍然采用第一人稱即“我”的視角來進行內敘事,由漢德森自己描述非洲之行。
第一部分,漢德森首先說明了為何要遠赴非洲, 他準備“從金錢講起” (7)。漢德森家族非常富有,他本人“從老頭兒那里繼承了三百萬元”(7)。讓人驚訝的是漢德森本人也很出色。他“曾是個榮獲紫心勛章和其他勛章的富有戰斗經驗的軍官”(103);是“常春藤聯合會中的一所名牌大學的畢業生”(8),可是漢德森仍然說:“如果我不是漢德森家族的后裔,不是我父親的兒子,他們早就把我趕出校門啦!”(8)這種 “被認知的自我”碾壓“進行認知的自我”使漢德森“一度非常消沉”(78),甚至把他逼到了死亡的邊緣,他說:“我顯然恰恰有著大量死亡的潛在因素……為什么死亡總是離我這么近?”(275)
第二部分,漢德森講述了非洲之行的經歷。為了擺脫死亡和“我要,我要!”,漢德森與導游洛米拉尤經過沙漠,來到非洲的阿內維部落。在這片荒蕪之地,他獲得的最大鼓勵來自女王威拉塔莉。在知道自己炸毀魚塘而做錯事后,漢德森開始唱起韓德爾的《彌賽亞》中的一段:“他被蔑視,被人厭棄,多受痛苦,常經憂患。”(98)威拉塔莉鼓勵他要“格倫-多-莫拉尼”(98),洛米拉尤幫她翻譯給漢德森聽,“她說你要活下去”(98),漢德森恍然大悟,意識到自己“正是為了尋求這個莫拉尼而來的”(99)。
在“活下去”這樣的啟示下,漢德森與洛米拉尤流浪至瓦利利部落。他搬動了神像門瑪,為土地帶來雨水,被封為“圣戈”(雨王)。漢德森感到“我還活著,而且活得很好,我獲得了那古老的格倫-多-莫拉尼”(212)。國王達孚帶他接近獅子阿蒂,并且說:“我要你想象自己就是一頭獅子。”(291)雖然漢德森的反應是,“我可能要昏過去了”(285),但他還是接受了這種瘋狂的挑戰。他不禁說:“我的全部憂傷都隨著吼聲傾訴出來了。”(292)此時漢德森的“進行認知的自我”由于自信、勇氣和膽量使“格倫-多-莫拉尼”(活下去)一步步成為可能。
第三部分,漢德森講述了如何結束非洲之行。當瓦利利部落由于王位之爭而強制截留漢德森,臨死前的達孚還要他當繼承人,他需要娶六十多個老婆,如果不能繁衍子女,他會被處死。這種野蠻的部落文明與漢德森的理性和正義起了沖突,他說:“我已經有了我所要的妻子”(344);“我想我指的是理性——就是那個理性……不過還有正義”(358)。在“理性”和“正義”的驅動下,“我們(漢德森和洛米拉尤)在月影里穿行”(356);繼而“越過兩三百英里荒無人煙的地區”(350);再而到達巴文泰等地;最后坐上了飛往美國的班機。當飛機在紐芬蘭機場加油時,漢德森走下了飛機,“走上幾乎永遠是冬天的冰凍大地,拼命做深呼吸,以至身體都發抖了,那純粹是幸福之路”(372)。這種依據“理性”和“正義”而完善的“進行認知的自我”使得漢德森走在了“格倫-多-莫拉尼”(活下去)的幸福大道上。
通過描述非洲之行,漢德森克服了對死亡的恐懼,擁有了自信、勇氣、膽量、理性和正義,領悟到愛和家庭的重要性,“進行認知的自我”戰勝了“被認知的自我”。故事外敘事中的主人翁變成了內敘事的人物,內敘事充實了外敘事的內容,使得“我要”“格倫-多-莫拉尼”(活下去)的倫理觀念生動而具體。
三、元敘事: “我要”“格倫-多-莫拉尼”(活下去)
相比僅一頁篇幅的外敘事和占篇幅最大的內敘事,《雨王漢德森》的元敘事就如同珍珠一般,鑲嵌在漢德森有關非洲之行的內敘事里,由回憶和反思組成,它們讓讀者接觸到了漢德森的內心世界。在這一層面上,有兩件具有代表性的事。
首先是漢德森對待死亡的態度。漢德森在紐芬蘭機場等飛機時回憶起了自己16歲時哥哥狄克的死亡:“他是在荒山里淹死的,我的爸爸那時望著我,感到萬念俱灰。”(368)他繼續回憶道:“老頭滿臉白胡須,他卻使我覺得我們的家族世系隨著狄克在阿迪龍達克山區死去而終結了。”(368)父親對哥哥的重視和對他的輕視加深了他在“被認知的自我”與“進行認知的自我”的對立上的痛苦,他陷入了死亡的陰影。中晚年時期,當莉莉勸他“趁現在做點什么事”(24)時,漢德森對她說:“如果你還要嘮叨這些,我就一槍把自己的腦袋打開花。”(24)
為了避免死亡,55歲的漢德森遠赴非洲,在到達阿內維部落后,決定用爆炸的方法來清除水中的青蛙和蝌蚪。在準備爆破前,漢德森又回憶起來:“在我們常去避暑的阿迪龍達克山脈間的小鎮,我哥哥狄克淹死的地方,有一座水力磨坊。”(115)現在的他來到了非洲,他很慶幸自己的選擇:“否則我將注定只能作為一個擁有三百萬元的搗蛋鬼或大笨蛋,或一個膽小怕事、忐忑不安的庸人而死去。”(116)當他在瓦利利部落聽從國王達孚的安排而學獅吼時,他找時間給妻子莉莉寫了一封信,他寫道:“再來一次較量吧,死亡,你和我。”(311)漢德森話鋒一轉,又反思道:“然而我反正是和死人打過交道的,而且也沒有在他們任何一個人身上賺過一文錢。我也許不如改變一下,為生計做點兒事情。”(311)漢德森在年少時對死亡的恐懼在非洲之行中得以釋然,萌發了“為生計做點兒事情”的渴望,表明他意識到“我要”“格倫-多-莫拉尼”(活下去)。
其次是與第二任妻子莉莉的關系。漢德森是猶太人。就猶太婚姻觀來說,“猶太教只認可夫妻之間的性關系……通奸是對婚姻的褻瀆,等同于違反神的誡命”。漢德森與第一任妻子生養了3個孩子,遇到小他20歲的莉莉后開始第二段婚姻,可是當莉莉堅持將自己的畫像與漢德森家族的畫像掛在一起時,雖然莉莉對物質、名利的追求與他人無異,但是漢德森絕望地反思道:“她要求結束我們各自的孤獨處境。如今她再也不孤單了,而我卻仍然孑然一身。”(94)
漢德森在瓦利利部落經歷了一些事情,他寫了封信托洛米拉尤寄給妻子莉莉,在信中,他闡明了自己的想法:“我回去以后,要去學習醫學。……為生計做點事情。”此外,他還表達了對愛的認識:“是愛才使現實成為現實的。”(311)當洛米拉尤告訴他并恭喜他要娶六十多個老婆時,漢德森反駁道:“我怎么能想要接受這一大幫女人呢?我已經有了我所要的妻子。”(344)在逃離的路上,他堅定地對自己說:“我一定要回到莉莉和孩子們的身邊。”(359)源于對家庭的渴望和對親情的堅守,漢德森選擇學醫作為生計,堅定地想要“格倫-多-莫拉尼”(活下去)。
綜上所述,漢德森對待死亡的態度和與妻子莉莉的和諧關系的建構貫穿于他非洲之行的內敘事里,表達了主人公的“我要”“格倫-多-莫拉尼”(活下去)的倫理選擇。漢德森的回憶、反思乃至辨析如繁星點點,帶著讀者走入了他的心理和精神世界,讓人物形象更加鮮活且生動,迎合了帕斯卡的一句名言:“人是一支蘆葦,但是一支有思想的蘆葦。”
四、結語
趙毅衡教授在專著《當說者被說的時候——比較敘述學導論》中提出了辨別敘述分層的明確標準:“敘述分層的標準是上一層次的人物成為下一層次的敘述者。”按照這個標準,《雨王漢德森》的外敘事、內敘事和元敘事可謂是層次分明。主人公漢德森是外敘事的主角,同時他又成為下兩個層次即內敘事和元敘事的敘述者,這三個敘述層復雜而不紊亂、嚴密而不松散、新異而不荒誕;每一層都服務于“我要”“格倫-多-莫拉尼”(活下去)的倫理觀,共同揭示了主人翁尤金·漢德森的精神困境和倫理追求,也凸顯了貝婁的以人為本、生存至上的價值取向和人文視野,這達到了南非小說家庫切所評價的“以無與倫比的修辭資源,用以編織過去與現在、記憶與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