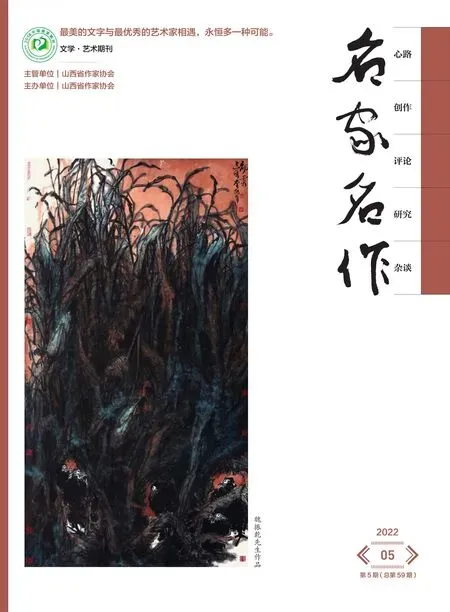細讀《孔乙己》
張建春 楊 威
作為魯迅先生短篇小說的扛鼎之作,《孔乙己》以其冷峻的筆調克制地敘事,不經意間地臧否,成功地為我們展現了底層知識分子,準確地說——科舉制度下進階失敗的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況。作為吳敬梓《儒林外史》精神與文脈的延續,對于在新舊文化互相碰撞下,舊文化土崩瓦解下的知識分子的生存困境,作者以其生花妙筆予以了準確而客觀的描述。“孔乙己”因其標本式的存在,在世界文學史的文學群像中熠熠生輝。
小說開頭,詳細地描述了獨特的南方市井風俗圖,“魯鎮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別處不同的:都是當街一個曲尺形的大柜臺,柜里面預備著熱水,可以隨時溫酒”,隨后,有一處貌似漫不經心的閑筆,“每每花四文銅錢,買一碗酒,——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現在每碗要漲到十文”,“現在每碗要漲到十文”這處閑筆,可以說是閑筆不閑。須知,作為具有虛構性質的小說,其最大的敵人就是虛假,而在此處刻意強調“現在”,最大限度地強化了小說的真實性。為了讓讀者更加直接地進入小說所描繪的世界——魯鎮,作者用貼標簽的方式,將顧客分成了短衣幫與長衫派。短衣幫與長衫派以符號化的方式對魯鎮進行了解構,非此即彼,涇渭分明。
接著,“我”也就是文中的“小伙計”出現了,作為整個事件的見證者,“我”的所見所聞無疑也增強了小說的真實性,小說中寫道:“幸虧薦頭的情面大,辭退不得,便改為專管溫酒的一種無聊職務了。”注意“無聊”兩個字,是整個小說的絕佳注腳,正如莎士比亞《麥克白》第五幕第五場所言:人生如同癡人說夢,充滿著喧嘩與騷動,卻沒有任何意義。
作者寫道:“我從此便整天的站在柜臺里,專管我的職務。雖然沒有什么失職,但總覺得有些單調,有些無聊。”仍然是“無聊”,反復鋪墊,為孔乙己的出場蓄勢,“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幾聲,所以至今還記得”。孔乙己的價值僅僅是博人“笑幾聲”,又讓我們感到一種深深的悲涼。
接著,孔乙己出場了,魯迅先生首先強調了他的身份,“孔乙己是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無疑孔乙己的身份極度尷尬,他自己也缺乏最起碼的身份認同感,猶如蝙蝠一般——異于禽,異于獸。在精神層面,孔乙己認為自己是知識分子,理所應當穿長衫,所以長衫無異于是他精神貴族的外化符號,而現實又無比殘酷,物質上的困頓又不得不讓孔乙己“站著喝酒”,精神與物質、理想與現實的嚴重割裂,讓孔乙己充滿了荒誕性,孔乙己可以說是流動的行為藝術,自身充滿了后現代主義的黑色幽默。作者對孔乙己的外貌以及服飾進行了詳細的描述,尤其是其精神圖騰長衫,“穿的雖然是長衫,可是又臟又破,似乎十多年沒有補,也沒有洗”,讓人不由生出“余生也晚”的感嘆,這件長衫我們無緣睹其干凈時的樣貌,現在只剩下臟破,可是孔乙己還要堅持穿在身上,他最后的倔強不由得讓人感慨唏噓。“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著他笑”,我們可以明顯地感覺到,眾人的“笑”實際上并無惡意,最起碼大家認為并無惡意。孔乙己以其精神上的高傲未做理會,“他不回答”,而且帶有挑釁性質地“排出九文大錢”,注意這個“排”字,這可謂是孔乙己人生的高光時刻,于是看客們繼續著孩子式的惡作劇:“孔乙己,你臉上又添上新傷疤了。”對于這種單純的人身攻擊,孔乙己可以不做理會,但人們說“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東西了”,對于涉及人格的攻訐,孔乙己必須做出回應:“你怎么這樣憑空污人清白……”“竊書不能算偷……竊書!……讀書人的事,能算偷么?”孔乙己金句頻出,只得偷換概念,玩點文字游戲,他近乎天真地認真應對,終于“引得眾人都哄笑起來: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薩特說:他人即地獄。人類的可悲之處是——有時候是狼吃羊,更多的時候其實是羊吃羊。
為了讓孔乙己的形象更為豐滿,除了別人視角中的形象,作者還特意安排了別人背后的議論,“孔乙己原來也讀過書,但終于沒有進學,又不會營生;于是愈過愈窮,弄到將要討飯了”,作者以另外的一種比較討巧的方式來完善孔乙己的人物形象,同時作者說孔乙己雖“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竊的事”,但強調“品行卻比別人都好,就是從不拖欠;雖然間或沒有現錢,暫時記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還清,從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作者實際在說孔乙己偶爾的偷竊不過是生活所迫,但對于儒家道德范疇的大節“信”,孔乙己是深以為然的,并不是像其他的知識分子說說而已,魯迅先生寥寥數筆,就揭示出了孔乙己性格中包含的復雜性。
當然,貓抓住老鼠以后,最大的快意絕不是馬上吃掉老鼠,而是純享于一場精致戲耍所帶來的精神盛宴。看客們是非常精通兵法的,看到孔乙己“漲紅的臉色漸漸復了原”,就先示弱:“孔乙己,你當真認識字么?”等到孔乙己志得意滿之時,他們才發出致命一擊:“你怎的連半個秀才也撈不到呢?”對于孔乙己人生當中最為慘痛的事情,看客們是深諳打蛇打七寸的道理,于是“孔乙己立刻顯出頹唐不安模樣,臉上籠上了一層灰色”,這“灰色”可以說是“死灰色”,正所謂哀莫大于心死,于是“眾人也都哄笑起來: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這“快活的空氣”卻讓我們感到了一種浸入骨髓的寒冷,看客們的這種陰毒的玩笑,讓我們感受到了底層人們之間的這種互相傷害,快樂似乎永遠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
按照馬斯洛理論,需求可以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五類,由較低層次到較高層次依次排列。作為底層知識分子,孔乙己在酒足飯飽基本滿足了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后,他也不可避免地產生了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當然,在成人世界作為弱勢群體,孔乙己是無法滿足以上需求的,于是他只能將視線投射到孩子身上。“你讀過書么?”孔乙己向我提出這樣的問題,實際上是渴望與人交流,也就是社交需求的一種體現,然后又很懇切地說道,“不能寫罷?……我教給你,記著!這些字應該記著。將來做掌柜的時候,寫賬要用”,這自然就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需要了,再看“我”,“又好笑,又不耐煩,懶懶的。”“誰要你教,不是草頭底下一個來回的回字么?”而孔乙己立刻“顯出極高興的樣子”,因為自己終于英雄有用武之地了,于是出現了經典的“回字有四樣寫法”,科舉制度下所謂的學問由此可見一斑。我們不由會想起吳敬梓寫范進不知蘇軾,馬二不知李清照。可見八股取士對讀書人學識、眼界、思想的禁錮——為了應考,他們只讀考試用書,只做八股文章,對包括蘇東坡、李清照的詩詞文章在內的所謂雜學毫無接觸。
接下來,是孔乙己與孩子們的良性互動,“這一群孩子都在笑聲里走散了”,無疑這是孔乙己的快樂與別人的笑在文本中唯一一次完全契合的地方,在這里,我們仿佛可以感受到隱藏在文字背后不易被人察覺的溫暖。魯迅曾在《吶喊》自序中用自嘲式的筆調寫道:至于我的喊聲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顧及的;但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委婉了一點,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里也不敘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魯迅先生的悲憫于不動聲色間流露出來。尤其是孔乙己的名言:“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孔乙己好像《皇帝的新裝》中那個永遠沒有長大的孩子,他對整個世界抱有最大的善意,而現實卻如黑鐵般冷酷無情。
“孔乙己是這樣的使人快活,可是沒有他,別人也便這么過。”可謂是一語成讖,孔乙己的這種可有可無的存在價值,可以說是他悲劇命運的千里伏脈,悲涼的氣息在文本中彌漫開來。
本來孔乙己的腿被打折,應該是他的生命中最為慘烈的部分,而描寫也應該是高潮迭起,而魯迅先生卻并沒有這么處理,他反而用了異常冷靜與克制的筆調,如動作描寫“掌柜也不再問,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賬”,如毫無感情色彩的語言描寫,“打折了怎樣呢?”“怎樣?……誰曉得?許是死了。”巨大的事件與情感的冷漠及行動上的無視,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以此使文章內部具有強大的張力。再說對孔乙己腿被打折的敘述,由于小伙計是限知視角,所以只能由別人只言片語的講述來拼湊還原事件,無形之中使得小說更加客觀真實,作者盡可能退居到人物角色之后,當然這也是對中國傳統小說寫法上的致敬與傳承,如《三國演義》中寫關羽溫酒斬華雄:“關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來。’出帳提刀,飛身上馬。眾諸侯聽得關外鼓聲大振,喊聲大舉,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眾皆失驚。正欲探聽,鸞鈴響處,馬到中軍,云長提華雄之頭,擲于地上。其酒尚溫。”當然,好的文章都是相似的,不好的文章才各有各的壞處,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如“冰山在海里移動很是莊嚴宏偉,這是因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這就是海明威的“冰山理論”。冰山漂浮在海面上的時候,我們只能看到它露出水面的一小部分,可是在水下,卻潛藏著巨大的山體。海明威以此比喻寫作:作家有八分之七的思想感情是蘊藏在文字背后的,真正通過筆端表現出來的只有八分之一。如果作家能夠處理好這一點,讀者就能強烈地感受到這八分之七的分量。藝術上的克制留白在此有著完美的體現,中國藝術重視空靈之美。虛實,是中國美學中的一對重要范疇,虛實結合,虛中有實,實中有虛。在虛實之間,中國藝術對虛更為重視,因為實從虛中轉化出來,想象空靈,故有空際;空靈澄澈,方有實在之美。老子說:“大白若黑。”在至虛之處有至實之感,這個白,并非空白,而是一個靈氣往來的地方。密不透風、氣韻不暢無疑是失敗的。留白即“冰山理論”中水下之冰,它靜默無聲,卻又博大而深沉。
很快,就到了孔乙己謝幕的時候。首先,是魯迅式文筆的景物描寫“秋風是一天涼比一天”,真正地體現了一切景語皆情語,秋風好比人心,人情冷暖在孔乙己身上可以說表現得淋漓盡致。然后,未見其人先聞其聲:“溫一碗酒”。接著寫外貌:“他臉上黑而且瘦,已經不成樣子。”與前面剛出場時“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臉色,皺紋間時常夾些傷痕;一部亂蓬蓬的花白的胡子”形成了一組鮮明的對比,我們很明顯地可以感受到孔乙己已經日薄西山,馬上就要走到生命的盡頭了。再看他的衣服,“穿一件破夾襖”,孔乙己已經被生活剝去了象征知識分子身份的長衫,他徹底被打回了原形,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對于孔乙己已經成為高不可攀的奢侈品,生理需求與安全需求成為必需品。掌柜的看到孔乙己后說的第一句話居然是:“孔乙己么?你還欠十九個錢呢!”他關心的仍然是孔乙己的欠賬,與自己利益休戚相關的事情被排在了第一位,除此之外的任何事情他都是漠不關心的。然后是一如既往地拿孔乙己取樂:“孔乙己,你又偷了東西了!”因為事實擺在面前,孔乙己只得說:“不要取笑!”老板步步緊逼刀刀見紅:“取笑?要是不偷,怎么會打斷腿?”可以說老板撕下了孔乙己最后一絲做人的尊嚴,用最為輕松的語氣殘忍地剝開了孔乙己的傷疤,孔乙己赤身裸體鮮血淋漓地在大家面前示眾,老板可以講是全無心肝。當然這并不是孔乙己的恥辱,而是整個社會的恥辱,叢林法則的使用程度可以說是社會文明與否的試金石,我們看到在魯鎮,叢林法則大行其道,整個成人社會彌漫著野蠻、冷漠、自私的味道,弱肉強食,每個人都渴望站在食物鏈的頂端,而每個人又不可避免地成為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對象,這也是魯迅在《狂人日記》中提到的舊中國的生態模式——“吃人”。下面又寫到了“此時已經聚集了幾個人,便和掌柜都笑了”,“便又在旁人的說笑聲中”兩次“笑”,孔乙己的一生仿佛就是以笑開場,以笑謝幕,而所有的笑幾乎都與孔乙己無關,笑都是與孔乙己疏離的,都是無厘頭的,看客式的笑毫無緣由,充滿了集體無意識的意味。孔乙己的此次出場,毫無疑問是對他死亡的一次預熱。此時,出現了一個細節“他從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錢”,這次已經變成了“摸”而非“排”了,“摸”有從袋里往外挖出的意思,孔乙己被丁舉人打折了腿,生活更苦,只能“摸出四文大錢”,神情沮喪。與前文“排”對比,鮮明地表現了孔乙己每況愈下的悲慘境地。隨后,魯迅仍然不動聲色地描寫“原來他便用這手走來的”“坐著用這手慢慢走去了”,“用這手”“走”,我們感受到一種滑稽的殘酷感,這無疑是魯迅先生故意為之,這已經不是歐亨利式“含淚的笑”了,而是魯迅式“神經撕裂的笑”了。
然后,孔乙己被人記起了兩次,一次是到了年關,掌柜取下粉板說:“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另外一次是到第二年的端午,掌柜又說:“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其生命的有無僅僅與微不足道的十九個錢有關,而更為荒誕的是記掛他的人其身份不過是債主而已。最后,孔乙己作為個體生命,猶如他在粉板上的欠賬一樣最后被輕輕拭去了。最后,魯迅先生用神來一筆為孔乙己的生命做了最后的注解:“大約孔乙己的確死了。”“大約”表示是自己的推測,自己并沒有親眼見到。但從孔乙己最后一次到酒店的狀況和當時的社會環境來看,是必死無疑的。當然我們不妨進行開放式閱讀:文中的孔乙已是死了,但生活中的類似“孔乙已”的人實際是活著的。這是魯迅的“冷”幽默,常冷不丁地激發你的思考。死了,連作為茶余飯后的談資也沒有,更深刻地表現了孔乙己的悲劇不僅是個人的悲劇,更是社會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