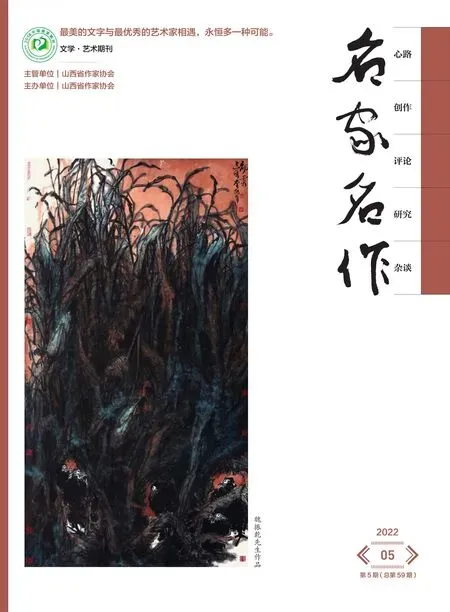從“自然美”的審美角度略談《湘行散記》
蒲泉伶
一、引言
李澤厚在《美學四講》里提出:“美的本質和根源是自然的人化,主觀實踐和客觀現實的交互作用。”格式塔心理學的同構說認為:“自然形式與人的身心結構發生同構反應,便產生審美感受。”“中國人認為只有在自然中,才有安居之地;只有在自然中,才存在著真正的美。”沈從文的《湘行散記》作為一本真實記錄返鄉見聞的散文集,淡化了人與自然之間的主客體身份,從而營造了一個“比人的世界大得多的文學世界”。因此,本次研究將從湘西的自然景觀入手,對其作品《湘行散記》中的湘西世界進行“自然美”的審美角度研究,探討作品中如何描述人與自然環境、自然生態的關系,以闡明自然與人的聯結,體現出沈從文作品里有關自然和人性豐富的文化內涵。
二、審美意象:河流生與死的隱喻
在《從文自傳》中,沈從文曾直言:“我幼小時較美麗的生活,大都不能和水分離。我受業的學校,可以說永遠設在水邊。我學會思索,認識美,理解人生,水對我有極大關系。”可見從年少時開始,沈從文的人生就一直受到“水”的滋養;到了中年后,他在給妻子張兆和的信中,還是動情地談道:“三三,我看久了水,從水里的石頭得到一點平時好像不能得到的東西,對于人生,對于愛憎,仿佛全然與人不同了。”可以說,水在沈從文的一生中占據重要地位。這一汪水具體而言,就是著名小說《邊城》、散文集《湘行散記》中描寫的,擁有五條支流、流經十個縣并且擁有百個河碼頭的湘西之源——沅水流域。
沅水是沈從文的湘西世界中最核心的風景和意象,在某種程度上講,沅水就代表著湘西。因此,在《湘行散記》中,沈從文特別側重“水”意象的刻畫,“水”是湘西景色中的主旋律,沈從文筆下的“河流”是一條生存之河、 生殖之河、 生死之河。 河面上漂流著生生不息的人類的痕跡,河中景象是河的兩岸一切生命場景的倒映與復指。“街的歲月就是河的歲月”, 街上流動著的人事就是河中流動著的水。因為人們依水而居,所以有“水手”,有“妓女”,有“船”,所以有無數動情的故事發生。水的柔情和殘酷也滲透到湘西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中。面對惡劣的自然條件,野性的湘西人會有一份如水的自在和韌性。這種如水的性格讓落后的水手、妓女等湘西人擁有獨特的善良和美麗。從宏觀上說也是沈從文對城鄉文明、歷史發展與停滯的思辨性表達。
(一)生存之河
“看他那數錢神氣,人那么老了,還那么出力氣,為一百錢大聲的嚷了許久,我有個疑問在心:‘這人為什么而活下去?他想不想過為什么活下去這件事?’不止這人不想起,我這十天來所見到的人,似乎皆并不想起這種事情的。可是,一個人不想到這一點,還能好好生存下去,很希奇的。多數人愛點錢,愛吃點好東西,皆可以從從容容活下去的。這種多數人真是為生而生的。”
如果說在《橫石和九溪》中沈從文還對這樣的生存方式有高下遠近之別的判斷,而到了《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和《歷史是一條河》中,他徹底拋卻了之前的觀點:“他們那么忠實莊嚴地生活,擔負了自己那份命運,為自己,為兒女,繼續在這世界中活下去,不問所過的是如何貧賤艱難的日子,卻從不逃避為了求生而應有的一切努力。在他們生活的愛憎得失里,也依然攤派了哭、笑、吃、喝。對于寒暑的來臨,他們便更比其他世界上人感到四時交替的嚴肅。”“我看到小小漁船,載了它的黑色鸕鶿向下流緩緩劃去,看到石灘上拉船的人的姿勢,我皆異常感動且異常愛他們。我先前一時不還提到過這些人可憐的生,無所為的生嗎?不,三三,我錯了。這些人不需我們來可憐,我們應當來尊敬來愛。”
有趣的是蘇童寫過《1934年的逃亡》這樣一本小說,亦是建構在1934年的時代背景下,通過一個人或一個家族的逃亡,表達了潰敗的農村向新興的都市逃亡的歷史。小說中的新老竹匠與沈從文也有映襯的地方,靈魂似乎都是那么孤獨,飄蕩在鄉村,又淪落在城市,而在心靈最柔軟的深處,又不斷地頻頻回首于故鄉。這種鄉村到城市的輪回,又寄托著逃亡與還鄉的記憶。在這種記憶之中,我們可以發現,《湘行散記》亦象征著某種意義上的流變與逃亡,到了湘西世界中,沈從文觀察勞作的水手如何日復一日與大自然抗爭,從最開始的“為生存而生存”的評價逐漸轉變為“順從自然環境的惡劣,但依然與生存環境斗爭”。
人同自然的關系直接包含著人與人的關系,他們擁有一份古樸的情誼,《一個多情水手與一個多情婦人》中描寫了情欲的人化,“性欲成為愛情,自然的關系成為人的關系”,水手牛保拿到蘋果第一時間并不是去撐船,而是送給吊腳樓里的妓女。這份感情在他們離別的時候表現得尤為突出,那份不舍讓人格外憐憫。
“陌生人自然也有來到這條河中來到這種吊腳樓房子里的時節,但一到地,在火堆旁小板凳上一坐,便是陌生人,即刻也就可以稱為熟人鄉親了。”在這樣質樸的環境之中,人與人的關系變得親切而自然,陌生人自然成為熟人鄉親,這是沈從文在湘西河流所聞所見,對其生存意義的思考,某種程度上幸免于其靈魂的流亡。
(二)生死之河
那時的人們根據周邊的環境優勢來決定生存的方式,湘西的這條河養育了無數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其中水手在這條河上奉獻了整個生命,日復一日地重復著似乎已經注定了的命運。
“至于小水手……上灘時一個不小心,閃不知被自己手中竹篙彈入亂石激流中,泅水技術又不在行,在水中淹死了,船主方面寫得有字據,生死家長不能過問。掌舵的把死者剩余的一點衣服交給親長,說明白落水情形后,燒幾百錢紙,手續便清楚了。”
在這樣一個地方,有著一座墳塋,上面刻的碑文,充滿了水手對河流的依賴,卻又充滿了對命運的無可奈何。這時的河是兇險的,似乎隨時都會把河上的生命榨干或是淹沒,此時河流洶涌中充滿著哀鳴。
《桃源與沅州》中還提到兩處死亡:“在這條河里在這種小船上作乘客,最先見于記載的一人,應當是那瘋瘋癲癲的楚逐臣屈原。在他自己的文章里,他就說道:‘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守城兵與特派員所帶領的請愿群眾發生了沖突。結果站在最前線上的特派員同四十多個青年學生與農民,便全在城門邊犧牲了。那個特派員的身體,于是被兵士用刺刀釘在城門木板上示眾三天,三天過后,便連同其他犧牲者,一齊拋入屈原所稱贊的清流里喂魚吃了。”
提到屈原之死,或與其文化背景有關,屈原是楚文化的代表,湘西是巫儺文化的發源地。沈從文從小就受到鬼神的影響并參與其中,所以他作品中的人物往往帶有鬼神文化氛圍的印記,具有神性特征。例如,他經常引用古苗族民間傳說作為題材。他的許多小說都取材于人們熟悉的湘西傳說和故事,描繪了神秘的楚巫文化和浪漫的古典情調,充滿詩意。從沈從文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湘西世界存在著狂歡和瘋狂。他作品中的人物往往處于狂歡狀態,進入一種忘我的狀態,脫離一切世俗的規則。這種神秘的場景,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沈從文想要宣揚的“神性”。在作品中讓人物無私地追求自己喜歡和想要的東西,展現出巫神的精神內涵,那就是蔑視一切外在的規則,尋求內心的釋放。
在這樣一條河流上,自然力量以常常激發人的悲哀為特征,其河水湯湯的幻滅和孤獨又有“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之感,一切在死亡面前展現原形,本體的探詢與感受無處遁形。“屈原”與“特派員”之死,某種程度是類似的,他們的選擇都是自我意識的充分顯露,是一種理性的情感抉擇,而非一時的沖動或者迷信的盲從,又如王夫之所說:“惟極于死以為態,故可任性孤行。”
三、審美表達:語言在自然中的構建與消解
維特根斯坦認為:“美學之謎是各門藝術對我們發生作用之謎。”藝術并非私人的心理,它是公共的游戲。游戲雖無規律,卻有參加者必須遵守的規則。而藝術的這種規則,是與一定的生活和文化緊密相連的。維特根斯坦說,為了明白審美表達,必須描述生活方式。
在《鴨窠圍的夜》中,出現各種描述聲音的場景和語句:“鋼鉆頭敲打著沿岸大石頭,發出好聽的聲音。”“這時節岸上船上都有人說話,吊腳樓上且有婦人在黯淡燈光下唱小曲的聲音,每次唱完一支小曲時,就有人笑嚷。什么人家吊腳樓下有匹小羊叫,固執而且柔和的聲音。使人聽來覺得憂郁。”“羊還固執地鳴著。遠處不知什么地方有鑼鼓聲音,那一定是某個人家禳土酬神還愿巫師的鑼鼓。聲音所在處必有火燎與九品蠟照耀爭輝。”“我所看到的仿佛是一種原始人與自然戰爭的情景。”動物聲、人們交談說話聲、婦人的歌聲、工具聲……那種聲音與光明,正為著水中的魚和水面的漁人生存的搏戰,已在這河面上存在了若干年,無不交織形成了一首富有節奏和韻律的和諧自然的贊歌。
而《過新田灣》中則有著名的鄉野景色的描寫:“河水已平,水流漸緩,兩岸小山皆接連如佛珠,觸目蒼翠如江南的五月。竹子、松、杉,以及其他常綠樹皆因一雨洗得異常干凈。山谷中不知何處有雞叫,有牛犢叫,河邊有人家處,屋前后必有成畦的白菜,作淺綠色。小埠頭停船處,且常有這種白菜堆積成A字形,或相間以紅蘿卜。”通過描寫鮮明的綠色、紅色,用最鮮明的部分來組成畫面,調動感官的知覺,勾勒出湘西的瑰麗,用河岸與田間的景色帶給讀者視覺上的沖擊力和明媚秀麗的強烈的美感,完成用視覺對沖達到新鮮景色個人感知上的真實。
“感知的真實”代替了推理和感覺,使人思考性的痕跡,主觀的情感甚至也不見了,完全融合在客觀的景物之中。
這樣的自然景色中,沈從文給夫人寫的信當中曾表示語言無法抵達那樣的場景,即使是聲音也無法用文字比擬,“使一個身臨其境的人,想用一組文字去捕捉那點聲音,以及捕捉在那長潭深夜一個人為那聲音所迷惑時節的心情,實近于一種徒勞無功的努力”。正是王夫之所說的“撐開說景者,必無景也”。語言可以建構感知的真實,但無法捕捉意境的靈動,在宏大的自然景觀之中,語言的意義被消解。
四、審美意義:“人的自然化”的消解與融合
通過對河流意象的解讀和《湘行散記》中對自然景致的語言描寫鑒賞,我們大致可以看出沈從文作品里提到人與自然關系的兩個層次:一是人與自然環境、自然生態的關系,二是把自然景物和景象作為欣賞、歡娛的對象。
在湘西世界中,地理的偏隅使得人們沒有辦法跟隨時代的腳步,與自然的抗爭仍然是日復一日的生存主題,但反而保留了質樸,人與人之間古樸的關系反映了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他們生活在自己的悲哀與苦樂之中。
而對湘西雋秀景色的大量描寫也是《湘行散記》的亮點之一,但是沈從文自己也坦言,無法盡興描繪景色之幽深曠然,語言在自然中消解。
“我縱有筆有照相器,這里的一切顏色,一切聲音,以至于由于水面的靜穆所顯出的調子,如何能夠一下子全部捉來讓你望到這一切,聽到這一切,且計算著一切,我嘆息了。我感到生存或生命了。”
這里的“生存”“生命”則是沈從文散文中對于人與自然關系理解的第三個層次,人的身心節律與自然節律相吻合呼應,而達到與天合一,或者說與自然合一的境界。在的現代語境下,沈從文試圖重建人物精神與自然精神的深度契合,他筆下的人既是社會的存在,又是自然的存在。但在自然中,體悟到景色的優美,人與自然的聯結,消解了自我的社會意義,從而達到“天人合一”的與自然同在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