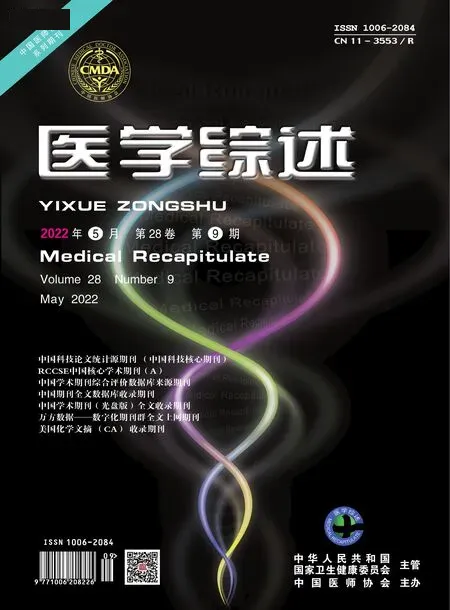鐵代謝與神經系統炎癥反應相關性研究進展
王建君,廖君,郭丹
(湖南中醫藥大學,長沙 410208)
神經系統炎癥反應是神經系統對外界刺激的一種防御性反應,也是中樞神經系統疾病損傷最常見的病理機制。神經系統炎癥反應涉及神經膠質細胞(主要是小膠質細胞和星形膠質細胞)的激活、炎癥因子、趨化因子的釋放等,與神經系統疾病的發生發展密切相關[1]。小膠質細胞是中樞神經系統的免疫細胞,是抵御外界刺激的第一道防線。星形膠質細胞作為血腦屏障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小膠質細胞共同介導神經系統炎癥反應。
鐵是人體內最豐富的微量元素,在神經系統中,鐵參與兒茶酚胺神經遞質的合成、髓鞘的形成以及突觸的重塑等[2]。因此,鐵穩態是維持神經系統正常功能的關鍵。有研究發現,神經炎癥誘導細胞內鐵聚集、神經元壞死及凋亡,藥物靶向干預則能有效治療疾病及繼發性損傷[3-4]。因此,深入探討神經炎癥與鐵代謝相互作用機制及共同靶點,有利于開發安全高效防治神經系統疾病的新型藥物。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kappa B,NF-κB)、骨形態發生蛋白(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BMP)6可能是神經炎癥與鐵代謝相互調節的共同靶點,對其進行深入研究可能為進一步探討神經炎癥反應與鐵代謝紊亂的相互作用機制、相關分子靶點及有效藥物研究等提供理論依據。現對小膠質細胞和星形膠質細胞介導的神經系統炎癥、鐵代謝的相關性研究進展予以綜述。
1 膠質細胞與神經系統炎癥
1.1小膠質細胞 小膠質細胞源于卵黃囊衍生的胚胎巨噬細胞,發育階段遷移至中樞神經系統,被視為中樞神經系統巨噬細胞。小膠質細胞在維持內環境穩態、修復損傷、防御病原體侵襲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5]。感染、缺血缺氧等刺激使小膠質細胞由靜息狀態變為活化狀態,其形態由分枝狀轉變為阿米巴狀;小膠質細胞極化為兩種表型M1型(促炎型)和M2型(抗炎型)[6]。M1型小膠質細胞釋放多種促炎性細胞因子,如白細胞介素(interleukin,IL)-6、IL-1β、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一氧化氮、活性氧等;M2型小膠質細胞則釋放抗炎性細胞因子,包括IL-4、IL-3、IL-10和轉化生長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等[7-8]。小膠質細胞作為中樞神經系統重要的免疫細胞,是介導神經系統炎癥反應的關鍵,可參與許多神經系統疾病的發生發展,如阿爾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以β淀粉樣蛋白(β-amyloid protein,Aβ)沉積及神經原纖維纏結為特征,患者認知功能減退為主要表現的神經退行性疾病。AD中Aβ沉積可激活小膠質細胞釋放炎癥介質,誘發神經炎癥反應[9-10]。腦卒中后小膠質細胞激活,分泌促炎性細胞因子加重神經元損傷,同時也清除損傷組織[11-12]。M1型小膠質細胞促炎加重損傷,M2型小膠質細胞抑炎則對腦組織發揮保護作用,小膠質細胞的不同表型可決定神經炎癥的轉歸,影響預后。因此,干預小膠質細胞極化表型有助于抑制炎癥反應,保護神經系統功能。小膠質細胞的激活由多種通路介導,如NF-κB[13]、Toll樣受體(Toll-like receptor,TLR)[14]、Janus激酶(Janus kinase,JAK)/信號轉導及轉錄活化因子(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STAT)[15]、促分裂原活化的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16]等,因此,針對不同靶點進行干預,誘導M2型小膠質細胞活化,可抑制神經系統炎癥反應,保護受損組織。
1.2星形膠質細胞 星形膠質細胞是中樞神經系統數量最多的膠質細胞,可通過調節、激活其他免疫細胞干預神經系統炎癥反應[17]。星形膠質細胞的功能包括參與突觸生成、調節離子穩態、信號轉導及能量代謝等[18]。星形膠質細胞參與神經系統疾病(如AD、帕金森病、亨廷頓病和肌萎縮側索硬化癥)的繼發性炎癥損傷病理過程[19-20]。被激活的星形膠質細胞在疾病不同階段發揮促炎或抗炎作用,調節血腦屏障通透性和小膠質細胞狀態[21]。炎癥發生時,星形膠質細胞胞體肥大,分泌膠質纖維酸性蛋白,形成膠質瘢痕;反應性星形膠質細胞分泌細胞外基質,增強細胞間連接,阻止免疫細胞的遷移[22];繼而分泌趨化因子,如CC趨化因子配體2、CXC趨化因子3配體1、CC趨化因子配體5、CC趨化因子配體6等[23]和細胞因子(IL-4、IL-10、TGF-β等)形成分子屏障[24],抑制谷氨酸神經毒性,保護神經元[25]。星形膠質細胞活化型為A1型(促炎)和A2型(抗炎),其“兩面性”受多巴胺D2受體表達的調控[26]。星形膠質細胞在炎癥反應中雖不占主導地位,但在血腦屏障和小膠質細胞調控炎癥反應過程中發揮了協同作用。因此,合理利用星形膠質細胞的抗炎及協同作用,可作為未來治療神經系統炎癥性疾病的新思路。
神經系統炎癥反應指中樞神經系統中小膠質細胞和星形膠質細胞激活的免疫應答以及一系列復雜的病理生理過程。神經系統炎癥是神經退行性病變、腦缺血損傷等發生發展的重要病理機制。小膠質細胞和星形膠質細胞介導的神經炎癥具有以下共同特征:①“雙重性”,激活后的不同表型起到“促炎”或“抑炎”作用;②神經系統炎癥反應是小膠質細胞和星形膠質細胞共同作用的結果;③不同類型的炎癥介質通過不同信號通路介導炎癥反應[27](表1)。因此,在神經系統疾病中,調控炎癥相關分子靶點,抑制促炎信號激活,誘導小膠質細胞和星形膠質細胞由促炎向抑炎表型轉化,對保護神經元以及促進疾病愈合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2 機體內鐵代謝機制
鐵是人體內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參與血紅蛋白生成、細胞色素和各種酶的合成。細胞內鐵獲取有兩種途徑:非轉鐵蛋白結合鐵(nontransferrin-bound iron,NTBI)和轉鐵蛋白結合鐵攝取途徑,NTBI通過

表1 神經系統炎癥中小膠質細胞與星形膠質細胞的表型
與細胞膜上的二價金屬離子轉運體1(divalent metals transport 1,DMT1)結合,而轉鐵蛋白結合鐵則與轉鐵蛋白受體(tansferrin receptor,TfR)作用[32]。肝臟(肝細胞)和脾臟(脾巨噬細胞)是鐵儲存的重要器官,根據機體需要通過膜鐵轉運蛋白(ferroportin,FPN)調節鐵代謝[33-34]。
鐵調素是調控機體內鐵離子的關鍵調節分子,鐵調素通過鐵調素-FPN軸內化降解FPN,調控全身鐵穩態[35]。炎癥反應、缺氧、紅細胞生成不足、溶血等均可增加鐵調素表達。調控鐵調素的信號通路主要包括BMP6/Smad通路、JAK/STAT通路等。BMP6由肝竇內皮細胞產生[36],當體內鐵水平升高,BMP6與BMPⅠ型和Ⅱ型受體結合,Smad1/5/8磷酸化,并轉移至細胞核內[37]。同時,BMP6通過旁分泌作用于與糖基磷脂酰肌醇相連的膜蛋白——鐵調素調節蛋白(hemojuvelin,HJV)。HJV作為BMP6的共受體進一步激活肝細胞Smad信號通路,促進鐵調素表達,引起細胞內鐵聚集[38]。因此,HJV/BMP/Smad通路是調控鐵調素分泌,增加腸道鐵吸收,維持機體鐵穩態的關鍵[39]。轉鐵蛋白是輸送鐵離子的重要載體,儲存在肝臟的Fe3+與轉鐵蛋白結合形成Fe3+-轉鐵蛋白復合物[33]。Fe3+-轉鐵蛋白與TfR結合介導穿過血腦屏障進入神經系統[40],其他通路還包括乳鐵蛋白/乳鐵蛋白受體通路、黑色素轉鐵蛋白通路[41-42]。中樞神經系統內鐵離子參與呼吸鏈電子傳遞、神經纖維髓鞘及神經遞質的合成[43]。細胞質和溶酶體、線粒體等細胞器中存在不穩定鐵池,過量游離鐵通過芬頓反應(即Fe2++H2O2→Fe3++HO-+·HO)生成大量活性氧,導致細胞損傷[44]。近年研究發現,鐵離子聚集是導致神經系統疾病損傷的重要病理機制之一,如腦缺血后鐵超載及氧化應激誘導線粒體損傷,加重腦缺血繼發性損傷[45-46]。磁共振成像顯示,AD患者腦組織中鐵含量升高[47],而腦內鐵聚集加速Aβ蛋白沉積[48],Aβ聚集誘導Fe3+還原為Fe2+,大量活性氧生成[49]。因此,抑制細胞內鐵聚集,可減少活性氧的生成,保護神經元。
3 神經炎癥反應與鐵代謝相關性
神經系統炎癥與鐵代謝存在相關性:①鐵離子聚集和以小膠質細胞活化為特征的慢性神經炎癥均為神經疾病的重要損傷機制。②炎癥刺激可增加神經元FPN表達,引起鐵聚集[50-51];鐵聚集也可誘導小膠質細胞促炎性細胞因子進一步釋放,加重神經炎癥損傷[52]。③鐵螯合劑干預可減少神經元內游離鐵,同時抑制部分炎癥因子的表達[53]。由此表明,炎癥反應可誘導鐵過載,催化活性氧;同時,鐵聚集可促進炎癥反應,加重損傷。炎癥反應和鐵代謝在神經系統疾病中相互關聯,但其相關性機制及靶點報道較少。因此,從小膠質細胞、星形膠質細胞、炎癥與鐵代謝相關信號通路及藥物靶向干預等方面探討兩者的相關性可能為藥物治療神經系統炎癥性疾病提供理論依據及治療靶點。
3.1小膠質細胞介導的炎癥反應與鐵代謝 小膠質細胞在介導炎癥反應的同時還參與調節鐵代謝。鐵代謝相關蛋白(鐵調素、DMT1、TfR、鐵蛋白、FPN)在小膠質細胞內均有表達,炎癥刺激可調節上述蛋白的表達[51,54];激活狀態下不同表型小膠質細胞鐵代謝相關蛋白的表達存在差異,M1型小膠質細胞中,鐵代謝通過NTBI途徑增加胞質中DMT1、鐵蛋白表達;而M2型小膠質細胞則主要參與轉鐵蛋白結合鐵途徑的鐵代謝,表現為TfR水平上調,引導自身調節,發揮抗炎效應[55]。非甾體抗炎藥阿司匹林可顯著降低TfR1,增加FPN1和鐵調素的表達,維持小膠質細胞鐵穩態。由此推測,神經炎癥發生時,小膠質細胞激活也啟動鐵代謝調節,通過不同表型促進炎癥反應或調節鐵穩態反饋抑制炎癥。
AD模型中,鐵離子通過增加Aβ生成激活NF-κB信號通路,進而增加小膠質細胞內IL-1β的表達[56]。小鼠認知功能障礙模型中,鐵螯合劑去鐵胺可抑制小膠質細胞的激活,減輕術后炎癥反應,改善氧化應激,保護神經元[57];小膠質細胞作為神經系統重要的免疫細胞,通過介導炎癥反應激活鐵代謝途徑,引起細胞內鐵過載,導致神經元損傷,加重疾病損傷;而細胞鐵代謝紊亂亦可引起細胞促炎表型極化,加重炎癥反應。因此,神經系統炎癥反應與鐵代謝紊亂具有交互作用,探究炎癥反應與鐵代謝間的關鍵靶點對神經系統疾病定向干預治療起至關重要的作用。
3.2星形膠質細胞介導炎癥反應與鐵代謝 星形膠質細胞參與血腦屏障的構成,血腦屏障調控血管與腦組織之間物質轉運,是維持中樞神經系統內環境穩定的結構基礎。NTBI是星形膠質細胞的主要鐵來源,高濃度NTBI條件下,谷氨酸釋放會促進突觸吸收Fe2+,而星形膠質細胞通過釋放信號肽調控鐵離子的血腦屏障通過率,進而抑制鐵吸收[58]。星形膠質細胞協同小膠質細胞起到抗炎作用,并具有細胞內鐵調控作用。研究表明,炎癥反應中小膠質細胞活化,促炎性細胞因子(主要是IL-6)表達誘導星形膠質細胞激活,產生鐵調素,降解FPN,阻止鐵離子進入神經元[59]。神經系統炎癥及神經退行性疾病中,活化的星形膠質細胞使鐵調素表達增加,緩沖過多的鐵離子,從而保護神經元免受鐵超載損傷[60]。由此可見,“小膠質細胞-星形膠質細胞-神經元”的細胞網絡在中樞神經鐵代謝調控中具有重要作用。綜上所述,在神經系統炎癥反應中,星形膠質細胞通過抑制鐵離子穿過血腦屏障及增加星形膠質細胞的鐵吸收,緩解中樞神經內的鐵聚集,保護神經元。
3.3神經炎癥與鐵代謝相關性信號通路 JAK/STAT是多種細胞因子和干擾素作用的信號轉導通路,不僅可作為應激反應的炎癥通路,也是鐵調節的重要信號途徑。炎癥因子(如IL-6、IL-1β)可激活JAK/STAT,引起細胞核內DNA的Smad結合元件與鐵結合元件結合,調控鐵調素[61-64]。小膠質細胞膜高表達TLR,在先天免疫和炎癥中發揮重要作用。TLR介導的信號通路,特別是TLR1/2、TLR4介導的信號通路可加重神經系統炎癥反應[65-66]。研究發現,TLR4/髓樣分化因子88(myeloid differentiation factor 88,MyD88)信號通路可促進下游炎癥因子IL-6的表達,誘導STAT3磷酸化,STAT3信號通路的激活可促進鐵調素表達,最終抑制細胞內鐵離子外流,加重神經系統的鐵過載損傷[67]。在肝細胞及巨噬細胞內,炎癥因子IL-1β通過依賴性MyD88激活NF-κB,誘導STAT3信號通路調控鐵調素[68]。因此,炎癥相關信號通路JAK/STAT、TLR4/MyD88、NF-κB可通過干預鐵調素分泌調節細胞鐵代謝。
鐵代謝紊亂可誘導炎癥因子釋放。研究發現,Fe2+通過活性氧-p38 MAPK信號通路促進炎癥反應[69];小膠質細胞鐵超載能激活NF-κB信號通路,分泌IL-1β和TNF-α,表明鐵代謝是神經炎癥的重要觸發因素[70]。BMP6通過激活Smad調控轉錄,干預鐵調素生成,其廣泛表達于小膠質細胞、星形膠質細胞、神經元內[71],是維持細胞內鐵穩定的關鍵信號分子。在巨噬細胞中,BMP6可促進炎癥因子(如IL-6、誘導型一氧化氮合酶、TNF-α)的表達[72]。因此,NF-κB和BMP6可能是神經系統疾病炎癥及鐵聚集相互作用的重要靶點,見圖1。被激活的小膠質細胞及星形膠質細胞釋放炎癥因子,導致神經系統內鐵水平改變,而鐵代謝失衡進一步加重炎癥反應。因此,探討神經系統疾病中炎癥反應與鐵代謝的發生順序有助于明確疾病防治的有效時間窗,并通過針對性靶點干預提高治療效果;進一步研究炎癥與鐵代謝之間的網絡信號調控機制將為神經系統疾病的治療提供新的有效治療靶點。
4 靶向性干預炎癥反應及鐵代謝治療神經系統疾病相關研究
炎癥反應與鐵代謝是神經系統疾病發生發展的重要病理機制,通過藥物靶向干預能有效治療神經系統疾病。人參皂苷及其化合物通過誘導M2型小膠質細胞極化抑制炎癥進程,促進炎癥消退[73];紫檀芪(一種白藜蘆醇提取物)通過靶向干預NF-κB磷酸化,減輕缺血再灌注損傷后星形膠質細胞炎癥反應及神經元氧化損傷[74]。去鐵酮[75]、去鐵胺[76]、地拉羅司[77]等鐵螯合劑已被廣泛用于鐵超載導致的神經系統損傷的治療。目前,抑制神經系統炎癥的同時調節鐵代謝可達到更好的治療疾病的效果。鐵螯合劑乳鐵蛋白干預星形膠質細胞炎癥反應,同時抑制DMT1、TfR上調,能改善PD小鼠運動功能障礙[54]。丹參酮ⅡA通過抑制NF-κB核易位下調DMT1、鐵調素,增加FPN1表達,減輕鐵超載,具有抗氧化及抑制炎癥損傷的作用[78-79]。Zhang等[80]研究證明,淫羊藿、黃芪和葛根的有效成分組方后可以有效降低轉基因小鼠腦鐵水平,并降低腦內IL-6、IL-1β和TNF-α表達,有效改善腦內氧化應激,對AD起治療作用。因此,匯總現有相關治療方法和藥物,可進一步開發神經系統炎癥及鐵代謝的靶向藥物,為中樞神經疾病的治療提供新思路(表2)。

注:TLR為Toll樣受體,MyD88為髓樣分化因子88,IRAK為白細胞介素受體相關激酶,TRAF為腫瘤壞死因子受體相關因子,TNF為腫瘤壞死因子,TNFRs為腫瘤壞死因子受體,NIK為誘導激酶,IKKs為IκB激酶,IκBs為核因子κB抑制蛋白,NF-κB為核因子κB,IL為白細胞介素,IL-6R-α為白細胞介素-6受體α,JAKs為Janus激酶,STAT為信號轉導及轉錄活化因子,BMP為骨形態發生蛋白,HJV為鐵調素調節蛋白,BMPR為骨形態發生蛋白受體,Smad為Smad家族蛋白,BMP-RE為BMP結合元件,NTBI為非轉鐵蛋白結合鐵,DMT1為二價金屬離子轉運體1,FPN為膜鐵轉運蛋白,hepcidin為鐵調素

表2 干預鐵代謝與炎癥反應治療神經系統疾病
5 小 結
中樞神經疾病常繼發炎癥反應,小膠質細胞、星形膠質細胞被激活,炎癥因子、趨化因子釋放;同時神經元、小膠質細胞、星形膠質細胞內鐵代謝相關蛋白表達異常,鐵離子聚集。炎癥反應與鐵聚集互相促進并加重神經系統損傷。闡明神經系統炎癥反應及鐵代謝紊亂的病理機制,有助于通過抑制炎癥及干預鐵代謝防治神經系統疾病。NF-κB及BMP6可能是神經系統炎癥反應與鐵代謝網絡調控的關鍵靶點,為神經系統炎癥和鐵代謝紊亂導致的繼發性損傷治療提供了新思路,并為安全高效的新藥開發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