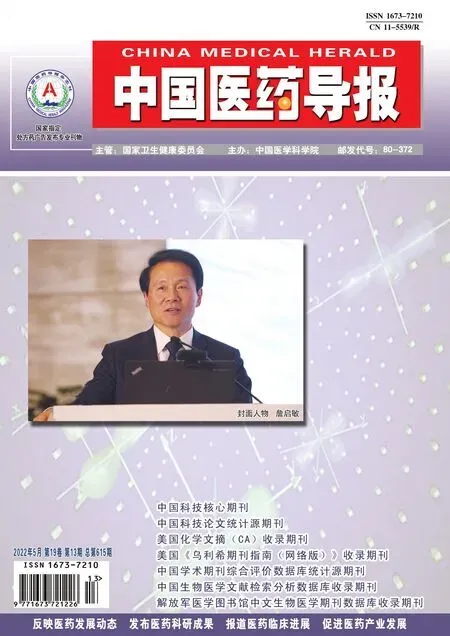早期腸內-腸外聯合營養對顱內血腫清除術后氣管切開患者的應用效果
馬炬俠 陳 麗 王瑞杰 佟玲玲
安徽省阜陽市第二人民醫院神經外科,安徽阜陽 236008
顱內血腫是腦出血患者的常見并發癥,可威脅生命[1-5],臨床上通常采取術后氣管切開等方式,維持患者呼吸的順暢[6]。既往臨床上主要關注顱內血腫清除術后氣管切開患者的呼吸道狀況及氣道干預[7-8],對于其營養干預的研究相對較少,而事實上,營養不良是腦出血患者的常見并發癥,故選擇合適的營養干預方式對于患者的預后改善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目前,單純腸內營養、單純腸外營養與腸內-腸外聯合營養三種類型各有利弊。本研究分析了三種營養干預方案的干預效果。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前瞻性選取2018 年6 月至2019 年12 月安徽省阜陽市第二人民醫院收治的78 例顱內血腫清除術后氣管切開患者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①頭顱影像學檢查確診為腦出血伴顱內血腫;②入院后存在不同程度的昏迷,格拉斯哥昏迷(Glasgow coma scale,GCS)[9]評分為3~8 分;③發病24 h 內行顱內血腫清除術,之后行氣管切開術。排除標準:①既往有消化道疾病史或既往消化道手術史;②合并嚴重影響營養代謝的疾病;③近3 個月內服用非甾體抗炎藥、糖皮質激素、免疫抑制劑等;④術前血白蛋白(albumin,ALB)水平<30 g/L;⑤凝血功能障礙。本研究獲得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的批準,所有患者均簽署知情同意書。將納入本研究的受試者進行隨機編號,隨機確定抽樣的起點和抽樣的順序,分別設為腸外組、腸內組和聯合組,各26 例。三組性別、年齡、體重、顱內血腫切除術的手術途徑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

表1 三組一般資料比較
1.2 治療方法
所有受試者接受顱內血腫清除術,術后行氣管切開,除了營養干預方式不一樣外,其他治療原則一致。采用Harris-Benedict 公式、Clifton 公式分別計算每日的基礎能量消耗(basal energy expenditure,BEE)、靜息能量消耗(rest metabolic expenditure,RME),然后計算出每日的熱能需要量(kcal/d)=BEE×RME[10]。
各組術后營養干預方式。①腸外組:接受單純腸外營養干預,經外周或中心靜脈導管輸注營養液(糖/脂肪的熱量比為1∶1),適當補充維生素、微量元素、水和電解質等。②腸內組:在術后第1 天開始給予單純腸內營養干預,通過鼻胃管輸注腸內營養液(商品名:能全力,紐迪西亞制藥公司),在1 周達到全部熱量,靜脈用藥僅補充電解質、生理鹽水、維生素、微量元素等,無糖類、脂肪、蛋白質等。③聯合組:術后同時給予腸內和腸外營養,其具體干預方法同腸內組、腸外組。
1.3 觀察指標
分別于營養干預前、干預后10 d 進行以下指標的評價。
1.3.1 營養狀況 收集靜脈血3~5 ml,將血樣經過室溫靜置(20 min)后,1500 r/min 離心15 min,分離血清后,經全自動生化分析儀檢測外周血總蛋白(total protein,TP)、前白蛋白(prealbumin,PA)、ALB、轉鐵蛋白(transferrin,TRF)等營養狀況相關指標水平。
1.3.2 免疫功能 收集靜脈血3~5 ml,放射免疫分析法檢測外周血免疫球蛋白(immunoglobulin,Ig)A、IgM、IgG 等水平。采用非平衡法,將試管進行編號,根據說明書依次加樣,混勻,室溫放置20 min,3500 r/min 離心25 min,測定沉淀放射性計數,預編程序計算相關參數和樣品濃度。
1.3.3 短期預后 所有患者干預前后接受GCS 評分,統計不良事件發生情況、住院時間。GCS 量表主要包含睜眼反應、語言反應及肢體動作三項。三項評分之和為最后得分,>14 分為正常,13~14 分為輕度昏迷、9~12 分為中度昏迷、3~8 分為重度昏迷,得分越低,昏迷程度越嚴重。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3.0 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多組間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兩兩比較采用LSD-t 檢驗。計數資料采用例數和百分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兩組比較采用Bonferroni 方法校正,檢驗水準為0.02。以P <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三組干預前后的免疫水平比較
三組干預前TP、PA、ALB 與TRF 水平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0.05)。三組干預后血TP、PA、ALB與TRF 水平均高于干預前(P <0.05)。聯合組干預后血TP、PA 與TRF 水平均高于腸外組,血PA、TRF 水平均高于腸內組(P <0.05);腸內組干預后血PA、TRF水平均高于腸外組(P <0.05)。見表2。
表2 三組干預前后的免疫水平比較()

表2 三組干預前后的免疫水平比較()
注 與本組干預前比較,aP <0.05;與腸外組比較,bP <0.05;與腸內組比較,cP <0.05。TP:總蛋白;PA:前白蛋白;ALB:白蛋白;TRF:轉鐵蛋白
2.2 三組干預前后免疫狀況比較
三組干預前IgM、IgG、IgA 水平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0.05)。三組干預后血IgM、IgG、IgA 水平均高于干預前(P <0.05)。聯合組干預后血IgM、IgG、IgA 水平均高于腸外組,血IgM、IgA 水平均高于腸內組(P <0.05);腸內組干預后的血IgA 水平均高于腸外組(P <0.05)。見表3。
表3 三組干預前后免疫狀況比較(mg/L,)

表3 三組干預前后免疫狀況比較(mg/L,)
注 與本組干預前比較,aP <0.05;與腸外組同期比較,bP <0.05;與腸內組同期比較,cP <0.05。IgA:免疫球蛋白A;IgM:免疫球蛋白M;IgG:免疫球蛋白G
2.3 三組患者的臨床預后比較
三組干預前GCS 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0.05)。三組干預后GCS 評分均高于干預前(P <0.05)。三組消化道不耐受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0.05)。聯合組上消化道出血發生率低于腸外組(P <0.02)。聯合組總住院天數短于腸外組和腸內組(P <0.05)。見表4。

表4 三組患者的臨床預后比較
3 討論
腦出血并發顱內血腫患者多存在不同程度的營養不良與免疫力減退,組織分解代謝速度加快、能量消耗增加,容易出現營養缺乏現象[11-12]。單純的腸外營養會引起腸道黏膜萎縮的現象,不僅延緩了胃腸道功能的恢復,同時也破壞了腸道的生理屏障,增加了感染發生的風險[13-14]。腸內營養的實施情況更加有助于對腸道黏膜屏障功能的保護[15-16]。但迄今為止,腸內營養的應用時機和應用方式尚未有明確的標準[17-20]。腸內-腸外聯合營養方式是目前常用的營養干預方法[21-24],兼具腸內、腸外營養的優勢,術后患者營養干預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較高,消化道黏膜損傷、胃腸道不耐受等不良反應的發生率較低[25-27]。
本研究顯示,三種營養干預方法的應用均能夠使患者術后的免疫功能與營養狀況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早期腸內-腸外聯合營養對免疫功能和營養狀況改善的整體效果最為突出,優于單純腸內或腸外營養者。關于術后腸內營養的開始時間目前仍然存在一定爭議[28-29]。腸內營養可以在術后24 h 以內開展,但應關注劑量和速度。聯合營養方式的早期應用能夠降低消化道不耐受的發生率,兼顧患者胃腸道黏膜的實際情況。本研究將腸內-腸外營養的能量供應初始比例設置為1∶3,以腸外營養為主,逐步增加腸內營養的比例,伴隨營養干預的進展,術后7 d 左右,腸內-腸外營養的能量供應比例能夠達到1∶1,實現腸內-腸外營養的基本均衡。聯合組患者術后胃腸道不耐受的發生率僅為3.8%,低于腸內組的11.5%,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0.05)。上消化道出血是顱內血腫微創清除術后的最常見并發癥之一,可能與交感神經麻痹引起胃黏膜淤血、迷走神經過度活躍導致胃腸道就不缺血、胃蛋白酶過度分泌等多個因素有關[15]。本研究顯示聯合組上消化道出血發生率低于腸外組、住院總天數短于腸外組和腸內組(P <0.05),這可能是由于腸內營養符合正常的生理過程,中和、稀釋胃酸,提高胃液的pH 值,促進胃黏膜的修復,降低促胃液素的含量,并能促進腸道蠕動,更快恢復腸道的吸收功能,維持胃腸道黏膜的完整性與內臟血流的穩定性,減少上消化道出血的發生,加快術后康復,促進早日出院。
綜上所述,早期腸內-腸外聯合營養能顯著改善顱內血腫清除術后氣管切開患者術后免疫功能與營養狀況,降低上消化道出血的發生風險,縮短住院時間,值得臨床推廣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