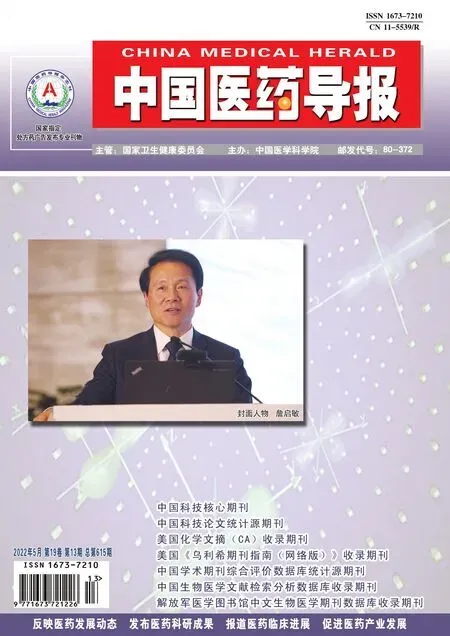疏肝健脾針刺法對腫塊型肉芽腫性小葉性乳腺炎患者免疫功能的影響
胡 珊 劉昱磊 陳鵬典 陳 妍 王俊玲 寧 艷
南方醫科大學附屬深圳婦幼保健院中醫科,廣東深圳 518028
肉芽腫性小葉性乳腺炎(granulomatous lobular mas titis,GLM)是一種發生在乳腺的良性炎癥性疾病,現代研究對本病的病因及發病機制并沒有清晰的認識,普遍以為GLM 的發病與炎癥反應和自身免疫相關。研究發現[1],本病患者血清中T 淋巴細胞、免疫球蛋白及補體水平等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變化,并認為免疫系統紊亂直接影響了本病的預后。激素治療取得一定的療效,這也驗證了免疫紊亂可誘發本病的觀點,但長期使用激素,輕則出現肥胖、痤瘡、月經不調等不良反應[2],重者可并發庫欣綜合征、多毛癥及血糖異常等疾病,且部分患者停藥后出現病情反復甚至加重的情況[3-4]。手術局部切除復發率高,容易出現廣泛的增生性瘢痕、切口愈合延遲和乳房變形等后遺癥,因此也不作為常規治療方法[5]。研究顯示[6],GLM 在自身免疫系統的作用下有一定的自限性。因此,也有學者[7-8]認為,臨床隨訪觀察和無創治療可作為治療本病的首選方案,但本方案存在一定風險,可能會加重病情,也不適用于膿腫范圍大的患者,且隨著人們對健康的要求越來越高,患者多不接收觀察療法。
中醫學注重整體觀念,以調節機體功能恢復平衡為主要目的,針刺具有不良反應小、操作方便等優勢。大量臨床研究表明[9-12],針灸具有改善機體免疫功能的作用,本研究在前人研究基礎上,采用疏肝健脾針刺法治療,觀察該方法對腫塊型GLM 患者免疫功能的影響。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9 年3 月至2021 年1 月南方醫科大學附屬深圳婦幼保健院中醫科門診及乳腺科門診就診的腫塊型GLM 患者80 例作為受試對象,均為女性,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分為對照組和治療組,每組各40 例。治療組年齡24~41 歲,平均(31.72±5.64)歲;病程20~52 d,平均(24.37±9.10)d。對照組年齡26~40 歲,平均(30.98±6.17)歲;病程27~49 d,平均(26.15±7.63)d。兩組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經南方醫科大學附屬深圳婦幼保健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核批準(批號:SZFZ2018046)。
1.2 診斷標準
1.2.1 西醫診斷 病理學診斷參照《乳腺病理診斷和鑒別診斷》[13]制定:以乳腺小葉為中心的肉芽腫性炎癥,病灶呈結節狀、多灶性分布;病變小葉的結構(末梢導管或腺泡)大部分萎縮或消失,病灶內可見多種炎癥浸潤,可伴有微膿腫形成,組織中可見導管擴張,并伴有導管炎癥。臨床癥狀參照最新制定的《非哺乳期乳腺炎診治專家共識》[14]:局部疼痛或無痛性腫塊,起病急,進展快,多自外周向中心蔓延,可全乳腫大;腫塊邊界欠清,無明顯波動感,可伴有結節性紅斑、關節疼痛、發熱、全身皮疹等乳腺外表現。
1.2.2 中醫診斷 符合《中醫外科學》[15]中瘡瘍及乳癰腫塊型的診斷標準:以乳房局部疼痛或無痛性腫塊為主,無明顯膿腫形成。腫塊邊界不清,質硬韌,伴或不伴紅熱,舌淡紅,苔薄白,脈弦細。
1.3 納入標準
①符合上述診斷標準;②知曉本研究用藥方案并簽署書面知情同意書;③凝血功能正常。
1.4 排除標準
①妊娠期;②合并其他乳腺疾病;③合并肝腎功能異常或血液疾病;④精神異常不能配合治療;⑤合并其他導致機體免疫指標改變的疾病;⑥其他危及生命的疾病。
1.5 治療方法
對照組:口服醋酸潑尼松片(廠家:山東魯抗醫藥集團賽特有限責任公司;生產批號:180713)治療,40 mg/次(5 mg/片),1 次/d,每周減量1 片,減至1 片時維持5 周停藥。
治療組:在對照組的基礎上予針灸治療,具體操作如下:取穴標準參照《針灸學》[16],取太沖、足三里、三陰交及乳房局部圍刺。操作:患者取仰臥位,暴露患側乳房及四肢,常規消毒后,合谷和太沖穴取1 寸毫針,其余穴位取1.5 寸毫針,進針方向與皮膚垂直,針刺手法以平補平瀉為主,以局部出現明顯酸、麻、脹感為度。留針30 min。1 次/d,連續治療5 d,休息2 d,此為1 個療程。共治療3 個月。
1.6 觀察指標
1.6.1 B 超檢測 腫塊3 徑平均值[(長+寬+深)/3)],并比較治療前后兩組患者3 徑平均值大小。
1.6.2 視覺模擬評分法(visual analogue scoring,VAS)比較兩組治療前后疼痛情況[17]:0 分,無疼痛;1~3 分,輕微疼痛;4~6 分,可忍受但影響睡眠的疼痛;7~10 分,不能忍受的疼痛。
1.6.3 血清T 淋巴細胞群、免疫球蛋白和補體水平 比較兩組治療前后患者血清T 淋巴細胞群(CD3、CD4、CD8)、免疫球蛋白(immunoglobulin,Ig)(IgG、IgA、IgM)和補體水平(補體C3、補體C4)。
1.7 療效判定標準
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行業標準制定的《中醫內科病證診斷療效標準》[18]中乳癰的療效評定標準:①治愈:全身癥狀及局部腫塊消失,瘡口愈合;②好轉:全身癥狀消失,局部腫痛減輕范圍減小,或瘡口好轉但尚未愈合;③無效:反復“傳囊”甚或形成乳漏。總有效率=(治愈+顯效+好轉)例數/總例數×100%
1.8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6.0 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表示,比較采用t 檢驗;計量資料用例數和百分比表示,比較采用χ2檢驗。以P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
治療組總有效率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0.05)。見表1。

表1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例(%)]
2.2 兩組治療前后乳房腫塊大小、VAS 評分比較
治療前兩組乳房腫塊大小、VAS 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意義(P >0.05)。治療后兩組乳房腫塊大小較治療前減小,且治療組小于對照組(P <0.05);治療后兩組VAS 評分較治療前降低,且治療組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意義(P <0.05)。見表2。
表2 兩組治療前后乳房腫塊大小、VAS 評分比較()

表2 兩組治療前后乳房腫塊大小、VAS 評分比較()
注 VAS:視覺模擬評分法
2.3 兩組治療前后血清T 淋巴細胞群CD3、CD4、CD8水平比較
治療前兩組血清免疫指標水平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0.05)。治療后兩組血清CD3、CD4 水平均低于治療前,且治療組低于對照組(P <0.05);治療后兩組血清CD8 水平高于治療前,且治療組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意義(P <0.05)。見表3。
表3 兩組治療前后血清T 淋巴細胞群CD3、CD4、CD8 水平比較(g/L,)

表3 兩組治療前后血清T 淋巴細胞群CD3、CD4、CD8 水平比較(g/L,)
2.4 兩組治療前后血清IgG、IgA、IgM、補體C3、補體C4 水平比較
治療前兩組血清免疫指標水平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0.05)。治療后兩組血清IgG、IgA、IgM、補體C3、補體C4 水平均低于治療前,且治療組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意義(P <0.05)。見表4。
表4 兩組治療前后血清IgG、IgA、IgM、補體C3、補體C4 水平比較(g/L,)

表4 兩組治療前后血清IgG、IgA、IgM、補體C3、補體C4 水平比較(g/L,)
注 Ig:免疫球蛋白
3 討論
近年來,GLM 的發病率逐年增加,就診率逐年攀升。關于本病的病因病機仍不明確,較為認可的是免疫學說[19-21]。據報道[22-24],GLM 病變組織中存在大量IgG4 陽性漿細胞和CD4 淋巴細胞浸潤,且在病變導管內彌漫炎癥反應中,可見大量CD3+、CD4+、CD8+細胞浸潤,并存在明顯的T 細胞亞群和細胞因子的失衡;部分患者對激素治療敏感,也證實免疫系統參與了疾病的發生發展,但長時間服用激素有不良反應大及復發率高等特點[3-4]。中醫將GLM 歸屬于“乳癰”“瘡瘍”范疇,其發病機制可總結為郁怒傷肝,肝氣郁結,郁久生火;肝郁傷脾,脾失健運,痰濕內生,以致氣郁、火郁、痰濕阻于經絡,氣血凝滯,結聚成塊。因此,疏肝健脾、散結消腫是治療的基本原則。針灸具有通經活絡、調理臟腑的作用,《外科啟玄》曰:“凡瘡瘍,皆由五臟不和、六腑壅滯,則令經脈不通而生焉。”因此,針灸在外科學中也得以廣泛應用。基于以上理論,本研究采用疏肝健脾針刺法治療GLM,以觀察該方案對GLM患者免疫功能的影響。
針灸治療免疫性疾病的報道已久,李檸岑所在團隊認為[25],針刺是通過體表的物理刺激,經穴位微環境中的神經、免疫細胞和化學物質應答,將信息通過經絡傳遞到靶器官,以達到通經脈、調節氣血陰陽治療疾病的目的,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三網聯動,以致中和”的針刺作用模式,認為穴位小網絡可將信息放大,在通過人體經絡大網絡(經絡網),作用于疾病網絡(病網絡),發揮針刺療效。這一過程與神經-內分泌-免疫等細胞間相互通訊密切相關。大量臨床研究也證實[9-12],針刺可改善患者血清免疫指標,平衡免疫功能。
本研究所選穴位為局部阿是穴圍刺配合太沖、足三里及三陰交,方義:局部消腫散結的同時充分體現了疏肝健脾的辨證論治配穴原則。從研究結果可得知,相對單純口服激素,針刺可顯著提高臨床療效,改善臨床癥狀。治療組腫塊范圍及疼痛評分小于對照組(P <0.05);與對照組比較,治療后治療組血清CD3、CD4 及血清IgG、IgA、IgM、補體C3、補體C4 明顯降低,CD8 明顯升高(P <0.05),由此得出結論,針刺可通過下調血清CD3、CD4 及血清IgG、IgA、IgM、補體C3、補體C4 水平,上調CD8 水平,平衡CD4/CD8 比值,從而抑制患者免疫功能過度應答,以達到控制炎癥反應的目的。
綜上所述,疏肝健脾針刺法可有效平衡機體免疫功能,改善臨床癥狀,提高臨床療效,其機制可能是通過穴位刺激調節神經-內分泌-免疫網絡發揮作用,后續將優化研究設計,引入動物實驗,進一步闡述針刺調節GLM 患者免疫功能的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