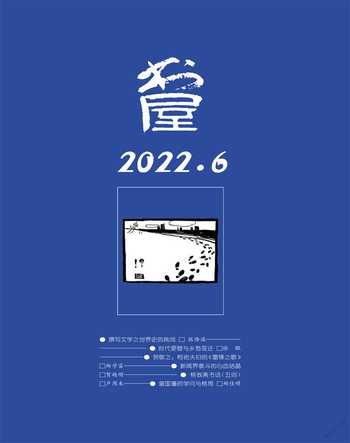2022年第6期書屋絮語
邵水游
突然想起辜鴻銘來,正好在書柜中翻到他的《中國人的精神》,書頁都泛黃了,應該是很多年以前買的原版,后來的翻譯本出來,也買來讀過,總覺得比起原版來有一層隔膜。林語堂曾評價辜氏“英文文字超越出眾,二百年來,未見其右。造詞、用字,皆屬上乘。總而言之,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異人之文采。鴻銘亦可謂出類拔萃,人中錚錚之怪杰”。但我印象最深的,還是他的《張文襄幕府紀聞》,文筆精致,行文典雅,敘事工整,言說完備。這么多年,不少人總是對傳統文化有誤讀,認為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文化阻礙了現代化的進程。隨著年齡的漸長,對這種看法有保留,而思想的底氣或許跟我對辜氏著作的閱讀與思考相關聯。傳統文化的價值中倫理、道德部分,依然是中華社會的內核,輕忽不得,不論是現代社會還是后現代社會。
讀秦燕春箋注的《思復堂遺詩》,心有余戚。陳卓仙乃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唐君毅的母親,她在《祭迪風文》中寫道:“吾君每言及孔孟學術垂絕,輒感慨欷歔。毅然以振起斯文自任,并以此教學子。授課時常常披肝裂肺,大聲疾呼,痛哭流涕,其苦心孤詣,我常為君抆淚。因以‘徒勞精力,于人何補之言勸君,君曰:倘能喚醒一人,算一人。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吾非智者,唯恐失人。吾不得已也。”近代以降,思想激變,傳統文化因外來文化的沖撞,損耗尤多;新文化運動啟動,再掀波瀾,又沖刷一遍。然萬變不離其宗,幾千年來的文明精粹依然留存于心,有識之士始終捍衛著傳統文化的價值,以禮當先,展現風度。書中附錄唐君實《母親給我們留下的教誨》一文,每次誦讀,可知老輩垂范,也略通自己父母的教導,尚能一一對應。
收到陳建軍新著《說不盡的廢名》,從中可見其治學態度與方法。廢名無疑是現代文學中一位有特色的作家,但個人更看重他一以貫之的君子風度與倫常表現,如何守住自己的本分乃至人格尊嚴,并將傳統文化的理念貫注于自己的言行和作品中,或許這才是個“說不盡”的話題。
又在書柜里翻出二本書,一本曾昭掄《緬邊日記》,一本丁文江《游記二種》。前者是抗戰期間由昆明到云南邊境實地考察的記錄,后者是到云南、貴州、湖南、山西等地考察地質、礦藏及民俗風情以及1933年到蘇聯實地考察的記錄,都是優美流暢的文字。想到辦公室書柜存有湖南教育出版社《丁文江全集》,應該去讀了。曾昭掄在書中寫道:“大理附近,很有幾塊有名的古碑。就中最出名的,一塊是元世祖碑,這碑就在城外不遠,上面記載元世祖征服大理的事跡;另一塊是南詔碑……古跡這樣多,可恨是本地一般無知的百姓們以為,古碑拿來煎水可以醫病。年深日久,敲碑者多,損壞很重。尤其可恨的,他們專愛敲有字的部分,說是效力最大。”敲碑毀字,無價的古跡就這般消弭于無形,后來者徒喚奈何。而丁文江的墓在風景優美的岳麓山上,雖不起眼,確是一個好歸處。那一代人走遠了,背影還在,傳統文化的根系會在這片土地上扎得更密更深。3FA4C0FF-2B1A-47A8-BBFA-EB7E822326D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