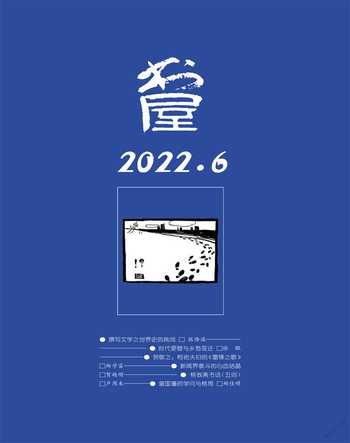“七絕圣手”王昌齡
郭丹曦
人生最難是放過自己,最怕是心有不甘。如若王昌齡棄了本心、依了權貴,抑或失了希望、離了仕途,皆不會那般痛苦。開元十五年他一舉中第,開元二十二年再中博學鴻詞科。然科場得意,官位無升,他備受打擊。后來,他被貶至嶺南,胸中塊壘難消,只得學魏晉名士放浪形骸。開元二十八年,從長安赴江寧任所,他故意遲遲不去報到,在洛陽一住就是半年,每天借酒消愁。到江寧上任后也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忙著去太湖、浙江一帶游覽。這種消極怠工的反抗,過于意氣用事也實在容易授人以柄。《芙蓉樓送辛漸》正是作于這種情境。屢遭非議、四面楚歌;好友將離,孑然一身。連夜風雨,寒的并非天氣;天明送友,孤的豈止楚山?若是一般人,早已抱怨“巴山楚水凄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想著“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恨不能破罐破摔、醉生夢死了。王昌齡呢?“一片冰心在玉壺”。他是孤標傲世的山峰,也是心境澄明的玉器,更是“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的熱血男兒,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儒家君子。
心之美者謂之“情”,唐詩最動人之處即在有情。王昌齡這句“一片冰心在玉壺”恰能概括唐詩的真諦——純粹、溫潤。
唐人的友情,誠意拳拳,念念不忘。王昌齡到襄陽探望孟浩然,沒幾日孟浩然舊疾復發身亡,他因此悲傷不已。誰知在返程路上于巴陵邂逅李白,二人一見如故,相交莫逆。他們在江邊泛舟飲酒,對詩暢談,此后歧路別離,天各一方,然情誼不改,互有唱和。李白的《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甚是著名,而王昌齡的《巴陵送李十二》也別具特色:“搖曳巴陵洲渚分,清江傳語便風聞。山長不見秋城色,日暮蒹葭空水云。”王昌齡有不少送別、留別之作,我最愛其“流水通波接武岡,送君不覺有離傷。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兩鄉”。正所謂“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唐人之別雖有離傷,卻不必歧路沾巾,而是攜手共勉,再啟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