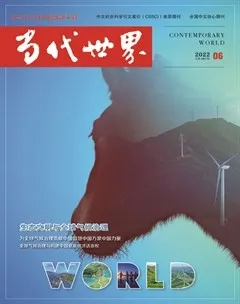后“脫歐”時代的英法矛盾及影響
張越塹
自2020年1月英國正式“脫歐”以來,英法兩國圍繞漁業、移民、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AUKUS)、《北愛爾蘭議定書》等議題矛盾齟齬不斷,在俄烏沖突背景下兩國對俄羅斯立場和外交行動也存在明顯差異。法國外交界甚至稱英法關系陷入“滑鐵盧戰役以來的至暗時刻”。在國際格局動蕩變革的大背景下,英法在內政外交各方面產生利益沖突、戰略分歧和影響力競爭,對歐洲一體化前景和跨大西洋關系帶來諸多復雜影響。
英法恩怨由來已久,早在1066年,來自法國諾曼底的威廉一世征服英格蘭并掌權,英法由此開啟長達八個世紀的復雜敵對關系。14—15世紀中葉,兩國圍繞王位和領土爭端爆發“百年戰爭”;17—19世紀上半葉,英法為爭奪殖民地又爆發了“第二次百年戰爭”,其間法國在爭奪北美的七年戰爭中落敗,卻協助美國贏下反抗英國的獨立戰爭。1815年,伴隨英國在滑鐵盧戰役中擊敗拿破侖,大英帝國全球霸主地位得以最終確立,英法交戰史就此終結。1904年,英法締結《友好協約》,兩國開始以盟友身份出現于世界舞臺,并在其后爆發的兩次世界大戰中并肩作戰。特別是在二戰中,英國支持戴高樂領導的“自由法國”運動解放法國,法國一度掀起“親英熱”。然而,對英國的戰略疑慮和對失敗的恐懼始終籠罩法國政壇,恢復國家尊嚴、追求大國榮光成為戰后法國政治家畢生奮斗的主旋律。

自歐洲一體化進程開啟以來,英法圍繞歐洲主導權再現微妙競合。20世紀60年代,為確保法國主導的歐洲免受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影響,戴高樂總統連續兩次否決了英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申請。直到戴高樂于1969年辭去總統職務后,英國才終于在1973年成功加入歐共體。隨后,英法關系步入快速發展的軌道。1994年,連接英法兩國的英吉利海峽隧道正式開通;2010年,英法簽署《蘭開斯特宮協議》,將合作拓展至安全與防務領域。然而,英法兩國在歐洲一體化走向問題上始終存在著分歧:法國力主建立更緊密的政治聯盟,努力推動歐盟實現貨幣、財政乃至防務一體化;而英國則深受“大西洋主義”影響,在除貿易以外的各個領域同其他歐盟國家保持疏離。
2016年的英國“脫歐”公投將英法關系重新置于緊張和矛盾之下。2017年,馬克龍憑借“挺歐”旗幟當選法國總統,將英國“脫歐”視為提升法國在歐盟內領導地位的機遇。在漫長的“脫歐”談判中,以馬克龍、歐盟首席談判代表巴尼耶等為代表的法國政治家對英國始終恪守強硬立場,堅持英國應全面退出歐盟單一市場、確保北愛爾蘭不設“硬邊界”等,致使兩國關系持續惡化。

2021年11月26日,法國漁民在圣馬洛港的入口處阻擋“諾曼底商人”號船,以示對英國“脫歐”后有關捕魚許可證問題的抗議。

2021年11月24日,穿越英吉利海峽的難民在英國鄧杰內斯獲救。
英國成功“脫歐”之后,英法兩國矛盾沖突此起彼伏,主要體現在以下3個方面:一是漁業糾紛。2021年4月,英屬澤西島政府拒絕履行《歐盟—英國貿易與合作協定》中的漁業條款,拒不向法國漁船發放捕魚許可證,法國漁船集結抗議,英法各派軍艦前往相關海域對峙。2021年10月,英國政府仍未足量發放許可證,法國隨即扣押英國漁船、切斷海峽群島的電力供應、封堵港口和海峽隧道、揚言對英實施制裁。二是潛艇合同風波。2021年9月,美英澳三國突然宣布組建AUKUS。英國配合美國與澳大利亞共享核動力潛艇技術,致使法國痛失與澳業已簽署的價值650億美元的柴油動力潛艇“世紀合同”。與美國總統拜登公開承認“處理不當”并展開系列補償的做法不同,英國首相約翰遜嘲諷馬克龍“反應過度”,戲謔“控制一下,讓我喘口氣吧”,點燃英法間輿論戰。三是移民爭端。2021年11月,一艘難民船在英吉利海峽傾覆,導致27人遇難。英法互相“甩鍋”,英國批評法國移民管控不人道,法國控訴英國“準現代奴隸制”的經濟模式是移民偷渡的根源。約翰遜在推特上公開致馬克龍的信函,單方面對法方提出五點要求,引發馬克龍強烈回應。此外,英法還在新冠疫苗生產上互相“卡脖子”,約翰遜、馬克龍二人在2021年6月舉行的七國集團(G7)峰會期間因北愛爾蘭貿易爭端激烈交鋒。一系列負面事件持續沖擊英法兩國民間信任,民調顯示,只有40%的法國民眾仍將英國視為盟友,遠低于對意大利、德國、西班牙等國70%以上的信任度。
俄烏危機升溫以來,英法兩國在對美情報解讀、對烏克蘭軍援以及對俄羅斯立場上也存在差異。英國堅持強硬反俄立場,在俄烏沖突爆發前率先向烏提供大量武器和援助,并在沖突爆發后大肆鼓動對俄實施最嚴厲制裁,奔走游說北約盟國向烏提供各類武器。而法國則堅持相對平衡的立場,馬克龍與普京通話十余次,在大國間穿梭斡旋、尋求和平解決危機,并批評北約向烏提供坦克“跨越紅線”,折射出英法兩國在歐洲重大地緣危機之下的戰略分歧。
英國“脫歐”以來,在歐洲內憂外患不斷的背景下,英法兩國領導人都面臨著抬升國內民意、彰顯自身全球影響力的挑戰,一系列結構性競爭導致兩國在內政外交諸多領域陷入“零和博弈”。
首先,兩國領導人為滿足國內政治需要,都急于證明自身歐盟立場的正確性。約翰遜和馬克龍分別為“脫歐”派和“挺歐”派代言人,雙方早已將自身執政基礎與后“脫歐”時代政績深度捆綁。英國希望證明“脫歐”成果斐然,法國則希望英國因“脫歐”蒙受重創。
從英方看,約翰遜承諾“脫歐”將使英國擺脫束縛、收回主權,開啟嶄新時代。然而,正式“脫歐”第一年,英國即遭遇供應鏈斷裂、勞動力短缺、通脹率高企、難民移民激增等一系列挑戰。民調顯示,只有18%的受訪民眾認為英國在“脫歐”后發展順利,大部分人認為“脫歐”結果糟糕。此外,保守黨在地方選舉中失利,民調支持率被工黨大幅反超,約翰遜因“聚會門”丑聞深陷危機,執政地位岌岌可危。在此背景下,約翰遜試圖將內部矛盾轉嫁至歐盟,將法國和歐盟作為諸多內政問題的“替罪羊”。
從法方看,歐盟議程是馬克龍內政外交政策的支柱。2022年是法國選舉年,4月和6月分別舉行總統和立法選舉,馬克龍尋求勝選連任并率領執政黨及盟友保住國民議會多數席位。面對選前民粹思潮再次抬頭、極右翼熱炒移民安全問題等挑戰,馬克龍需要全方位推高英國“脫歐”代價來彰顯歐盟的現實價值,以進一步提高“挺歐”立場吸引力、招攬搖擺選民。此外,法國漁業重鎮多位于北部經濟凋敝地區,馬克龍需要通過在具有象征意義的漁業問題上挺身而出來擺脫高高在上的“富人總統”標簽,打造捍衛主權、保護底層民眾利益的“接地氣”形象,對沖民粹主義勢力的煽動。

2020年12月30日,英國首相約翰遜簽署《歐盟—英國貿易與合作協定》。

2022年3月11日,法國總統馬克龍(中)、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右)和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在法國巴黎出席歐盟成員國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后的新聞發布會。
其次,英法兩國為在歐英關系重塑期占據主動,急于在對方關切領域謀求優勢。《歐盟—英國貿易與合作協定》作為“簡版‘脫歐’協議”,對于歐英外交與安全防務關系、監管與規則“對等”等問題并未作出妥善安排。英法在相關議題上互有訴求和倚重,現階段保持斗爭、堅持斗而不破是為在下一步歐英談判中積累籌碼、謀求主動。
在安全防務領域,英法兩國軍事實力旗鼓相當,共同對歐洲安全與防務承擔特殊責任。在大國競爭加劇、俄烏沖突延宕、美戰略重心東移的背景下,法國主張歐盟戰略自主,通過加強歐洲防務建設推動歐盟“掌握自身命運”。在這一進程中,調動英國參與防務合作將是法國放大自身力量的關鍵,并會對戰略文化保守的德國和安全防務依賴美國的中東歐國家形成倒逼。然而,英國長期堅持北約在歐洲安全中的首要地位,“脫歐”后更是“親美疏歐”,以強化北約作用稀釋歐盟戰略自主努力,以雙邊外交安全磋商、“烏克蘭—波蘭—英國三邊機制”等做法擠壓法國提出的“歐洲安全委員會”“諾曼底模式”等倡議空間,破壞法國主導的歐盟防務自主計劃。
在經濟領域,法國是歐盟內重要的標準輸出者,近年來先后推動歐盟出臺投資審查、數字監管、碳邊境調節機制等一系列新規,并力推歐盟將監管和市場力量轉化為大國博弈抓手,與美國在貿易與技術委員會(TTC)框架下就新興科技領域規則標準加強協調。此舉對英國構成“越頂交易”,置英國產業于規則壁壘和監管趨同壓力之下,對英國鋼鋁、金融、科技等優勢產業影響巨大。總的看,英法在歐英關系重塑期互有需求、步步為營,意圖通過相互施壓增加在相關談判中的籌碼。
最后,英法兩國都致力于在大國競爭時代施展全球抱負,在推進各自全球戰略布局時難免產生沖突碰撞。英法都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國際舞臺上的中等強國,具備較強核威懾能力、遠程作戰能力以及全球外交情報網絡。在大國博弈加劇的時代,英法均希望通過外交手段保持地位、施展影響。
英國在“脫歐”后依托英美特殊關系和英聯邦體系加強全球力量投放,致力于以“全球化英國”戰略彌補“脫歐”缺失,通過戰略力量“向印太傾斜”謀求恢復英國海上和商業強國地位。為此,英國作出幾十年來最大規模的海外軍事部署,派遣“伊麗莎白女王”號航母打擊群赴印太地區40多國巡航,與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越南、新加坡等國達成自貿協定,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并配合美國拉建“印太北約”的需求加入AUKUS。
法國則依靠歐盟維系并拓展其全球影響力,通過主導歐盟戰略自主建設放大自身優勢。作為唯一在印太地區擁有海外領土和永久軍事基地的歐盟國家,法國率先推出“印太戰略”并推動歐盟緊隨其后,與美日澳舉行海上聯合軍演,與日本召開外長防長“2+2”會談、謀求締結《互惠準入協定》,與印度建立元首戰略熱線、構建“真正的戰略伙伴關系”。法國自視為美國在該地區不可或缺的天然合作伙伴。然而,潛艇合同風波不僅令法國利益嚴重受損、顏面蒙辱,更使其印太戰略價值遭受質疑,對其成為亞太“利益相關方”和獨立大國的愿望構成重大威脅。總之,同為中等強國的英法在大國競爭日漸加劇的世界中心態失衡,兩國全球戰略布局沖突,彼此間嫌隙和不信任感進一步加深。
當前,歐洲一體化進程面臨新挑戰。俄烏沖突全方位沖擊歐洲安全環境,挑戰歐盟“繁榮換和平”的理念根基;多重危機加劇歐洲面臨的能源短缺、供應鏈阻斷、通脹高企等問題,沖淡歐洲經濟復蘇前景;波蘭、匈牙利與歐盟在憲法管轄權上的爭端難解,為歐盟內離心傾向埋下隱憂;大國博弈之下歐盟“選邊站隊”壓力陡增,凸顯歐洲戰略困境。在此背景下,英法作為具有共同地緣利益和戰略雄心的歐洲大國,開展外交和防務安全合作對于化解歐洲戰略困境、維護戰略利益至關重要。英法持續拉鋸可能削弱歐洲危機應對能力、牽制歐洲一體化進程,并加速歐洲權力結構的解構與重組。
首先,英法對立將掣肘歐洲防務與安全合作。英法是推動歐洲防務建設、難民移民體系改革的關鍵力量。自兩國矛盾激化以來,法國已相繼取消兩國防長、內政部長對話,歐盟與英國協同解決安全、防務、移民等問題渠道受阻。當前英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脫歐”成為保守黨內部意識形態絕對主流,即使進入“后約翰遜時代”,英國大概率仍將維持“疑歐”基調。英法出于各自利益盤算互不相讓,雙邊關系短期內難以改善,英歐關系也將繼續承壓,雙方達成安全與防務協議前景渺茫。

2022年1月20日,德國、美國、法國、英國外交官員在柏林舉行會談。
其次,英法矛盾激化將為歐盟內部團結增加變數。作為曾經最“叛逆”的成員國,英國曾多次聯合部分北歐和中東歐國家阻撓歐盟議程。如今,英國是最熟悉歐盟運作模式、內在矛盾和潛在風險點的外部力量。法國舒曼基金會主席朱利安尼評論稱,“脫歐”不會改變英國長期“一只腳在歐盟內、一只腳在歐盟外”的狀態。在英法關系惡化、英歐關系僵化背景下,英國將優先發展與歐盟成員國的雙邊關系,并可能繼續以英法、英歐矛盾為切入點,分化成員國,從“外部”平衡、牽制歐盟,繼續以歐盟“散、亂、弱”的結果凸顯英國“脫歐”的成果。
最后,英法關系惡化還將引起歐洲內部權力結構調整。一方面,英國對法國“挑釁”將進一步激發法國拓展歐盟新軸心的斗志。英國“脫歐”使歐盟權力回歸歐洲大陸,法德意形成新的歐盟權力三角。在“默克爾時代”落幕的背景下,法國領導地位相對提高。近段時間以來,法國乘歐盟輪值主席國的東風,加緊與德國新政府校準法德發動機,拉意大利簽署新友好協約、推動改革歐元區預算規則,加大歐盟大國對盟內小團體的制約和平衡。另一方面,英法交惡將提升德國在英法德小三角關系中的運籌能力和相對地位。當前,E3(Europe 3)機制為法德與英國協調立場、解決中東和薩赫勒問題提供了松散但不可或缺的平臺。英德關系曾長期是英法德三邊關系中最弱的一邊,兩國日前建立戰略對話、簽署外交與安全政策聯合宣言等動向頻密,顯示出歐洲三巨頭博弈組合產生新變化。
英法沖突不斷為2021年英國主辦的G7峰會和格拉斯哥氣候變化大會蒙上陰影,雙方敵對情緒進一步蔓延至北約、世貿組織等其他國際組織。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美國和歐洲中心主任賴特認為,英法反目或將使美國再次陷入類似于因日韓關系緊張而造成的“盟友內斗”等困局。面對俄烏沖突導致的歐洲周邊安全威脅迅速上升局面,美國需要英法強化防務合作、分擔對歐洲的安全責任,從而幫助美國實現低成本控局,向東騰挪更多資源。此外,拜登政府為推進印太布局向縱深發展,也需要英法統籌印太政策和行動,從而擴大盟友體系在印太地區的戰略協同作用。英歐防務合作停滯、英法反目將在一定程度上羈絆美國盟友體系協調和延伸,遲滯美國戰略布局和利益延展。
雖然俄烏沖突促使英法暫時專注于共同威脅,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兩國矛盾,但從英法對俄、烏外交行動的差異可以看出,兩國在戰略和戰術上的分歧不會輕易消除。英國和法國作為美盟友體系內盎格魯—撒克遜派和平衡派代表,將持續在外交政策上展開“明爭暗斗”,以證明自身價值、抬高相對分量。在此背景下,美國將基于自身戰略和利益動態調動這組關系。潛艇合同風波后,拜登為安撫法國和歐盟的受挫情緒,對歐盟戰略自主的表態發生重要轉變,支持歐盟強化防務建設作為對北約的補充,并宣布啟動美歐安全與防務對話。未來,美國為重新平衡美英歐關系,仍將繼續加大對英法、英歐的“居間調和”力度,可能在“E3+”框架下與英法德就伊朗核、烏克蘭等熱點問題加強磋商,邀請歐盟國家加入“四邊機制+”“AUKUS+”等框架,并在TTC、“印太經濟框架”等制度安排中給予歐盟切實利益。
在俄烏沖突助推美歐加強政策協調的背景下,美國的補償性措施可能進一步彌合跨大西洋關系裂痕、提振美歐同盟關系。然而從長期看,美國戰略重心東移動能不減、國內政治極化趨勢未變,歐盟在美國戰略全局中地位和價值下降是必然趨勢。在經歷特朗普沖擊波和拜登磨合期后,歐盟對美國保障盟友利益的意愿和能力心存疑慮、對美國未來政治走向深感不安,推動自身戰略自主的決心愈發堅定。若共和黨在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中重新執政,或使跨大西洋關系再度緊張,英國與法國、歐盟之間的分歧也將愈發明顯。
作者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八局工作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