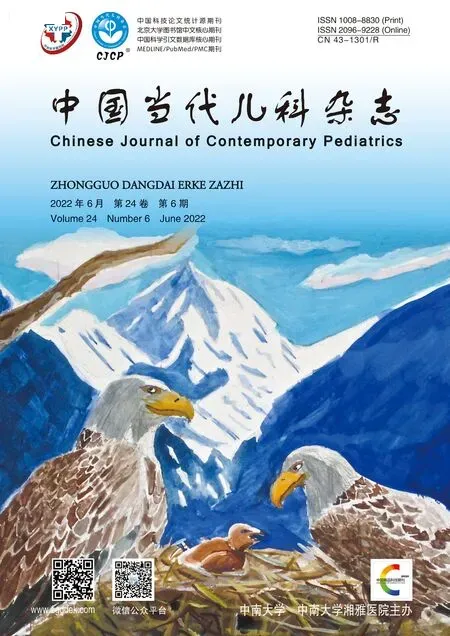兒童腦白質營養不良的臨床遺傳學研究進展
黃喆蘭 綜述 周文浩 審校
(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新生兒科,上海 201102)
1 腦白質營養不良的定義
1984年,腦白質營養不良(leukodystrophy,LD)被定義為由少突膠質細胞或髓鞘的原發損傷所導致的腦白質病變[1]。2015年,國際腦白質營養不良協會達成以下共識:腦白質病(leukoencephalopathy,LE)包含所有獲得性和遺傳性的腦白質異常疾病。LD為一組由遺傳性原發性神經膠質細胞和髓鞘損傷所導致的腦白質病變。遺傳性腦白質病(genetic leukoencephalopathy,gLE)為存在顯著腦白質異常的遺傳性疾病,但不伴有神經膠質細胞和髓鞘的原發損害(如全身系統性病變引起的髓鞘繼發損傷)[2]。2019年,van der Knaap等[3]認為所有遺傳因素所導致的LE都可被稱為LD,該定義更廣泛地囊括了2015年共識中的gLE。
由于腦白質相關疾病的表型和發病機制復雜,如何對其進行定義和分型一直難以統一,但隨著對疾病理解的加深,高通量測序技術在臨床中普遍應用,LD的定義將會更加符合疾病本質。本文將沿用2015年的定義共識,對近年來LD的臨床遺傳學研究進展展開綜述。
2 LD的流行病學
由于LD的臨床特征存在顯著異質性,因此其流行病學資料十分有限。國內尚無相關報道。國外基于住院患兒的流行病學調查顯示:遺傳因素所致的兒童LE的總體發病率約為1.2/10萬,其中約50%為LD[4]。基于人類基因突變數據庫(http://www.hgmd.cf.ac.uk)和基因組聚合數據庫(http://gnomad.broadinstitute.org)的預測結果估計,約每4 733個活產兒中即存在1個LD患兒,該預測值顯著高于先前的臨床診斷統計值[5]。雖然近年來有大量基于遺傳學檢查獲得診斷的LD病例報道[6-9],但目前尚未得到基于分子診斷模式的發病率數據。隨著遺傳學技術在新生兒篩查和診斷中的廣泛應用、基于大規模人群基因組學數據測算的LD相對頻率[10]、更多LD相關基因的挖掘[11],基于遺傳學檢查的陽性診斷率將得到進一步提升,LD的流行病學數據也將得到進一步完善[12]。
3 LD的遺傳學病因
遺傳變異如單基因變異、線粒體基因變異、染色體數目異常和微缺失/微重復綜合征等均可導致LD。多數LD為單基因病,根據在線人類孟德爾遺傳數據庫(https://omim.org)的檢索,截至2021年1月已有406種LE有了相對明確的致病基因(涉及410個基因),其中包含了119種LD,其中最多的為核基因變異相關的線粒體疾病(102個),最少的為編碼髓鞘特異性蛋白基因的異常(3個)。約80%的LD呈常染色體隱性遺傳。線粒體基因變異引起的LD有線粒體腦肌病伴高乳酸血癥和腦卒中樣發作、Leigh氏腦病、線粒體呼吸鏈功能異常相關腦病、Kearns-Sayre綜合征等。染色體異常如12p四體綜合征、環狀18號染色體、49,XXXXY綜合征和染色體18q缺失綜合征等也可導致LD。此外,微缺失/重復綜合征如6p25微缺失、3p21.31缺失、22q11.2重復等也被視作LD的發病原因[13]。
4 LD的基因型-表型關系
近年來,神經病理學、神經影像學、遺傳學等領域的發展使人們對LD的認識進一步加深,同時也產生了多種分類方式。如根據LD的細胞病理學特征,可分為髓鞘形成低下、髓鞘形成障礙、脫髓鞘等[14];根據主要累及的腦組織成分可分為原發性髓鞘病、星形膠質細胞病、小膠質細胞病、白質-軸突病、白質-血管病等[15];根據神經影像學特征可分為髓鞘形成減少、脫髓鞘、髓鞘空泡化、異常髓鞘物質堆積、白質血管病變等[16-17]。值得注意的是,由于LD的發病機制復雜,上述分類方式不完全獨立,可能同時屬于多個種類。本節將基于細胞病理學特征的分類方式,對各類型LD中常見的基因型-表型關系進行介紹。
4.1 髓鞘形成低下性LD
髓鞘形成低下是指少突膠質細胞的原發缺陷導致髓鞘無法生成或維持,如佩梅病(Pelizaeus-Merzbacher disease,PMD)、佩梅樣病、POLR基因相關LD等。以X連鎖隱性遺傳的PMD為例,PLP1基因變異可導致髓鞘的主要成分PLP1蛋白或其剪接變異體DM20的異常折疊,進而導致少突膠質細胞無法形成或死亡。通過檢測PLP1基因拷貝數或直接進行測序可明確遺傳學診斷。PMD為遺傳異質性疾病,具有嚴格的基因型-表型相關性,不同PLP1基因變異類型可導致臨床表型嚴重程度不同。如重復變異可致經典型PMD,錯義變異可表現為更嚴重的先天型PMD,而無效變異如缺失變異等則可導致病情較輕的無PLP1綜合征和痙攣性截癱Ⅱ型[18]。經典型PMD男性患兒多在生后第1年內發病,表現為運動發育遲緩、肌張力障礙、眼球震顫、共濟失調、痙攣等,并伴有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礙;先天型PMD患兒生后早期起病,臨床可表現為眼球震顫、肌張力障礙、吞咽困難、癲癇等,運動智力發育嚴重受損,多于兒童期死亡;而無PLP1綜合征和痙攣性截癱Ⅱ型患者神經系統表現相對溫和,通常于青少年期起病,可保留行走能力并伴有輕微的認知功能障礙[19]。
4.2 髓鞘形成障礙性LD
髓鞘形成障礙是指形成的髓鞘定位異常或功能異常,如亞歷山大病(Alexander disease,AxD)、伴皮質下囊腫的巨腦性白質腦病、Aicardi-Goutières綜合征等。以常染色體顯性遺傳的AxD為例,GFAP基因的功能獲得性變異可導致星型膠質細胞無法正確調節髓鞘形成,形成異常膠質纖維酸性蛋白,激活星型膠質細胞內的多重應激途徑而致病;此外,星型膠質細胞的缺陷也可導致細胞內外離子不平衡,進而造成髓鞘內液體積聚(空泡化)而致病[20]。疾病嚴重程度與GFAP基因的過表達水平和受影響的氨基酸種類均密切相關[21]。AxD的發病年齡從產前到成年期不等,可根據臨床表現將AxD分為2類,Ⅰ型AxD為早發型,患兒多在嬰兒期出現整體發育遲緩、進行性的大頭畸形和癲癇發作,并隨著疾病的進展出現運動功能和認知能力的退化,多于10年內死亡;Ⅱ型則可發病于所有年齡段,臨床上主要表現為共濟失調、構音障礙、自主神經功能紊亂、眼球運動障礙、肌陣攣等。而Ⅱ型AxD患者發病較為隱匿,晚期可出現共濟失調、肌陣攣、吞咽困難和構音障礙等,伴有不同程度的認知能力下降[21]。
4.3 脫髓鞘性LD
脫髓鞘是指已形成的髓鞘丟失或被破壞,多為累及腦白質的遺傳代謝性疾病(嚴格定義上屬于gLE),如球形細胞腦白質營養不良/克拉伯病、腎上腺腦白質營養不良(adrenoleukodystrophy,ALD)、異染性腦白質營養不良(metachromatic leukodystrophy,MLD)等。以常染色體隱性遺傳的MLD為例,ARSA基因變異可導致芳基硫酸酶A活性降低或缺乏,進而導致硫酸鹽在中樞和周圍神經系統中沉積,前者可通過影響細胞鈣穩態、細胞應激、細胞凋亡等使髓鞘結構不穩定而致病。ARSA基因的變異類型與殘留的芳基硫酸酶A活性密切相關,也因此產生了不同的疾病類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其他生化或表觀遺傳因素的影響,即使具有相同致病變異的患者,其發病時間和臨床表型也有差異[22]。據推測,酶活性越低,發病年齡越早,MLD可根據首發癥狀的發生年齡分為晚期嬰兒型、青少年型、成人型。晚期嬰兒型MLD為最常見和最嚴重的類型,在中樞神經系統癥狀出現前通常先出現快速進展的周圍神經病變,臨床表現為運動功能受損、痙攣性四肢癱、癲癇發作、共濟失調、視神經萎縮和認知障礙等,患兒通常于兒童期死亡;青少年型MLD起病于3~16歲間,起病相對隱匿,認知障礙和行為改變為主要起病癥狀,進而發展為中樞和外周神經系統的異常;而成人型MLD起病于16歲后,其典型特征為精神病性癥狀(如幻覺),由于進展緩慢,常被誤診為早發性癡呆或精神分裂癥[23]。
5 LD的臨床遺傳學診療流程
隨著遺傳學檢查技術在臨床的普及和廣泛應用,結合神經影像學檢查和遺傳學檢查二者的深度表型信息將成為LD的主流診斷模式[12]。該模式顯著提升了LD的診斷率,對評估預后和指導精準化治療等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但全面的病史采集、神經影像學檢查等在LD遺傳學檢查的前期評估中也不容忽視。LD的臨床遺傳學診療流程如圖1所示。

圖1 LD的臨床遺傳學診療流程圖
5.1 病史采集
家族史等臨床信息可以使LD的遺傳學檢查分析更有針對性。了解疾病發生的誘因可排除獲得性LE,避免不必要的檢查;明確的家族史可有助于推測LD的遺傳模式。多數LE患者于兒童期起病,極少數起病于成人期[24]。如PMD多起病于1歲以內;巨軸索神經病多起病于5歲以內;ALD多起病于幼兒期內,新生兒ALD起病于1個月以內;MLD多起病于青春期內;成人葡聚糖體病可至成年期才發病[15]。LD的臨床表現主要可分為神經系統癥狀和非神經系統癥狀。運動障礙是LD最常見的神經系統癥狀之一,病變累及錐體束時,患者可出現驚厥、行走能力受限或肌張力障礙等;病變累及周圍神經時,初期可表現為肌張力低下,而至晚期則可出現痙攣發作;病變累及基底節時,可表現為異常不自主運動。隨著疾病進展,以運動障礙為主要癥狀起病的LD還可出現其他神經系統癥狀,如自主神經功能異常、認知損害、共濟失調、眼球震顫等。除了神經系統癥狀,非神經系統癥狀的綜合評估也有助于診斷[13]。如伴皮質下囊腫的巨腦性白質腦病的特異性表現為巨顱畸形,而Aicardi-Goutières綜合征的特異性表現為小頭畸形[25]。隨著新生兒高通量測序技術的臨床推廣應用,針對患兒不同發育過程中多維度的自然病史采集有助于LD的早期發現與精準管理。
5.2 神經影像學檢查
頭顱MRI是既往診斷LD的主要影像學檢查手段。各類型LD的MRI特征有共性也有差異[26],如表1所示。然而生后早期髓鞘發育變化迅速,很難對圖像進行準確判讀,因此Desai等[27]認為6月齡前的患兒主要應參考T1加權像,而T2加權像對大于6月齡的患兒更有參考價值。不同MRI序列對大腦結構成分的敏感度不同,目前主流觀點認為T1加權像、T2加權像和液體衰減反轉恢復序列是疑似LD患者的必選。MRI以低成本的優勢為后續的遺傳學分析提供了更有針對性的信息,并通過多模態的神經影像學評估為臨床提供了預警標志物[28]。

表1 不同類型LD的病理變化及MRI特征表現
5.3 遺傳學檢查
目前家系全外顯子組測序(whole exome sequence,WES)是疑似LD的首選。其檢測范圍主要為外顯子組區域及其剪切位點周圍5~20 bp范圍內的單堿基變異和50 bp以內的插入/缺失變異,雖然上述區域只占基因的1%左右,卻包含了85%的致病變異[29]。有文獻報道,目前基于WES的LD診斷率可高達73%[12]。將WES應用于LD的診斷不但有助于增強診斷特異性,而且還有助于擴大LD病種和加深對疾病的理解。WES已幫助發現了約72種新的LD基因型-表型聯系,但由于技術所限,WES無法準確檢測重復序列、拷貝數變異、內含子變異等[13]。與WES相比,靶向目標基因包測序(targeted panel sequencing,Panel)和全基因組測序(whole genome sequencing,WGS)在LD的使用和研究較為有限[30-31]。雖然Panel價格低廉,但由于LD的臨床表現異質性過高,很難錨定準確的基因包,因此基因組的低覆蓋率導致了其相對較低的診斷率,LD的隊列研究顯示Panel的診斷率僅為13.3%[30]。WGS的廣覆蓋度顯著提升了LD的診斷率,但是其高成本和分析難度的增加使其難以被大規模應用到診斷實踐中。
5.4 精準化治療
明確的臨床遺傳學診斷有助于指導患兒個體化的精準靶向治療。干細胞移植在治療LD上有很大潛力,尤其造血干細胞移植可在早期延長患者的生存期[32-33],目前研究證實造血干細胞移植僅對部分LD,如ALD、MLD、克拉伯病等有效[34-36]。中樞神經干細胞移植的細胞替代療法也可通過刺激內源性神經發生以促進髓鞘重塑,而遺傳學診斷可指導移植的神經細胞類型,如PMD患兒應移植少突膠質細胞、AxD患兒應移植星形膠質細胞等[37]。此外,基因治療基因治療也有望在未來投入到LD患兒的治療中。然而上述療法尚未在臨床中被廣泛應用,支持對癥治療仍是目前大多數LD患兒的主要選擇,但遺傳學診斷可以指導不同類型LD的特異性對癥治療。如ALD患兒在發病前服用不飽和脂肪酸如洛佐倫油或極長鏈脂肪酸可緩解病情進展[38];MLD患兒可在早期行膽囊切除術預防膽囊息肉或膽囊癌等[39];Aicardi-Goutières綜合征患兒全身性應用皮質醇可緩解自身免疫異常相關癥狀[40]。
6 總結與展望
LD是一組以原發性神經膠質細胞和髓鞘異常為特征的遺傳異質性疾病,多數具有嚴格的基因型-表型相關性。新生兒篩查可通過早期積極的臨床管理,有效降低疾病嚴重預后的發生率,高通量測序的應用顯著改善了傳統篩查的診斷效能。目前在我國LD尚未被納入新生兒篩查,然而部分LD是可防可控的,2021年中國新生兒篩查專家共識首次將ALD納入了新生兒基因篩查推薦疾病清單[41]。隨著對疾病的進一步認識和特異性療法的出現,更多LD病種將被納入潛在篩查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