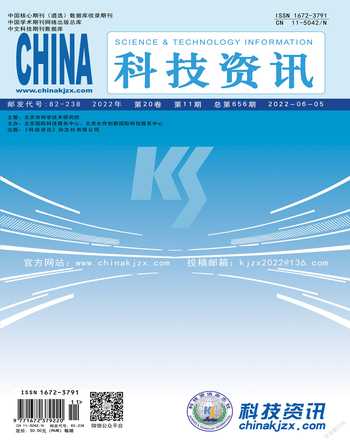探微城市空間對于公眾共通的意義空間的影響
殷曉宇

摘要:近年來,我國城市化進程不斷推進,城市化也在朝著更高水平不斷發展。這一過程,已逐漸從粗放型的改農業用地轉為城市建筑用地,轉變為合理地規劃城市建設。隨城市的不斷發展,城市的功能區也不斷細分,各不同功能用地子集之間協助互補,共有交集,與城市進一步發展齊頭并進。城市工業區由于其地理位置劃分的邊緣化和城市功能的欠發展,使得在此居住的居民與城市其他地區居民的精神活動和精神交流受到一定影響。該文以從大連市普蘭店區太平工業區的控制性詳細規劃為例,以期管窺各中一二。
關鍵詞:傳播學城市空間城市規劃共通的意義空間
中圖分類號:TU982.29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672-3791(2022)06(a)-0000-00
1重要的概念梳理
關于城市規劃,學界并沒有一個明晰的概念,這里簡單概括為:城市化規劃就是為了使城市發展達到既定的發展目標,而進行的城市設計和布局。由于城市的定位和發展目標不同,因此城市的規劃也不盡相同。在進行城市規劃的時候,設計者要充分考慮到地理、生態、社會等因素,以合理的規劃,更好地發揮城市功能。
城市空間是一個跨學科概念,筆者總結為,城市空間是一個自然和社會的實體,是進行城市各種活動的“容器”。既是一個空間物理上的概念,也是一個居民進行精神活動的場域。根據地理邊界劃分出結界,居民在此場域內進行精神活動和精神交往。但在消費社會中,現代具有強烈的實用主義目的下的城市規劃,削弱了城市在物質空間上的居民之間的精神交往的功能。古希臘時期廣場的主要作用之一——作為居民演講和辯論的場所,在現代的城市規劃看來似乎是無法想象的。要么廣場作為公共用地讓步于高回報的商業用地,要么在廣場周維興建大型商超——一切為消費社會服務,這是當代城市規劃的缺憾。一個城市的空間生產,既是構筑市民創新生產、生活方式的場所,又是型塑市民享受權利和實現希望的新型社會關系,具有典型的社會資本屬性、文化符號價值及其社會關系特征[1]。不得不承認,城市工業區的存在是一個尷尬的角色,另外工業區的誕生就是為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所容納的居民在職業和生活方式上就有異于其他一般社區居民。同時,欠發展的生活基礎設施又限制了多元的城市生活的發展。
符號互動理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認為,事物的意義由人在社會互動過程中賦予;人在此互動過程中,會根據自身的元語言環境理解[2] 。工業區內居民相似的或者接近的生活經驗和文化背景,是居民社會互動的基礎。他們多為在工業區工作的個人或家屬,工業區的配套設施較于正常社群存在一定差異。工業區內相對嚴格又長時間的的工作時限,使得這一部分居民彼此之間或向外交流較少。同時,居民的精神活動的一個重要物質載體就是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其成熟與完善與否,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居民的精神交流。因此,通過解讀城市規劃,可以大致了解居民精神交往的水平,使用與需求的滿足情況,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2大連新生行政區的工業區的控制性詳細規劃解讀
2014年6月23日,國務院設立大連金普新區,作為中國第10個國家級新區,也是東北三省地區唯一一個國家級新區,太平工業區有著政策上的先決優勢條件,是大連最年輕,最具有發展潛力的行政區,也是大連的產業轉移的重要承載區,交通便利,區位優勢突出。
依據《太平街道發展戰略規劃》,太平街道的功能定位為普蘭店區拱圍灣底的關聯產業先導區;普蘭店城區重要的產業。規劃的三大目標即發展特色鮮明、功能完備的綜合型的現代園區;內行通暢、外聯順達的復合型的高效交通;建設宜居宜業的生態城區組團[3]。由園區規劃的定位可知,園區在規劃最初,就是完全倚靠其經濟職能而發展,對于社會文化等方面訴求有所欠缺。很容易讓人有一種冰冷感,似乎工業區的規劃都是圍繞轟隆作響的機器而生,一排排藍頂白墻的活動板房,缺少一種人情味充盈的溫暖感。事實上根據下文所展示的詳細規劃圖來看,也確實如此。空間是社會性的,空間里彌漫著社會關系,它不僅被社會關系支持,也生產社會關系和被社會關系所生產 [4]。太平工業區的規劃,忽略了市民文化發展需要的生存空間。重經濟,輕人文,這種規劃從減少了居民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和實踐所能構成一個文化共同體的可能性和居民從中受益的可能性。居民間的社會交往和活動,可能始終維系在一個基礎的水平,而非深入的長久的有意義的生活體驗,這也是追逐經濟效應帶來的巨大犧牲。
據表1所示,規劃太平街道內的公共管理與公共服務設施用地主要包括行政辦公用地、教育科研用地、文化設施用地、社會福利用地等,總面積為29.74hm2,占城市建設用地面積的1.24%。這些用地主要呈一條帶狀集中分布在工業區北部和中部,圍繞交通較為便利的地點延伸開來。國家對于工業用地規劃中公共管理與公共設施用地雖然沒有明確規定,但是相較于居民區公共管理與公共服務用地占比的15%~20%,太平工業區1.24%的比例著實太小。這意味著工業區內居民的基礎娛樂性活動僅能維持在一個較低水平。
建筑等景觀都是媒介傳播符號,在信息的傳播和流動之間,訴說著城市的性格和氣質,記錄和昭示著社會的發展。比如:規劃當中的廣場的大小其實也透露出城市居民公共活動的參與度高低——大型的廣場更利于大型活動的舉辦,更容易聚集更多的居民的參與,不僅有利于居民的城市交往,更是對于城市共通意義空間的強化。《規劃》下的工業區布局,儼然使得公共空間遭到一定的破壞,使得居民共通的意義交流空間陷入困頓之中,從內部間離了居民之間信息傳遞,城市空間作為重要的居民傳播與交流的途徑和媒介,不但沒有維持最基本的作用,反而產生了些負面效應,甚至產生交流上的壁壘——傳播隔閡。目前,國內工業區空間的演替價值普遍存在的問題是輕文化,重經濟,這是由資本的逐利性導致的。因此維護傳統文化“記憶場”,適當拓展當代文化需求,就顯得尤為重要[5]。每一個城市同人一樣,也有屬于自己的記憶。生活在這里的居民更是如此,童年路口拐角夏日里的冰棍,公園里冬日湖邊的溜冰,兒童公園的旋轉木馬……沒有了過去的記憶,就失去了現存的價值。工業區由過去荒涼的空地轉變為廠房林立,熱鬧喧囂的生活區域,浮華喧囂的外衣下掩蓋不住的是空虛的內涵。它過去的歷史是空白,這種遺憾無法補救,那么現在規劃時就要格外注重文化和共同記憶的培養,否則這里的居民只是生活在工業時代下冰冷的建筑硬殼子里。短期來看這種規劃或許從經濟角度考慮是不得已而為之,但長久來看是對工業區內外公眾精神文化的損失。
3思考與對策
工業區的規劃,由于其自身性質,難以磨滅本身經濟屬性帶來的強大烙印,但是人的發展始終是一切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所以不可舍本求末。
文化對于公眾的影響是潛移默化但是又深刻雋永的。空間本身就是信息的載體,就如“無聲的語言”一般,藉由它的結構、特點傳遞出空間自身的文本含義;再者,空間對人的組合與行動能發揮著塑造和控制的作用,對人們各種傳播活動的開展,各種關系的建構會產生直接影響[6]。社會空間是具有文化隱喻性的。現代人的身份、階級、性別、權力等因素實際上從某個層面上來說也是由空間所體現的,比如:關押在監獄里的囚犯自然和生活在生活環境優渥的中產階級不同。作為工業區而言,地價較為低廉,基礎設施不夠完善,這都有別于市中心商圈的地價和生活的便捷性,考慮到這一敏感因素,要盡力減少這一因素給這一群體帶來的心理落差。并要力圖從其他方面打造一個屬于該工業區的居住優勢,讓工業區內外的人都產生心理認同,增強居民的精神文化自信,減少由于經濟或社會地位等因素造成的居民和外部世界的心理認同上的差異。因此,物理上的空間(如公共基礎設施)和文化空間(居民的精神交往)是需并駕齊驅共同建設的。張鴻雁認為,城市必須創造城市人共通的生活愿景,創造屬于城市自己的精神和文化,這是現代城市自身的一個責任[7]。因此在處理好經濟效益的同時,也要兼顧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多打造能夠增進居民文化活動的場域和多種多樣的活動,培養居民對于所處環境的文化認同感和歸屬感。比如:不定期舉辦納涼晚會、聯歡會、組織社區工作人員多走訪了解居民,加強居民之間的互動交流,維系和培養好情感的溝通,讓居民自發對所處空間和生活環境產生認同和維護。對外,相關部門應當做好工業區的對外宣傳工作,做好營銷推廣工作,在工業區硬件創造經濟利益的同時,也可以利用好軟實力增強影響力,為工業區下一步轉型和升級做好準備。
另外,不斷完善信息處理和傳播系統,保證信息在信源和信宿之間流動通暢準確,避免傳播中“噪音”對于信息的干擾。也要考慮由于受眾的背景和文化教育水平等因素的不同,個體對于信息接收和處理的差異性。因此,在傳播過程中要形式靈活多樣,解讀因“策”施教,以期達到傳播效果的最大化。
居民自身也要主動融入大環境之中。居民多為身在工業區的從業人員或家屬,彼此身份上的趨同性有很多共同話題,因此要多加強溝通,溫馨和睦的鄰里關系不僅有利于生活和工作,更有利于加強凝聚力和身份認同。當工業區居民面向工業區外部的群體時,也更加有底氣和自信。
總而言之,工業區的規劃,會深切影響到居民的共通的意義空間的交往,不論是在淺層的語言風俗習慣方面,還是精神交往和文化交往方面。但是既然是被專門劃分稱作為“工業區”,這樣的結果就是在預期當中存在的,我們亟待解決的就是怎樣使負面影響降到最低,甚至可以結合該地區的區位優勢,因地制宜,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多層面聯合發展的特色工業區,在不斷發展中,慢慢揭下“工業區”的標簽,成為宜業宜居的優秀居住小區。
參考文獻
[1] 陳進華.中國城市風險化:空間與治理[J].中國社會科學,2017(8):43-60.
[2] 肖珺,張馳.短視頻跨文化傳播的符號敘事研究[J].新聞與寫作,2020(3):24-31.
[3] 李乘.小城鎮建成環境可持續更新策略研究[D].杭州:浙江大學,2019.
[4] 張誠.城市化進程中鄉村公共空間的流變與重構[J].城市發展研究,2021,28(10):58-64.
[5] 顧大治,徐益娟,洪百舸.新媒體融合下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傳承與重構[J].現代城市研究,2021(12):40-47,55.
[6] 杜未未.空間的文學建構與文化闡釋[D].長春:吉林大學,2020.
[7] 孫仁禮.人工智能影響下未來城市理想空間模式研究[D].濟南:山東建筑大學,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