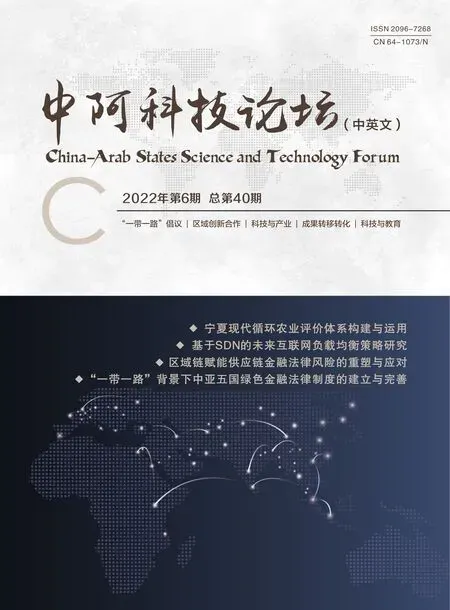工會幫扶下城市困難職工生計恢復力評價
——以新疆X州為例
寧 靜 王華麗 陳 琳
(新疆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新疆 烏魯木齊 830052)
目前我國正處于城鎮化發展的重要時期,鄉村振興戰略正如火如荼地進行,城市面臨著向智慧城市轉型的巨大挑戰,城鄉融合發展也在有條不紊地進行,因此對于城市來說,建立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是尤為重要的,其中對于困難職工的救助幫扶十分重要。中華全國總工會在第十六屆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上,把困難職工解困脫困工作列為重點,全面提高困難職工幫扶工作的規范性和有效性[1]。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速,社會生產結構調整,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經濟沖擊等,失業職工數量持續增長。城市困難職工缺乏固定資產和基本生活物資,若遭遇意外危機,其生計恢復力更差,貧困程度更深,長此以往,這樣的現象會對城市秩序和穩定發展造成負面影響。本文對新疆X州城市困難職工生計恢復力進行測度,以期為提升城市困難職工生計恢復力,加快城市化進程和產業結構轉型提供參考和借鑒。
1 生計恢復力概念及工會幫扶研究現狀
生計恢復力最早被用于生態學領域,是指生態在受到沖擊后,能夠維持原有狀態的一種能力[2]。隨著學者們對其概念和內涵的深入研究,恢復力概念被引入社會學領域,用于研究各類組織,以研究差異化主體在遭受干擾和沖擊后的恢復力為主。關于生計與貧困的碰撞,Sen(1981)認為貧困人口缺少自身發展能力以及逃脫貧困陷阱的能力[3];為了對貧困人口進行生計測度,Speranza等(2014)建立了以緩沖能力維度、自組織能力維度和學習能力維度為基礎的指標分析框架[4]。隨著恢復力內涵的不斷延伸,生計恢復力現還被用于生活環境惡劣的居民、搬遷的居民或失地的農戶的生計研究。江易華等(2020)對失地農戶生計恢復力的效應和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5];紀金雄等(2021)將生計恢復力測度運用到茶農的生產發展研究中[6];吳孔森等(2021)從三個維度評價了黃土高原農戶生計恢復力,并提出生計建設路徑[7]。
2 城市困難職工生計恢復力指標體系構建
2.1 研究對象和指標選取
本文選取新疆X州11個縣市基層工會所幫扶的困難職工作為研究對象,從緩沖能力、自組織能力、學習能力三個維度出發,選取適用于困難職工的指標,建立城市困難職工生計恢復力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

表1 城市困難職工生計恢復力指標體系
緩沖能力,指城市困難職工根據自身擁有的各類資本采取不同的應對方式以抵御突發事件沖擊的能力。由于城市困難職工缺少自然資本,而社會資本更能反映困難職工對外部社會網絡的依賴性,歸入自組織能力。因此本文選取人力資本(勞動力人數X1、健康狀況X2)、物質資本(住房類型X3),金融資本(月人均收入X4)來衡量城市困難職工的緩沖能力。自組織能力,指城市困難職工依賴社會資源,通過社會互動塑造社會恢復力,促使外部環境穩定的能力。根據Speranza等(2014)的生計恢復力框架并結合調查區域實際情況,本文選取社會關系(是否為工會成員X5)、參與社會事務(是否參加工會活動X6)、對社會網絡的信賴程度(與幫扶人聯系緊密程度X7、家中遭遇變故時向工會求助的可能性X8)以表征自組織能力。學習能力,指城市困難職工利用所擁有的知識和技能而且把其轉化為謀取生計的能力。因此,本文選取困難職工自身所擁有的學習能力(受教育程度X9、是否接受過技能培訓X10)和轉化后的生計能力(是否通過培訓獲得工作X11)以表征學習能力。
3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熵權TOPSIS城市困難職工生計恢復力測算模型構建
3.1 主成分分析確定權重
利用SPSS軟件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后確定指標權重,分別為緩沖能力(0.326)、自組織能力(0.416)、學習能力(0.258),城市困難職工生計恢復力計算公式為F=0.416F1(自組織能力)+0.326F2(緩沖能力)+0.258F3(學習能力)。
3.2 TOPSIS進行評價結果分析
計算生計恢復力及三種能力與正負理想解的歐氏距離D+、D-和相對貼近度ζ:

對新疆X州城市困難職工生計恢復力框架下三種能力的相對貼近度進行計算并排序如表2,結果分析如下。

表2 新疆X州11個縣市城市困難職工生計恢復力
(1)自組織能力
自組織能力方面,排名靠前的是D縣和C縣。
資源方面,D縣位于中國與哈薩克斯坦邊境,擁有中哈國際邊境合作中心,是中哈經濟往來的要塞,D縣將地理位置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實行稅收優惠政策,吸引了較發達城市各行業的大中小型企業在此落戶。因此D縣生產力水平和經濟水平較高,基層工會在企業中起到較好的組織作用,當職工遇到突發事件時,工會能夠及時行使救助職能。工會幫扶方面,D縣和C縣的基層工會幫扶人員都與困難職工家庭聯系緊密,熟知困難職工家庭的實際情況,工會與困難職工之間形成了信任橋梁,建立了精確的困難職工檔案,縣總工會和基層工會每個季度進行入戶走訪摸排,建立了困難職工信息庫。
(2)緩沖能力
緩沖能力方面,排名前三的是I縣、D縣、A縣。
社會資源方面,I縣、D縣、A縣有一定的經濟基礎,且三地各有特色,周邊各類資源豐富,對口援疆政策輸送了很多優質企業和人才,企業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就業崗位,城市人均收入水平高,因此困難職工在獲得工作的前提下能夠積累較多的金融資本;工會均與住建部門積極聯動,為困難職工提供廉租房,使職工在遭遇突發事件時有較強的抵御能力。在健康方面,I縣、D縣由于經濟基礎和自然生存環境較好,困難職工群體醫療保健支出較高,總體健康狀況略優于其他縣市,因病致困人數少于其他縣市。

(3)學習能力
學習能力方面,排名靠前的是E縣、D縣。
在技能培訓方面,E縣和D縣依托當地企業、工廠、園區給予困難職工技能培訓、就業崗位和創業機會,幫助困難職工發展新生計方式,一方面保證了困難職工正常的收入來源,另一方面幫助困難職工重建自信,實現社會價值。同時E縣、D縣的產業園區發展也為解決周邊村鎮農民工的就業問題做出了貢獻,因此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給予企業優惠政策以激勵企業吸納更多困難職工就業,長期穩定地實現了解困脫困。
4 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本文通過對工會幫扶下新疆X州城市困難職工生計恢復力進行模型計算,得出其排名結果:D、C、B、E、F、J、K、G、H、I、A。此結果與新疆X州城市困難職工返困率排名大致相同,因此用該方法評價是合理的。新疆X州城市困難職工生計恢復力呈現橄欖型分布,D縣最高,大部分縣市為0.5~0.6,A縣、I縣、H縣分列最后三位。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有以下三類。
第一,區域優勢導致的經濟發展不均衡。C縣、B縣、A縣和K縣都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旅游資源,其中包含幾處聞名全國的大型風景區。C縣充分利用了景區資源,多年來將景區的宣傳和建設置于重要地位,使得C縣的經濟水平不斷提高,成為脫穎而出的旅游大縣;其他縣由于縣域經濟水平差異較大,且多數縣域內基礎設施匱乏,導致景區崗位數量有限,不能有效帶動當地就業。
第二,困難職工與社會網絡聯系的緊密性差異。D縣和C縣工會在困難職工幫扶方面把基礎工作作為重點,做到掌握困難職工家庭經濟狀況,每季度進行入戶摸排,長期以來,縣總工會已經為困難職工建立了完善的信息庫;相比之下,B縣和A縣在困難職工的精準識別和精準幫扶上還有所欠缺,在檔案管理工作上也有所欠缺,存在困難職工家庭信息不完整和滯后情況。
第三,工會對困難職工就業創業幫扶的力度不同。E縣、D縣和H縣在“造血式”幫扶中多采用鼓勵困難職工實現創業和再就業,這些縣市工會多與支援新疆的大企業合作,長期舉辦技能培訓班,教學內容以服務業和手工業為主,當困難職工掌握新技能,工會就可以為他們推薦工作,形成良性循環,提高了困難職工的學習能力。
4.2 建議
針對以上問題,從工會職能角度提出建議:
(1)行使救助職能,幫助困難職工提升緩沖能力。
工會要做到應幫盡幫,首先需要將階段性貧困的困難職工家庭資金保障落實到位,階段性貧困致困原因包括遭遇下崗失業、重大疾病、子女教育、意外災難等。需要落實中央、地方幫扶資金,確保困難職工享受到應享受的政策,幫助困難職工積累各類資本以應對階段性貧困。利用好大數據技術將幫扶對象按照困難職工、困難學生、困難患者和困難企業的類別建立困難職工信息庫,為精準幫扶搭建平臺,讓正式資源和非正式資源能夠“一站式”服務于困難職工家庭。
(2)行使維權職能,增強困難職工的自組織能力。
通過常態化入戶,精確掌握每個困難職工家庭情況,加強困難職工檔案管理,確保信息更新;建立法律咨詢點,為遇到保險、工資等勞動糾紛問題的困難職工提供政策咨詢、法律援助等維權服務,建立工會與困難職工之間的信任網絡,使困難職工選擇通過工會等各類社會資源獲取信息、資本以抵御各類危機。
(3)行使服務職能,提高困難職工的學習能力。
與政府其他部門建立聯合機制,實現協同治理,消除信息孤島,達到信息共享,掌握困難職工在社會網絡中的真實情況,為困難職工精準識別提供有效保障;加大教育幫扶投入,與企業合作開展聯合助學,為合作的企業頒發公益獎牌,鼓勵企業為社會多做貢獻,通過獎助學金、困難補助等政策幫助困難職工家庭子女完成學業,進一步通過子女的就業實現家庭的穩定長效脫困;注重“造血式”幫扶,對于體質健康的家庭富余勞動力,依托園區、企業、工廠為其提供就業崗位、就業技能培訓、創業支持等多元化服務;建立返困機制,做好脫困后跟蹤服務,脫困不脫政策,確保困難職工實現長期穩定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