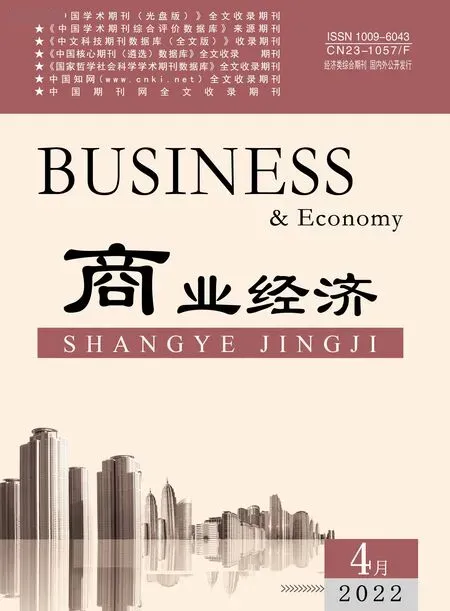經濟高質量發展背景下鄭州市科技創新路徑研究
——基于成都、武漢、西安等城市的比較分析
周 倩
(鄭州財經學院 商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2)
一、引言
國內外學者關于高質量發展的研究從理念到評價體系等多元展開(Ghosh,2017;Niebel,2018;張博雅,2019;張合林等,2019;李夢欣和任保平,2019)。其中李夢欣(2019)構建了評價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的五大指標體系:創新、協調、綠色、開放與共享。對于科技創新的研究,辜勝阻等(2018)認為,我國核心技術的突破能夠維護國家安全,搶占全球科技發展先機,進而實現高質量發展;陳麗嫻(2016)基于技術進步作為評價地區創新能力關鍵指標的基礎上,研究得出創新對我國高質量發展水平有顯著正向影響;王守文等(2021)利用加權熵權法,從科學資源存量、科學資源投入、科學成果產出3個維度衡量長江經濟帶的科學競爭力。
由以上文獻可知,現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國家或者地區層面科技創新能力水平研究,對于具體某個城市在特定發展背景下科技創新能力的評價(尤其是橫向對比)相關文獻較少。建設創新型城市輻射帶動周邊城市群發展,是新時代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本文運用熵值法測算含鄭州在內的中西部七市的科技創新能力,提出針對性建議,為鄭州市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助力高質量發展提供借鑒。
二、鄭州、成都等城市的科技創新能力評價與實證分析
(一)科技創新能力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與數據來源
在借鑒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郭國峰等,2020),構建了4個一級指標體系,13個二級指標體系評價城市的科技創新能力(詳見表1)。基于可比性,選取與鄭州同時入選國家第二批中心城市的成都、武漢、西安以及中部城市太原、合肥、洛陽。數據來源于各市2019年統計年鑒及統計局網站。

表1 科技創新能力評價指標
(二)指標處理與方法
依據構建的科技創新能力指標體系,利用熵值法對4個一級指標、13個二級指標進行權重賦值,進而對鄭州、成都等城市的科技創新能力水平進行客觀評價。
第一步:構建指標矩陣:

上述矩陣給定了n個不同類型的指標,m組城市的評價對象,其中x是評價城市m的指標n的原始數據。
第二步:閾值法對指標消除量綱處理。科技創新能力水平測度涉及多個不同量綱及量級的指標,因此不具可比性,因此需要消除量綱影響后再進行接下來的分析,公式如下:

公式(1)(2)中M和m分別是指標j在所有樣本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第三步:計算各指標熵值、權重。具體如下:
計算各項指標的熵值:

第四步:七大城市科技創新能力水平的測度。根據熵值法測算出來的指標權重,再通過加權法測算各個城市四個二級指標得分,然后計算各個城市科技創新水平總體得分。
(三)測算結果分析
通過運用熵值法,測算出鄭州、成都等城市四個維度指標得分及綜合得分(見表2)。從科技創新能力總分來看,鄭州總分在七個城市中排名第五,科技創新能力總分最高的是成都,其次為合肥。從更加深入微觀的角度可以看出,在科技創新投入方面,西安居于首位,鄭州落后,主要由于鄭州市R&D經費投入強度得分較低,從科技創新產出維度來看,成都得分第一,武漢第二,鄭州居于中等水平,從科技創新環境維度來看,依然成都和武漢數一數二,鄭州市第四名,洛陽市在營造科技創新環境以及科技創新產出方面都比較落后。從科技創新成效維度來看,合肥市居于首位,成都第二,西安最低。

表2 2019年鄭州、成都等城市科技創新水平指數
鄭州市在選取的七個城市中科技創新能力綜合排名第五位,具體來看,科技創新產出、成效和科技創新環境排名第四位,均處于中等水平。科技創新投入指標最后一名,存在明顯的短板。以下將具體對比分析鄭州市在科技創新發展中存在的薄弱方面。
三、鄭州市科技創新能力薄弱方面分析
(一)R&D經費投入強度低
通過上述對比分析,鄭州市科技創新投入指標存在明顯短板,其中R&D經費投入強度低排名最后。鄭州市2019年GDP總值11589.7億元,位居全國第6位,而R&D經費投入117.46億元,位居全國第15位(十五座新一線城市排名墊底),兩者相比非常不匹配。西安、成都、合肥等城市以項目為紐帶,切實用“真金白銀”全面推動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建設,落實財政資金支持科技創新研究,充分激發創新“源頭活水”。另外,萬名就業人員中研發人員數這一指標,西安和合肥遙遙領先,鄭州排名第四位,人才是第一資源,鄭州市在集聚創新資源吸引優秀人才的政策貫徹還并不徹底。
(二)技術市場產出有待提高
鄭州市科技創新產出總體得分在七座城市中排名第四位,屬于中等水平,但與排名前三位的成都、武漢、合肥相比,差距還是比較大。尤其是技術市場交易額占GDP比重這一指標,鄭州市在七座城市中評分表排名最后一名。位居第一的合肥市在應用層,聚焦國家重大需求,抓好國家新興產業重大生產力布局落地,構建高質量發展內生動力。鄭州市技術市場占比大幅度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主要產業結構仍然是傳統行業,產業結構需要進一步優化。
(三)科技創新基礎薄弱
鄭州市科技創新環境水平也顯著落后于武漢、成都、西安,高等教育一直是鄭州市發展的短板,經過多年努力,雖然在數量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質量上與同等發展水平的城市還有不小的差距,不利于形成長期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持續動力。鄭州市只有一所211高校,尚未有985高校,這與其他中部省會城市相比差距甚遠,也與鄭州市較大的人口基數很不匹配。另外,鄭州市累計認定高新技術企業數量這一指標綜合得分也遠低于成都、西安,鄭州市2019年累計認定高新技術企業2048家,僅為成都的不足一半。成都市主推新興產業加快發展,建立科技與金融融合機制,努力搭建投資機構與成都科技成果轉化項目對接的平臺,培育了一批未來細分行業的隱形冠軍企業。而鄭州市多數企業技術水平較低,發展模式仍為粗放式發展。
(四)科技創新成效轉化不足
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是一項系統工程,不僅僅是需要轉化為GDP和財政收入,在當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構建集約型與環保型城市也成為科技創新的成效展現。從指標表現可以看出,鄭州市在空氣質量、資源利用方面存在明顯的短板,鄭州市依靠資源產業使經濟總量不斷提升,但在經濟快速增長的背后,環境形勢卻不容樂觀。因產業轉型以及新興產業的發展需要一定的時間,工業燃煤將繼續帶來大氣的污染。由以上可知,在全面邁向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鄭州市基于科技創新成果在構建綠色發展體系上的成效存在明顯不足,環境整治壓力仍然較大。
四、提升鄭州市科技創新能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對策建議
提升科技創新能力是夯實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驅動力。通過對比分析,并結合《2021版鄭州市推動新型研發機構高質量發展管理辦法》,提出補充建議。
(一)提高科技創新投入,促進創新資源集聚
在提高科技創新投入方面,圍繞鄭州市產業轉型和新興產業培育發展需求,加強對創新型科研機構的支持與獎勵政策以及落實高新技術企業獎勵政策和優惠稅收政策。此外,以科研機構和高校所為依托,在技術轉移轉化與高層次人才方面探索可持續發展機制,保持并壯大科技創新隊伍,通過人才引進政策,引進外部“金鳳凰”在鄭州“筑巢”。最后,通過整合科技創新基金與市內外基金,多方面籌措科技創新基金。
(二)搭建創新平臺,提高科技創新產出數量和質量
在提高科技創新產出方面,鄭州市應堅持問題導向,引進國內運營較成功的科技成果轉化服務平臺(如西安、廈門等市的“科易網”平臺),為企業、專家、高校、科研機構等,提供政策配送、項目申報、技術評估與交易等服務,打通科技創新服務綠色通道,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率。另外,通過采取專家輔導、小班化診斷、上門走訪等對接形式,實施精準服務,解決科技成果市場化過程中出現的各類問題,有效調動各創新主體的自主創新積極性,進而提高科技創新產出的質量和數量。
(三)多舉并措引入科創型企業,優化科技創新環境
在優化科技創新環境方面,第一,圍繞已經規劃好的中原科技城,積極引入科創型企業。借助區位優勢,抓住國家經濟內循環的機遇期,從土地、配套設施及相關政策等多個層面增強吸引力,引入具有競爭力的科創型企業。第二,加大財政教育支出,增加招生數量、高校數量。培育當地科研力量,引進高水平科研團隊,提高辦學質量。最后,精準發力,積極從資金、制度等多方面出臺政策,引導和支持建立產學研協同創新的體系。堅持“走出去、請進來”、多方聯動,激發創新活力,優化創新環境。
(四)推動綠色高質量發展,強化科技創新成果轉化
針對鄭州市科技創新成效在空氣質量和資源利用效率方面存在的明顯短板,首先,加快利用科技創新成果助力綠色產業發展。優化產業結構,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用綠色材料支持綠色建筑產業,用新能源構建綠色交通系統。其次,強化創新示范作用,以點帶面,促進生態環境工作提質增效。最后,充分利用專業環境保護科技平臺,有效進行科研在大氣污染治理與資源利用效率等方面的科技成果轉化,多舉并措加快落實綠色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