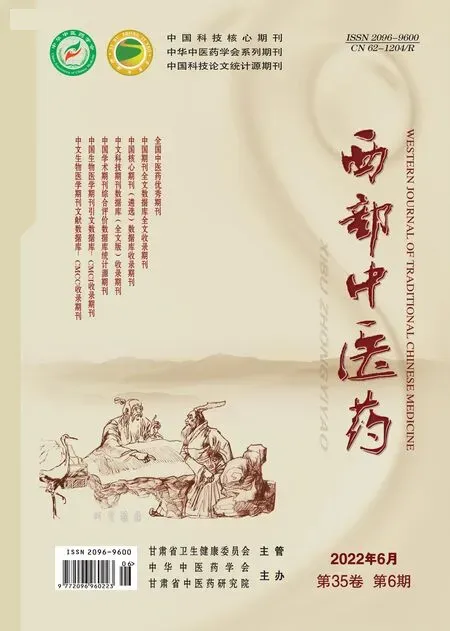基于臨床癥狀探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中醫證素分布及證候特點*
陳金紅,張少強,鄧芳雋,郭圣璇,李曉鳳,杜武勛△
1 天津中醫藥大學研究生院,天津 300193;2 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3 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簡稱新冠肺炎)是新型冠狀病毒引起的傳染性較強的急性呼吸道傳染病[1-2]。根據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頒布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七版)》[3],該病以發熱、干咳、乏力為主要表現,伴有或不伴有肺炎,臨床分為輕型、普通型、重型和危重型。從目前收治病例的情況看,中西醫結合治療該病效果顯著,尤其在中醫藥的全程參與下,患者咳嗽、乏力等癥狀明顯改善,輕型患者易痊愈,普通型向重型轉化較少[4]。此外,在預防新冠肺炎、改善臨床癥狀、縮短病程、減少激素用量、愈后康復等方面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并獲得了世界衛生組織(WHO)的認可。本研究通過流行病學調查的方法,收集匯總新冠肺炎患者的臨床癥狀及有代表性的理化檢查,從證素及證候方面入手,對新冠肺炎患者的證素、證候的分布規律進行歸納總結,探討其病位證素及病性證素的分布特征,以期為該病的中醫診斷和規范化治療提供參考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本研究共納入2020 年2 月1 日至2020 年3 月10 日入院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634 例,分別來源于16 家定點醫院,其中男性336 例,女性298 例;年齡9~92 歲,平均(54.1±16.3)歲;輕型1961例,普通型302例,重型123例,危重型13例。本研究數據來源于新冠新冠肺炎病例信息網絡采集系統(2019-nCoV臨床研究系統,網址:https://tcmae.com/observe/m/login),包含患者基本信息(包括所在醫院)、初始癥狀、病情、體征、中醫現癥、理化檢查、中西醫治療等,主要用于新冠肺炎的病采集和研究,信息收集已獲取武漢江夏方艙醫院有關部門批準。
1.2 數據收集方法在入院當天完成癥狀、體征、舌象、脈象等中醫四診資料及實驗室理化指標所需樣本的采集。
1.3 西醫診斷標準參照國家衛生健康委辦公廳、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辦公室頒布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七版)》中對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有關標準制定診斷標準。1)具有流行病學史:曾有武漢居留史或與確診病例有過密切接觸;2)無流行病學史的患者,需同時具備以下3種臨床表現,有流行病學史的患者,需具備以下臨床表現中的任意2 條:(1)發熱和/或呼吸道癥狀;(2)胸部影像學檢查符合典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特征;(3)發病早期外周血白細胞總數正常或減少,淋巴細胞總數正常或減少。3)具備病原學或血清學證據之一。
1.4 中醫診斷標準參照《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七版)》[3]中中醫辨證臨床治療期的相關內容制定。
1.5 證素診斷標準以臟腑辨證、氣血津液辨證等中醫辨證診治體系進行證候的綜合辨證,證素診斷標準參考《證素辨證學》[5]制定。
1.6 納入標準納入:1)符合上述西醫診斷標準及中醫辨證標準者;2)患者無意識障礙及精神系統疾病,能配合完成病史采集者。
1.7 排除標準排除:1)疑似病例及無癥狀感染者;2)中醫四診信息缺失者。
1.8 統計學方法采用SPSS Clementine 12.0及SAS 9.4統計軟件數據統計,計量資料以xˉ±s表示,中醫證素采用頻數分析、關聯規則Apriori 算法以及聚類分析進行統計。
2 結果
2.1 證素分布將納入的634 例患者的中醫現癥、舌象、脈象、理化檢查結果進行規范化處理,分為病位及病性證素后,共得到病位證素合計827次,病性證素合計1475次。見表1—2。

表1 病性證素頻數分布

表2 病位證素頻數分布
2.2 證素間關聯規則結果使用SPSS Clementine 12.0統計軟件對高頻證素(出現頻數≥20次)進行關聯規則分析,使用Apriori 建模進一步挖掘不同證素之間的組合關系,設置支持度為12%,置信度為80%,最大前項數為5,提升≥1 等條件挖掘出高頻證素中的潛在證素組合,共計得到核心證素組合26種。全部證素組合的提升度均>1,說明這些藥物組合差異有統計學有意義(P<0.05)。26 個核心證素組合的統計結果見表3,高頻證素(出現頻數≥20 次)關聯“網絡化展示”見圖1。

表3 證素之間的關聯規則分析 %
2.3 證素間聚類分析結果運用SAS 9.4 軟件,采用系統聚類的統計方法,以出現頻數在10 次以上的20 個證素作為聚類的對象進行聚類分析,聚類結果如圖2所示。結合圖2及證素特征,共提取到5 組核心證素組合:1)脾、氣虛;2)血熱、毒;3)熱、陰虛;4)表、外風;5)濕、痰、肺。在標尺5 時,“脾”與“氣虛”,“血熱”與“毒”可聚為一類,可歸納證型為脾氣虧虛、血分熱毒。在標尺10 時,“表”與“外風”聚為一類,可歸納為證型風邪襲表。在標尺15 時,“熱”與“陰虛”聚為一類,并且與“血熱”“毒”共同聚為一類,“濕”“痰”“肺”歸為一列,可歸納為證型痰濕蘊肺、肺熱陰虛。見圖2。
3 討論
新冠肺炎屬于中醫學“瘟疫”“疫病”范疇,為感受疫癘之邪而發病。《素問·刺法論篇》云:“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6]對其發病特點的明確定位及對今后的治療指導和轉歸有重要價值。證素是指辨證的基本要素,“證素”是通過對“證候”(癥狀、體征等病理信息)的辨識,而確定的病位和病性,是構成“證名”的基本要素[7]。
本研究納入新冠肺炎患者634 例,共出現證素2303 次。其中病位因素出現827 次,平均每例1.29 個,接近1 個病位證素。臨床最常見的病位證素中包括肺、表、脾,其中肺所占比例最高,達60.00%。盡管此次瘟疫發病初期伴有許多消化系統癥狀,如納呆、乏力、腹瀉,但總體還是以發熱、咳嗽、惡寒等肺衛表證為主要表現,《溫疫論》曰:“此氣之來無論,老少強弱,觸之者即病,邪自口鼻而入。”[8]肺表通于口鼻,在此前匯總的全國24 個診療方案中,有21個診療方案明確病位在“肺”[9]。從三焦辨證來看,“溫邪上受,首先犯肺”,肺表先受邪為病是溫疫類疾病的首發和代表癥狀。
病性證素共出現1475 次,平均每例2.32 個,近似2 個病性證素。常見的病性證素包括濕、熱、痰、陰虛、毒、氣虛、外風,其中濕出現的頻數最高,占病例總數的54.80%,其他出現較多的證素還有熱、痰、陰虛、毒。證素組合中痰+熱、痰+濕、熱+陰虛、毒+濕較為多見,實性證素以濕、熱、痰、毒及外風多見,虛性證素以陰虛和氣虛為主。縱觀全國其他地區專家對本次疫情的病性分析,王怡菲等[9]認為本病的核心證素為“濕、熱、毒、閉、虛”,其中“濕、毒”為本病的核心證素;張樂樂等[10]認為新冠肺炎的病因屬性為“濕毒之邪”,基本病機是濕毒閉肺,升降失司,甚則內閉外脫,病機核心是“濕毒”,以“濕、熱、毒、虛”為特點。目前大多數學者認為,新冠肺炎為實證,常見虛實夾雜[9–12],結合肺、脾二臟的生理功能,痰、濕、熱、毒皆可作祟。再結合三焦辨證,上焦肺燥熱,多耗陰,中焦脾濕盛,多傷陽,故易出現上焦肺燥熱陰虛,中焦脾氣虛濕盛的病理特點。
通過關聯規則,發現肺與痰、濕,外風與肺表,脾與濕、氣虛,肺熱與陰虛常相互夾雜為病,結合聚類分析中的證素組合,臨床中常見證候類型為痰濕蘊肺、痰熱蘊肺、熱毒郁肺、濕毒郁肺、風熱襲表、脾虛濕盛、脾氣虧虛、肺熱陰虛,充分體現出痰、濕、熱、毒、風在新冠肺炎致病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中醫學認為,“百病皆由痰作祟”,脾土不足導致的素體濕盛常與痰邪交互為病,導致病性黏膩纏綿。痰濕毒等邪氣在體內膠結日久,極易郁而化熱,傷津耗氣,出現一系列肺陰虧耗,脾虛氣弱的證候。體現了新冠肺炎隨著病程進展出現證候分布多樣性的特點。在各地中醫藥防治新冠肺炎用藥規律上,預防高頻藥物以甘草、蒼術及藿香使用頻率最高,治療高頻組方以麻杏甘石湯等為基礎方,總體以芳香化濕、清熱瀉肺、解毒通腑為主,且用藥歸經多歸于肺、脾二臟[13],同樣與本研究得出的結論相吻合。
本次新冠肺炎無論從臨床資料分析,還是從五運六氣理論角度來看,“濕”在新冠肺炎中扮演著重要角色[14]。土運不及,則木來侮,金來復,木性升發,且木氣是庚子年初之氣的主氣,自然界的生物和氣候皆自內向外表現出陽氣漸升,風氣漸旺,人體多風熱見證。加之肺金受邪,痰濕、痰熱壅滯于內,若得不到及時消散,便耗傷氣陰,中焦脾胃也見虛實相兼。故在治療時,應該結合患者即刻的癥狀表現,參考《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七版)》中的疾病分期,平衡上下虛實的輕重,祛邪的同時當重視對中焦脾胃的顧護,補虛而不助余邪,以防閉門留寇。此外,不同的地域、氣候特點、個人體質、年齡又會對人體產生影響,因此根據《黃帝內經》中“三因制宜”即“因人、因地、因時”理論制定合適的預防措施和治療方案,才能使防治發揮更好的效果,同時注重瘥后防復[15]。
基于本研究,我們希望對新冠肺炎的病性和病位有一個總體的認識,但由于研究方法有一定的局限性,故而在實際治療中仍要結合不同辨證方法綜合調理患者的機體狀態。且本研究收集病例以輕型和普通型為主,重型及危重型少,故諸如疫毒閉肺、內閉外脫等重癥證候出現頻率較低,證候類型也未必全面,后期可根據重癥患者所占比例按等級計算所需要的樣本量,使分析結果更趨于規范化和標準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