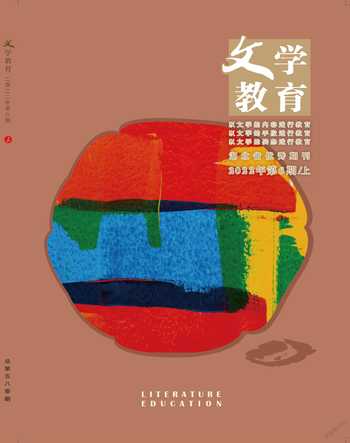小星球

這是真的:有時候只要一抬眼,奇跡就會出現。
那確實是一只石榴。它旁邊的兩只,也是石榴。我已經瞪著它們看了幾十秒鐘,好像眼前街景鋪展,樓群中間突然升起了一顆陌生的星球。
搬來這個小區已有半年多了。我住在四號樓,21世紀的建筑物,但是除了兩部電梯,整棟樓房的布局與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筒子樓并無二致。一條長長的走廊貫穿整個樓層,并且走廊在東,陽臺朝西,冬季罕有陽光入室,盛夏西曬有如失火天堂——為什么一定要設計成這樣?
站在陽臺上看出去,對面就是一號樓的單元入口。再往北,二號樓和三號樓。這三棟樓共用一個小區大門,門口有保安把守。明明是同一個小區,為什么四號樓單獨被排除在外,只配做另外三棟樓的屏風?
商業劃分出服務,資產劃分出階級。人與人之間的分野,就像同一個小區的商品房和回遷房,涇渭分明。
留神觀察,對面三棟樓里的住戶,以年輕人居多;而住在四號樓里的,多為中老年。我的鄰舍,是一對中年夫妻和他們的老母親;鄰舍的鄰舍,人口繁雜,足有五六口人之多——區區六十平方米,真不知他們是如何擠下的。有一天為了什么事咨詢這家的主婦,她眉頭緊皺,掃我一眼,懶得搭腔。大約人在那樣的環境里,是很難涵養出好脾氣的。
剛搬過來的時候,因為時常停水,去問鄰舍的男人,他說這棟樓的供水設施是直上直下,我家和他家并非同一個管道。他家有水,不等于我家也會有;至于我家為什么停水,要問我的樓上和樓下。我跑上去敲401的門,沒人;又敲501,開門的是一對八十多歲的老夫妻,他們告訴我,從一樓到四樓才是同一個管道,總閥在101。他們問我,是租的房子嗎,老家在哪里?聊起來,老先生年輕時曾經當過兵,部隊就駐扎在我老家的Y市。見他們如此年邁,兒女似乎也不在身邊,我想問問他們,是否有什么需要我幫忙,但轉念一想,剛見面就這樣問,似乎并不妥當。
一個人初到異地,又是獨居,總覺得不安。且這樓沒有門禁,外人出入無阻,加上墻壁隔音欠佳,總有些奇怪的響動,讓人疑神疑鬼。我的房間位于最盡頭,走廊里沒燈,夜間走在里面,不開手機手電筒,黑燈瞎火的,著實嚇人;開手電筒呢,想到旮旯里可能埋伏著某個壞人,手電筒會讓自己輕易成為攻擊目標——真正是左右為難。偏偏初來乍到,總有些工作做不完,下班時天色已然黑透。拐進小區大門,迎面撞見一間靈棚,里里外外擺滿花圈和花籃,鑲了黑框的遺照在供桌上默然靜立,一盞白熾燈昏黃地照在上邊。忙不迭垂下眼皮,屏息從靈棚側旁繞過去,總覺得有身影尾隨在后,后頸上涼颼颼的,汗毛直立。一口氣奔上三樓,早早掏出鑰匙,飛快地開鎖進屋,一把按下門側所有的電燈開關,伴隨“咔嗒”的一聲輕響,身后的影子終于被擋在了門外。
小區門口有個修理自行車的小攤,周圍擺了一圈各式各樣的小板凳。只要不下雨,總有幾個老人坐在那里閑談。我留意過幾次,501的那對老夫妻并不在其間。就這樣每天出來進去,慢慢地,也能依稀認得出其中的幾張面孔,但是倘若在別處碰見,卻也不一定能夠辨識出來。人到了暮年,無論男女,看上去似乎總有幾分相似。
就在老人們坐的小板凳后邊,生長著一叢凌亂的灌木,葉片細碎,枝干歪扭,野生野長的樣子。灌木與老人,看上去彼此互為背景;而所有的背景總是退往遠處,如同被時間的風沙蝕過,劃痕遍布,模糊不明。
或許正是因為老人們的存在,讓我每次走到小區門前,總會下意識垂下目光。在中年與暮年之間,只隔著一道低矮的山巒。然而中年的譫妄在于,總是難以坦然面對暮年的降臨。我因而并未發覺,就在那些老人們的頭頂上,榴花似火,將一個個庸常的晨昏點燃。這些稍縱即逝的焰火,一旦錯過,就再也難以重逢,連同那相遇中的驚喜、歡悅、疑竇,甚至幻覺——誰的人生不需要一點幻覺加持呢?
這些花朵的火焰,蝴蝶的幻境,是如何慢慢鼓脹,膨成混沌初分的小小星球?這天生多籽的果實,近似于某種胎生的動物,至死保留著與母體相連的傷口:一顆凹陷向內心的六角星星。
時序已是仲秋,留在枝頭的石榴,大約是最晚熟的幾只?或者,樓角的土質過于瘠薄,這棵石榴樹,總共只結出了這幾只果實?石榴已然熟透,主人何以遲遲沒有采摘?前幾日,我整理雜物間,發現了一根拐杖,它有四只萬向輪,向各個方向皆滑行自如,獨立時亦站得很穩,像一只矮腳長頸的小獸,里面活著一顆倔強的老靈魂。從扶手的高度估算,它的主人應該是一位男性。我的房東是一對六十歲上下的夫婦,而拐杖的主人,想必是他們的父輩——他會是那個種下石榴樹的人嗎?
暮色降臨,眼前的這幾只石榴色澤朦朧,懸而未決,仿佛即將溶解于步步逼近的長夜。
多年以前,我家的院子里也曾經有一棵石榴——說是“我家”并不確切,因為那是我公公婆婆的家。婚后最初的一年多時間里,我們與公婆同住。兩棟房子圍成“L”形,分別構成了院子的兩道邊長,一座長方形花壇則占據了這院子的大部分空間。花壇正中挖有一眼魚池,里面游弋著十幾條金魚,那棵一人高的石榴樹就種在魚池旁邊。必須承認,那是我第一次見到真正的石榴樹,而在此之前,我一直以為石榴是最難養活的植物——我母親曾經試種過不止一次,那些石榴苗養在花盆里,從來未能連續熬過兩個冬季。
我結婚時,正值9月下旬。到了10月份,婆婆收獲了十幾只石榴,全家人分吃了數只,又有幾只送給了來訪的親友,還剩下的幾只,婆婆收在廚房的柜子里。
過了幾天,婆婆說,柜子里的石榴怎么少了一只?
我說,不知道呀。
婆婆狐疑地看我一眼,沒有再說什么。
這曠日持久的羞愧,從來不曾被稀釋過。但為了某個人,它是值得的。
那時候蓮香還在Y市。作為初中同窗,與蓮香之間的友情是如何展開的,我早已無從追憶。只記得那時的晚自習極其漫長,而我已開始近視,一旦輪換到靠窗或者靠墻的位置,書寫在黑板另一側的那些習題,就變成了混沌的湖水,除了反射日光燈的一團白光,剩下的,就是些線條凌亂的漣漪。每一次,都是蓮香匆忙把那些習題抄寫下來,隔著好幾位同學,將本子傳遞到我的手上。初中畢業,我們考進了不同的學校。有一年中秋,有人送給蓮香的父親兩盒月餅。是那種極新鮮的月餅,用料考究,餅皮松軟,沁出棗泥餡誘人的甜香,仿佛前一天才剛剛出爐。蓮香家五口人,所以她分到了兩塊月餅。我們這兩個高中女生,還都文質彬彬地戴著近視眼鏡,就那樣坐在我們學校門口的花壇邊上,一人一塊,把月餅吃掉了。
再后來,我們都畢業了,進了各自的單位。某個周末,蓮香家里做鍋烙。她母親負責包,蓮香負責掌勺,烙得最金黃的幾只,她用一只大碗盛著,偷偷藏在碗櫥的最深處。吃過午餐,家里來了親戚,聽說表哥還未吃飯,蓮香的妹妹說,她看見碗櫥里還有幾只鍋烙呢——誰知卻是遍尋不見。蓮香的母親說,別找了,沒看你姐一下桌就不見了?那幾只鍋烙,一定是給沙爽送去了。
那是一個剛剛豐足起來的時代,多數人的味蕾平生第一次舒展開來。只是那時候,我們還太年輕,除了手中大把的時間,能夠支配的事物是如此之少,無論索取還是給予,總是不能坦然。
再再后來,蓮香就職的那家國營貿易公司瀕臨倒閉,她辭職前往北京發展。又過了幾年,她嫁給一位跨國公司的白領,隨夫君移居威海。
二十年天各一方,音信杳然。我幾次動念尋找蓮香的聯系方式,終究還是放棄了。反過來想想,蓮香若要找我,似乎也并不困難。人類的內心有兩種恐懼同時存在:失落的恐懼,以及失落之物終于尋回卻已不復如初的恐懼。或許,橫亙在我和蓮香之間的,并不是漫長的離別,而是我們早已明了了時光的真相:世事的熔爐會將相同的材質淬煉成迥異的星體,讓它們身不由己,屈服于各自的星系。
(選自《福建文學》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