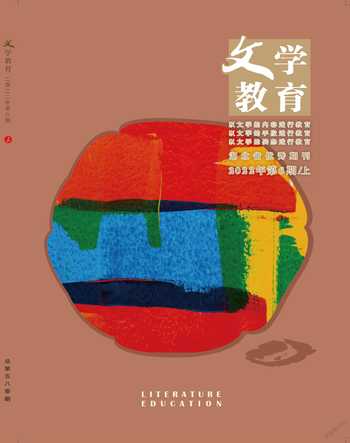異地獨居者的心靈圖譜

沙爽的《小星球》寫的是一段關于租住的異地獨居經歷,作者從故鄉搬到了一個新城市的小區,她像是陌生人般打量著這里的建筑布局以及居民的生活日常。在作者的敘述中,人與人的交往顯得謹慎而節制,“見他們如此年邁,兒女似乎也不在身邊,我想問問他們,是否有什么需要我幫忙,但轉念一想,剛見面就這樣問,似乎并不妥當”,“我”內心的善意與猶疑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我”有能力也樂意幫助這些年邁的兒女不在身旁的鄰居;另一方面,陌生人之間的距離感使得“我”不敢貿然行動。獨居使“我”的內心缺乏安全感,因這棟樓的門禁系統并不完善,隔音效果也欠佳,“我”自然容易疑神疑鬼,于是,下班后回家的“我”擔心黑暗中的某處壞人會攻擊自己,家中燈的光亮成為祛除“我”害怕心理的重要憑借。“我”的獨居生活,充滿了某種不確定性,猶豫、擔憂、糾結等意緒交織在一起,繪制出作為異地獨居者的“我”的心靈圖譜。
饒有意味的是,因租住的小區以老年人居多,“我”的感慨不可避免地帶有對時光流逝的喟嘆,“在中年與暮年之間,只隔著一道低矮的山巒。然而中年的譫妄在于,總是難以坦然面對暮年的降臨”,不論是小區門口自行車修理小攤前老年人的閑談,還是對房東父輩是否種下石榴樹的猜測,抑或雜物間發現的那根拐杖,“垂下目光”是“我”觀察的視角,這種觀看中儼然平添了一絲滄桑感。小區里的石榴令“我”聯想到老家的石榴樹,“我”與婆婆之間因一只石榴心生芥蒂的往事再次重現,與過去一起撲面而來的,還有“我”的好友蓮香,童年的經歷被小星球狀的石榴喚醒,讓人唏噓不已的是,物是人非之感油然而生,那些歲月中的溫暖與美好都定格在遙遠的時空。“我”不敢輕易聯系蓮香,不敢跨越歲月橫亙在我們之間的鴻溝。自然,尋找蓮香也僅僅是“我”的某種心理沖動,一旦觸碰到強大的現實壁壘,重返過去也成為遙不可及的奢望。
在作者的行文中,“小星球”是小區里“我”抬眼發現的一只石榴,這是真實可感的物體,在作者對石榴、石榴樹、蓮香的交往史的書寫中,“小星球”實則演變成一種聯系自身與外在世界的象征體,“小星球”隱含著每一個個體的宿命:“世事的熔爐會將相同的材質淬煉成迥異的星體,讓它們身不由己,屈服于各自的星系。”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小星球”被賦予了某種抽象的哲學層面的意義,人與人在時光的鍛造中必然存在著某種差異,哪怕在起點時經同質同根,最終難免也會分道揚鑣。“小星球”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必然的分野,這種區分是由生活經歷與人生經驗決定的,它不可逆,也無法完全抹去。
如果說《小星球》前半部分重在再現“我”的租住生活、重在描摹“我”獨居的心理嬗變的話,那么它的后半部分則聚焦故鄉的人和事。前半部分觸及的是現在的“我”,后半部分書寫的是曾經的“我”;前半部分與現實生活的關聯性更加緊密,后半部分作為敘述者的“我”已經退到生活的背后,以一種帶有距離的視角來進行呈現。在作者由近及遠的敘述中,“我”的情緒狀態也從相對冷靜變得波動起伏。
在我看來,《小星球》最為迷人之處,就是沙爽的敘述姿態,她像是一個幕后的觀察者,不動聲色地觀察著眼前的人和物,并始終保持著些許的距離,保持著敘述的節制感,被觀察的人與物投射到她的生活中,或濺起層層漣漪,她內心深處卻涌動起巨大的能量,蘊含著豐富的心理信息。作為對現實世界的回應,她的態度顯得異常冷靜和客觀,既不顯山不漏水,不超然物外,也不休戚相關。她始終把從容與善良留給他人,把內心的躁動留給了自己。
周聰,長江文藝出版社編輯,湖北省作協第二屆簽約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