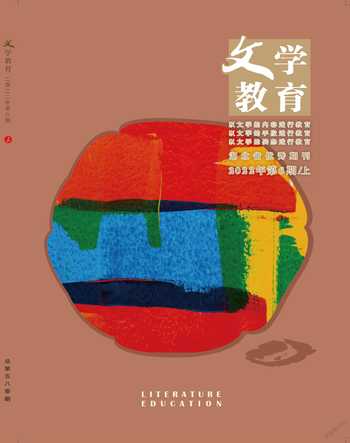《地下室人》:在凝視中存在與終結
王兆瑋
內容摘要:本文以拉康、薩特和福柯的“凝視理論”為主要工具,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地下室人”的形象進行系統分析,勾勒出其內心變化的基本線索:首先,“地下室人”在自我的“鏡像”幻想與他者的凝視中確立自己的存在,而后又在外界凝視所施加的權力壓迫之下走向異化,最后在反凝視的努力中失敗并走向終結。本文不僅通過“凝視”理論深入觀察了“地下室人”的建構與變化、剖析其中所蘊含的對人的存在和價值的深刻反思,更重要的是使其成為人們不斷反思主體與他者、集體與個體之間關系的一個重要橋梁,讓文學研究本身更具現實意義。
關鍵詞:陀思妥耶夫斯基 《地下室人》 “凝視理論” 凝視 異化 反凝視 俄羅斯文學
“凝視”,譯自英文單詞“gaze”,漢語中也常譯作“注視” “盯視”,其基本理論來自于薩特、拉康、福柯三人的精神分析學及哲學著作。現代文化批評中將其定義為“一種與眼睛和視覺有關的權力形式”[1],國內文學批評界對該詞匯的界定如下:“凝視是攜帶著權利運作或者欲望糾結的觀看方法。她通常是視覺中心主義的產物。觀者(the gazer)被權力賦予“看”的特權,通過“看”確立自己的主體位置。被觀者(the gazed)在淪為“看”的對象的同時,體會到觀者眼光帶來的權力壓力,通過內化觀者的價值判斷進行自我物化。”[2]由此可見,“凝視”一詞除卻“看”這一動作本身以外,已然被賦予了與權力和欲望密切相關的社會文化意義。
回歸到《地下室手記》這部作品本身,百年之中它不斷地以多樣化的角度被解讀和闡釋。如1822年米哈伊洛夫斯基在論文《殘酷的天才》中將陀氏的創作分為兩個階段,即側重描寫羊被狼吞食時的感受和狼吞食羊的感受。他認為《地下室手記》就是作家詳盡描寫狼吞羊時感受階段的開端。但是筆者的看法稍有不同,《地下室手記》恰恰是將這兩種感受雜糅在了一起——“狼”和“羊”正是在凝視與反凝視的過程中發生了位置互換,而這一點在地下室人和麗莎的對話之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進入20世紀以后,對該作品的分析逐漸轉向了哲學和詩學層面,舍斯托夫將其視為“一篇反理性的宣言式作品”,美國哲學家考夫曼則將小說的第一章定義為“最好的存在主義序曲”。在巴赫金重獲重視的60年代,他對小說主人公的獨白話語進行細致分析后指出:“地下人在同自己、同他人、同世界進行交談。……地下人是陀氏塑造的第一個思想者的形象,這是以進行意識活動為主的人物,其全部生活內容集中于一種純粹的功能……認識自己和認識世界。”[3]弗里德連杰爾認為:“地下室人在敵視他的社會為他準備下的無數災難和屈辱中生長……”,在馬爾科姆·瓊斯看來:“《地下室手記》寫作上那種自我暴露的風格正是解構主義的本質特征……在他人和自我的關系上保持著一種不斷顛覆的狀態……”[4]綜合以上不同側面的信息及筆者本人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結論:1.《地下室手記》涉及了存在與本質、理性與自由、個人意志和集體意識等存在主義經典命題;2.“地下室人”的獨白中包含著一系列雜語,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與他者(此處既包括幻想中的“小他者”,也包括實際存在的“大他者”)進行的對話;3.“地下室人”渴望獲得他者(此處指周圍的人群和社會環境)的認同但是始終無法得到理解,從而轉向了自我折磨以及對相同處境的“同貌人”(此處指麗莎)的折磨。
“凝視”理論常被用于探討和分析女性問題、種族問題、殖民問題等等文化領域的重要命題。但本文卻以他者的“凝視”中自我確立與異化問題為主線,通過對“地下室人”形象的剖析,厘清其在他者的凝視中尋找自我、迷失自我、奮力抗爭的過程。法國思想家讓-雅克·盧梭的政治著作《社會契約論》開篇就提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 (這里的枷鎖原指契約之上建立起來的國家),自由雖然是人與生俱來的稟賦和權利,但現實中的人卻不得不像“地下室人”一樣在集體的凝視中徘徊思索、彳亍前行。
一.從“鏡像”到“他人即地獄”——“地下室人”的存在與異化
首先,談到主體這一概念,就無法繞開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他認為“注視”使得主體與他人之間建立關系,兩者都在彼此的目光中確認存在。但是與此同時,被凝視的一方往往處于“凝視”的包圍之中,產生羞恥、驕傲乃至虛榮的情感感受,即“我在我的活動之中把別人的注視當作我自己的可能性的物化和異化”[5]。這無疑會造成一種高位者對低位者的權力壓迫,同時迫使被凝視者作出改變去迎合“凝視”所反映出來的取向。
很多學者認為“地下室人”是自我意識極強的、追求自由的、注重反思的一個與眾不同的個體,這當然是這個形象的一個相當重要的側面,但是更重要的是“地下室人”時刻處于一種擔憂、恐懼和憤恨之中,其中的大部分來自于對他者“凝視”的一種揣測和畏懼,小說第二章描寫“地下室人”過去的生活經歷時就曾寫出他隱秘的內心活動:“我也十分清楚地發現,我的同事們不僅把我當作怪人,而且——我一直覺得就是這樣——似乎還用某種厭惡的目光在看我。……我甚至可以承認臉上的表情下流無恥,只要別人同時認為我的臉聰明絕頂就行。……我生怕自己顯得可笑,甚至害怕到病態的程度,因此我奴性十足地崇拜有關儀態舉止的一切成規慣例。……沒有一個人與我相似,我也不與任何人相像。‘我只是唯一,而他們是全體’。”[6]除了這段典型的“凝視”描寫之外,小說全篇都處于一種和暗含的讀者以及內心矛盾的對話之中,且這種對話主要是建立在主人公對外界“凝視”的反應之上。“地下室人”在開篇對自己的定義即是:“我是個病人……我是個兇狠的人。我是個不招人喜歡的人。”而他在和軍官較勁、努力擠進“朋友”西蒙諾夫的小團體的過程也就是試圖通過他者對自己的“凝視”來證明自己的存在,維護自己的自尊心和虛榮心,但最后他發現自己“既成不了兇狠之徒,也成不了善良之輩;既成不了流氓無賴,也成不了正人君子;既成不了英雄,也成不了蟲豸。”甚至連他所畏懼的他者和社會的“凝視”都已經消失了,別人把他當做“整個世界的一只蒼蠅”,徹底忽視了他的存在,否定了他的價值。關于注視和見證薩特曾說過這樣一段名言:“由于我們存在于世界之上,于是便產生了繁復的關系,是我們使這一棵樹與這一角天空發生的聯系……這個風景,如果我們棄之不顧,它就失去見證者,停滯在永恒的默默無聞的狀態中……”[7]可以說,見證是存在的見證,人的存在需要他者的見證。“地下室人”在他者的“凝視”之中畏縮、惶恐,他者凝視中帶來的并不是肯定而是否定,他始終未能得到一只渴求的對存在價值的“見證”,他人也終成地獄。
拉康的“鏡像階段”理論是從薩特的主體理論和弗洛伊德的窺淫癖理論繼續延伸出來的,這一理論原指六個月左右的嬰兒能夠在第一次目睹自己鏡像時辨認出自己的形象,拉康認為這種情景認識是人類智力發展的關鍵一步,本質上也是確認自我存在、獲得自我認識的第一步。但與此同時,拉康也指出,鏡中形象盡管給主體帶來了肯定自我存在的喜悅,但它實質上卻是一種虛無的、異化的幻象。這種幻像便是拉康所說的與自我幻象相對應的“小他者”(即“地下室人”幻想中的正直、無私、有尊嚴的自己),而與真正主體相對的“大他者”(即“地下室人”周圍的環境和環境中的各色人物)才是將主體確立下來的必要客體。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主人公窺視著軍官的一舉一動,通過各種方法試圖為自己受到的羞辱討回一個公道,最后通過撞一下肩膀(軍官甚至并未注意到這一撞)“達到了目的,在大庭廣眾之中使自己與他處于完全平等的社會地位。”其實,主人公的這一行為是頗具“阿Q精神”的一種自我安慰,他在一種實現目標的虛幻滿足中給自己建構出了一個“高大威猛的英雄”形象,以這個“小他者”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和自尊心。當然,這里并不是對“地下室人”形象的徹底否定,畢竟正如主人公所說:“所有那些率直的實干家和活動家之所以如此生龍活虎,是因為他們蒙昧無知,目光如豆。”即使只是一種幻想,“地下室人”也望向了鏡子中,試圖去尋找自己存在的意義和價值,但是他周圍的“大他者”仍然處于蒙昧的迷霧之中,他們順從于社會凝視所形成的權力威壓,而后憑此在集體之中獲得一種安全感和尊嚴,再把這種凝視投向于任何一個試圖反抗的“地下室人”。
這也就涉及到了福柯在《瘋癲與文明》中所闡釋的一種內涵于“凝視”目光中的知識與權力的運作。醫生有權以治療疾病、馴服瘋癲的名義,通過自己的專業醫學知識和技能對病人進行單向度的觀察。《規訓與懲罰》中提到的邊沁的全景敞視主義監獄的構想也給出了一個更具啟發性的解讀方式,即社會并不是一個公開的社會,而是一個監視的社會。高位者通過全景敞視的結構來監管所有下位者,但是所謂的“高位”也只是相對的,最終必然會形成一個監視的循環。在福柯的理論中,“凝視”的主要內涵在于“監視”,這也是知識和權力運作的必然結果。而當人淪為各類凝視、社會常態化監視下的產物時,人已成為客體,成為毫無主體性可言的對象——他人,因此福柯得出結論:“人死了”,“真正的自我已經被他者化了”[8]。“地下室人”正是不服從于這種權力監視的人,他獨立而自由的反思使其無法盲目地參與到這個大循環之中,因此他雖然在雙重“他者”中確認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卻永遠無法站到“凝視”鏈條的更高一層。那么,在各種努力都失敗了以后,他又是如何進行“反凝視”的呢?
二.反凝視的失敗——“地下室人”的終結
“凝視”是一個雙向的動作,凝視者與被凝視者是可逆的,他們的位置擁有互相轉換的可能性,這就是“反凝視”一詞得以出現的原因。“地下室人”也多次做出類似嘗試,從對軍官的“報復”、到努力加入西蒙諾夫的小團體,他都試圖通過一些行動獲取他人的尊重,證明自己的存在和平等,以求瓦解“凝視”行為中的二元對立。但是與此同時,他的內心對于這種行為又是極其鄙視和不屑的,在內心的這種矛盾之中他的“反凝視”行動常常以失敗告終。
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失敗便是“地下室人”和麗莎之間的交往經歷。從“女性凝視”的角度來看,這段故事首先來自于男性對待女性時的一種欲望,將女性他者化、對象化、客體化,他們在女性身上看到了這種欲望的匱乏,按照女性主義者的觀點,這時男性會采取以下兩種做法:1.妖魔化女性;2.物化女性[9],這兩種貶低行為的最終目的就在于站在凝視者的高位上“教訓”女性。“地下室人”在受到西蒙諾夫小團體的無視和侮辱后,開始對妓女麗莎進行道德訓誡,他表示“男人和女人根本不能相比。完全是兩回事;我雖然自暴自棄,糟踐自己,可我卻并非任何人的奴隸……可拿你來說吧,從一開始就是個奴隸。”由此可見:主人公此時就是把自己放在了一個凝視者的立場上,通過語言將麗莎從想象界帶入象征界(拉康語),試圖掌控麗莎的敏感善良的心靈,最后在看到麗莎“可憐的、扭曲的、不必要的微笑”的時候他感覺到了片刻的勝利。只可惜小說結尾麗莎來拜訪他的時候正看到他受辱,因而他為自己建立的凝視者之高位迅速轉變成了被麗莎所“凝視”的低位。
“地下室人”反凝視的失敗并不在于缺乏反抗精神和反思意識,而在于社會凝視所形成的權力壓迫本身就非常強大,他試圖反凝視的意志又是不堅定的、左右搖擺的、充滿懷疑的。或者說,他始終無法從來自于他者的“凝視”目光中掙脫出來,“忙于無盡無休地尊重自己”,時時刻刻感到“我被注視”,不斷體驗到“我的為他的存在”,所以他無法完成對“凝視”的最終解構。叔本華早早就對此問題有過經典的解答:“人性一個最特別的弱點就是,在意別人如何看待自己。“地下室人”試圖在他者的“凝視”中確立自己的存在,導致了個性的異化,最后嘗試以“反凝視”的方式恢復尊嚴,結局卻是否定了個人的存在價值。
本文以“凝視”理論探究的“地下室人”形象變化的意義不僅僅在文學分析本身。而是“地下室人”作為個體面對“集體凝視”的一個折射,其更深遠的意義在于揭示出一種自我反思和社會反思的必要性——個人在集體的“凝視”中如何自處?“凝視”中如何確立自我的存在意義?“反凝視”的意義何在?無論是在文學研究還是文化研究中,被凝視的“地下室人”的現實意義才是其出發點和落腳點。
參考文獻
[1]丹尼·卡瓦拉羅著.張衛東等譯.文化理論關鍵詞[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127.
[2]趙一凡主編.西方文論關鍵詞[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349.
[3]巴赫金著.白春仁,顧亞鈴譯.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4]馬爾克姆·瓊斯著.趙亞莉,陳紅薇,魏玉杰譯.巴赫金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80-90.
[5]薩特著.陳宣良等譯.存在與虛無.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6.331.
[6]陀思妥耶夫斯基著.臧仲倫,曾思藝等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07[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5.6.440.該作品引文都出自此處,以下不再另作注.
[7]柳鳴久選編.薩特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2-3.
[8]王曉路等著.文化批評關鍵詞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324.
[9]朱曉蘭.“凝視”理論研究[D].南京:南京大學.2011.82-95.
(作者單位:北京外國語大學俄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