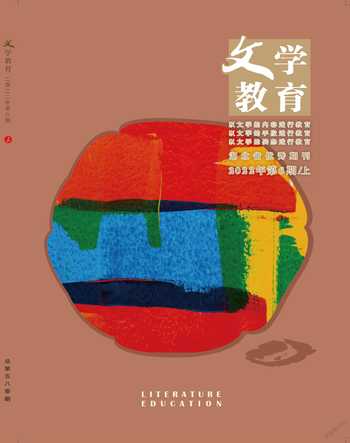“17年文學”中的女性英雄形象及其敘事
張倩
內容摘要:當代文學史上的“17年”是一個推崇英雄的時期。這個時期的文學作品中,英雄敘事是主流文學敘事方式之一。而女性英雄作為與男性英雄對立統一的存在形式,能更真實客觀的反應文學作品的主流價值和審美走向。本文將嘗試從“17年”時期作家筆下的女性意識著手,分析文學作品中的女性英雄形象,探究“17年文學”的英雄敘事特征。
關鍵詞:當代文學史 “17年文學” 女性意識 女性英雄形象
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后,文學為政治目的服務的基調基本確立。而此后的“17年”文學,其生態在主流意識的影響下具備了濃厚的時代氣息,這種時代氣息展現在文學作品的敘事特征上,即虛構和現實疊加的英雄敘事。英雄敘事從字面來看就是講述英雄如何走向成功的過程,主人公一般是平凡的個體,他的事跡有可能是虛構的,也有可能是真實發生的,但不管真實與否,在現實與虛構的交叉敘事中反映出英雄的共同特點就是堅定目標、勇往直前、一路披荊斬棘、可歌可泣,從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故事。“17年文學”集中使用了這一敘事方式,甚至說“17年”是當代文學史上使用這一寫作方式最鼎盛的時期,并為整個新中國文學創造出了一批具有現實價值的英雄形象。事實上,人物形象的塑造很大一部分要通過人物獨立意識的覺醒、成長來刻畫,因此我們嘗試挖掘女性意識的覺醒,從作家們對女性英雄的形象描寫來分析這一時期的英雄敘事特征。
一.意識形態引導下的虛構性英雄敘事
女性意識是女性擁有完整且獨立的人格,在具備一定的思考力或在外界作用力的加持下,認同自身除性別特質以外的其他感受及價值后,而自我覺醒的非物化產物。從個體本身角度出發,它體現在兩個維度:一是從女性角度出發,不限于性別界限,看待世界的目光;二是從性別特質出發重新定義自己的審美角度,審視自身的目光。
(一)“17年文學”中的女性意識
女性是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不可缺少同時也無可替代的角色,然而漫長的封建社會里,女性的生活方式被限制于男權創立的條條框框,女性的地位被男權弱化,女性的價值依附于男性,甚至僅僅體現在“傳宗接代”。1916年啟蒙運動的文化陣地《新青年》專欄探究了“女性問題”,大批作家針對“三從四德”等封建舊俗提出疑問。1919年的五四運動,新思潮涌入,西方女性獨立生存的社會現狀與我國女性封建傳統的壓制產生碰撞,沖破舊思想和舊環境下的社會生活,塑造出一批新獨立女性,在經濟獨立和社會責任方面都展現出同男性并肩而立的氣概。這個時期的文學作品也能夠較為清晰的反映出女性意識隨著女性在社會事業的融入過程中開始成長。
文學作品能夠較為客觀的展現一個時代的風貌。新中國成立初期至文革前后,也就是“17年”時期,在推崇英雄的“17年文學”中,女性渴望擺脫傳統的約束,表現出同男性一般強烈的人格獨立和參與社會生產的意識。如李畢的《李雙雙小傳》中的主人公李雙雙;羅廣斌、楊益言的《紅巖》中的雙槍老太婆;楊沫的《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靜;柳青的《創業史》中的秀蘭等。
恩格斯說:“婦女的解放,只有婦女社會規模的參加生產才有可能實現。”[1]李雙雙是“17年文學”中一個較為出名的人物,如現代文學中大多數人評價的那樣,她是個“鐵一般的女人”,她的身上兼具男性的陽剛直爽和女性的溫良敦厚。小說一開篇就寫道雙雙是孫喜旺的愛人,仿佛她并不是一個擁有“獨立”存在意義的人,甚至她的名字在村里也少有人知,而更多的是使用代稱,比如“喜旺媳婦”、“喜旺嫂子”,丈夫在外對她的稱呼也是“俺小菊她媽”、“俺屋里人”等,這一系列描述可以稱之為是男權引導下的社會生活的最好體現,女性從屬于男性和家庭,女性的價值仍然依賴于男性的存在而存在。在1958年的春天,大躍進開始后,雙雙的世界才發生了一點點變化,“家務事,真心焦……整天圍著鍋臺轉,躍進計劃咋實現”[2]寫著幾個歪歪扭扭的字的大字報讓大家驚訝,這也是李雙雙作為一個家庭女性第一次突破家庭而表現出來的“叛逆”,這種“叛逆”不僅僅是對長久周旋于家庭事務的反抗,更具有一種“女英雄”的氣勢,就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腳步而產生的迫切的想要參與社會生產的欲望。她不滿足于日復一日的生活現狀,主動打破傳統,走出家門,上學識字,追求同工同酬,參與修水渠,研究如何喂豬,被評為模范…李雙雙這個人物越來越多的活躍在男性視野中,可以說在新的制度的發展階段下,李雙雙的一系列事跡都能作為女性反抗從屬地位的代表事件,同時也展現出她在追求自身存在價值的過程中,從女性的角度出發而不局限于性別特質,審視世界的女性意識逐漸被喚醒。
在專門解讀女性文學的研究中,“17年文學”里的女性缺乏性別色彩,這一時期的文學中,女性意識或淡漠,或遮蔽,或潛隱。[3]意在指出女性的性別特征不夠明顯和突出,男女界限模糊,女性意識在關注世界這一層面被喚醒的同時,在關注自身的層面越來越薄弱,甚至瓦解。但是這一說法并不具有概括和代表性,如果說《李雙雙小傳》中的李雙雙這一女性對世界的審視角度極大的被限制于女性在不同時代和特定環境下,那么女性對于愛情和婚姻的態度則能很好的展現對自身原始欲望的追求,比如林道靜。
林道靜是“17年文學”里極具個性的人物,在《青春之歌》里,她聰明、美麗、溫婉,是充滿活力和散發光芒的女青年,是成長于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家庭的知識分子,性格剛強,思想先進,不滿足于被安排的婚姻命運,扔下一句“我寧可死,也不做軍閥官僚的玩物!”[4]便與封建家庭決裂,抗婚后幾經輾轉只身前往北戴河謀生,此時的她作為一個女學生已經能夠分辨女性的部分自我價值,她對愛情和婚姻有獨立的思考和看法,可以說她已經是一個逐步走向思想上獨立,靈魂上自由的新女性了;而后結識了那個有騎士風度的男人并與她成為伴侶,大膽的追求自己的愛情,從關注自身的角度來說,女性意識的覺醒體現在她內心勾勒出的對于獨立愛情的模樣。但是她并非是典型意義上的賢妻良母,她不甘于做一個平凡的家庭主婦,最終雙方人生價值的不對等促使她離開了愛人,毅然決然投身于革命,關注政治局勢,參與發傳單、革命游行等活動鼓勵人們積極抗日,關心國家前途命運,多次入獄遭受酷刑,這一系列的磕磕碰碰使她逐漸從一個知識青年成長為一個無產階級戰士,林道靜以最初的對婚姻愛情的堅守為契機,到后來加入中國共產黨,從關注世界的角度,女性意識的覺醒體現在不囿于性別界限,把自我融入家國之中,把女性的命運同國家的前途緊密聯系起來。
(二)“17年文學”中的獨立女性形象
從某個時期的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追尋這個時期的文學并不是一個新穎的方式。但是通過對人物形象的研究和把握卻能很好的反映作品的風格和基調,挖掘作品的敘事方式,探究敘事特征。“17年文學”作品與其他時期的文學作品中的人物有很大的不同,不管是《保衛延安》中的周大勇、彭總,《林海雪原》中的楊子榮這些男性英雄,還是我們前面分析過的李雙雙和林道靜這兩個女性,他們的共同特征就是帶有傳奇色彩,人物身上凝結著濃濃的愛國主義情懷,以及在形象刻畫過程中人物與時代相匹配的獨立意識。女性相對于男性更直接打破了人們對于性別的認知,給我們開辟出一個全新視角,構建出一個理想主義傾向的女性生命情態。我們看到的不再是處于弱勢地位,一味服從的傳統女性,而是勇于斗爭、渴望平等的新女性。
李雙雙是一個潑辣、倔強的人,性格爽朗,敢說敢做。小說中描寫的她在精神世界這個層面與男性一樣,有著不可多得的干勁,而在外貌特征上也不是文學作品中一貫討喜的“林妹妹”式女性,相反的從語言、性格特質、外貌特征都表現出了健壯、堅韌的特點。從小說中的具體描寫可以看出她的形象符合社會生產所需要的條件,也就是說她的形象與當時時代發展的需求,或者說在歷史進程中女性角色的轉變是十分匹配的;她是一個公正無私、大義滅親的人。向老支書提出興辦公共食堂,為了辦好它,盡心盡力,在丈夫不愿意成為炊事班的成員而撒謊自己不愿聞見蒸饃氣時,雙雙揭穿了丈夫,并積極的自己加入食堂,做起炊事員,并和丈夫說道:“保護黨提出來辦的一切事情,誰破壞,就和他斗爭!”[2]在挖出金樵家藏起來的水車時,雙雙“越想越氣,睡不著”[2]孫有提出不入公社,商議著與雙雙家共同使用,卻被雙雙立馬拒絕,“布衫大衣一裹就沖出去了。”[2]立即匯報給了老支書。在得知丈夫喜旺幫助孫有做過壽的五碗大菜而偷偷挪用公共食堂的東西時,不顧私人利益和情分,毅然揭露這種不正確的做法,并讓喜旺寫大字報道歉……在當時的社會生活環境下,作為一個家庭從屬意義上的女人萌生出女性意識,敢于沖破男權的壓制,并時刻表現出一心為公的思想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而從故事的一系列情節可以看出作者將李雙雙這個人物的形象有意識的進行了理想化和美化。
(三)理想性、虛構性的英雄敘事
李雙雙在形象上刻畫的理想化和美化,實質上更多的是從這個人物如何看待公社的角度來寫作的,也就是說文學作品的形象創造極大的限制于當時的社會環境,公社正是需要雙雙這樣思想的人,也需要通過雙雙這樣的女性向社會傳達女性在生產環境中的作用和地位。文學在“17年”時期被當作實現政治意圖的傳聲筒,作家的文學創作自由得到了限制,極大的社會需求使得文學作品中的男性形象或者女性形象都有清晰而模糊的“模板”,清晰在于主要人物的思想情感偏向都展現出一致的對黨的擁護,對黨領導下的事業充滿希望和干勁,模糊在于這些人物處于不同生存狀態下、不同情感經歷成長中的各個階層。在雙雙批評丈夫去道歉和想到金樵家藏著水車實際上是心不在社里,故而氣急敗壞睡不著這兩件事情上,我們可以看出雙雙作為一個農村女性在維護公社利益也即國家利益時身上的不貪圖小利,無私和高大,也許這與我們接觸到的社會生活現實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我們說這個人物參雜一些假設成分,是一個過于理想化的存在。這樣的人物比比皆是,還有《紅巖》里的江姐,江姐被捕后被關在渣滓洞集中營,在獄里她遭受了非人的待遇,敵人妄圖用饑餓和干渴動搖革命者的意志,用竹簽戳進十指的酷刑逼迫江姐就范,但江姐堅韌不屈,甚至高喊“共產黨的意志是鋼鐵鑄成的”[5];林道靜一個柔弱女子,兩次入獄,受盡摧殘,第二次被捕后,拒絕在《自首書》上簽字,遭到敵人的嚴刑拷打,在獄中待了一年,出獄后終于如愿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不論是江姐還是林道靜作為女性承受的不單是與性別不相符合的身體痛楚,給讀者帶來的最直接的沖擊是突破人性所能承受的范圍。
因此單單從女性的人物形象去窺測這個時代以英雄為主角的文學作品,關于英雄敘事的寫作方式我們可以進行大膽的推測和判斷,就是帶有理想主義色彩和虛構藝術意味的寫作。
二.現實環境引導下的真實性英雄敘事
“十七年文學”的英雄不論男女,總是帶有時代意味,人物形象的塑造在迎合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發展的過程中可能產生一些夸張或隱藏的處理。為凸顯人物形象背后的精神意義而稍顯理想化,但是文學作品在離開現實的基礎上創作是危險的。老舍先生說語言是生命與生活的聲音[6]。十七年文學的敘述是一定程度上的現實主義寫作,作品誕生的寫作背景為這一寫作手法的形成創造了充分的條件,新中國成立前歷經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一系列事件,時代的風云變幻會催生更多的時代故事的講述者,也會影響講述者關于時代的思考,這種思考體現在文學作品中即敘述的變化。十七年時期的作家大多親眼見過戰爭的殘酷,因此我們在很多作品中都可以看見作家對于戰爭給人情感沖擊的描述,比如杜鵬程在《保衛延安》的創作過程中他所要極力展現出來的正是自身對于人民解放戰爭的宣泄,他說道:“難道積壓在我心里的東西,不說出來我能過得去嗎……這不僅是創作需要,也是我內心波濤洶涌般的思想情感的需要”[7]懷揣著這樣的創作沖動的作家在十七年文學作品流域中并不少見,也正是這樣的義不容辭的沖動,使得作品塑造了很多,或者說真實反映了很多戰爭英雄。
《紅巖》的作者楊益言和羅廣斌都曾是戰爭中摸爬滾打過的人,經歷了戰火和血液的洗禮,在他們創作的《紅巖》中,重點敘述了重慶解放前夕殘酷的地下斗爭,特別出彩的獄中描寫尤為牽動人心。小說中英雄層出不窮,女性英雄像江姐、雙槍老太婆都是現代文學中極具代表性的典型形象。
(一)戰爭洗禮下的女性意識
雙槍老太婆在小說第十四章中的描寫是一個讓人聞聲喪膽的人,警察局長前一秒還威風凌凌,下一秒看見隔壁桌的老太婆“大吃一驚,朝后一退,把椅子也絆倒了”,“她仿佛看見老太婆的白太綢長衫底下暗藏的兩支上了膛的快槍,只要老太婆的手稍微一動,子彈就會穿透他的腦袋”[5],以及后文寫道他的一系列肢體動作,比如手腳發抖、連連哈腰都側面展示出雙槍老太婆在惡勢力面前極大的震懾力。老太婆是戰爭年代一個獨立、剛強、堅韌的女性,在李敬原告知她謀劃營救集中營里被捕戰友的事情上,她表現出急切又激動的心情,仿佛一個從未經歷戰爭的戰士一樣擁有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氣概,毫不退縮且堅定的說“多給點任務吧,挑的動的”,“我們保證完成指定的一切任務,盡量多救出一些同事來”[5]。大多數軍事文學作品中,女性并沒有作為主要人物在戰爭中被突出,這源于這一類型文學語境中對女性描寫的局限性。但是《紅巖》在描寫英雄的過程中,并沒有像其他軍事文學作品一樣,直面戰爭激烈的場面,通過渲染戰爭的屬性,花大量的文筆和情感去描摹主要英雄在一場戰爭里的突出地位,而是從側面切入,將文本所要傳達的核心要義從精神折磨和信仰堅定這兩個角度的沖突去對比反映。江姐被捕入獄,在獄中的種種磨難和隱忍就能充分的反映作者的這一寫作特點,以及老太婆在營救被捕同志這件事情上表現出來的關懷和對黨的服從,也展示了她對斗爭和解放的認識,這兩個女性的共同之處都是對于信仰的堅守,堅定不移的跟隨黨的步伐,相信信仰的力量可以成為斬斷一切苦難的利刃。在《紅巖》中,凸顯的女性意識所展現的角度不同于林道靜和李雙雙,更多的反映了革命者對生命意志的思考,挖掘支撐生命意志生生不息的背后精神,把女性的獨立意識發展融入到整個社會對信仰的認識發展之中,與中國革命一路走來的發展態勢交相呼應。
(二)“十七年文學”中的傳奇女性形象
十七年文學為女性立傳的小說很少,女性英雄由于自身和時代的雙重局限性,很難成為戰爭的主角,但是在十七年文學所塑造的英雄群像中,女性的形象反而是多元化的,有飽受摧殘還堅貞不屈的女英雄,有革命洪流中大義凌然的老母親,有歷史舞臺中斗志昂揚的女知識分子…這些極具歷史情感特征的女性類型在十七年文學中對構建故事的合理性、豐盈故事情節、推動情節張力等方面都具有突出的貢獻。在《紅巖》里,女性人物出現的不多,有沉穩機敏的江姐、有愛憎分明的雙槍老太婆、有勇敢堅強的孫明霞、成瑤。江姐是推動《紅巖》故事發展的主要人物之一,她是一個比較豐滿的藝術典型,她是一個妻子,更是一個共產主義戰士,她擁有地下工作者豐富的工作經驗和警惕沉穩的工作方式,在看到丈夫的頭顱被掛在城頭上示眾時她悲痛萬分,但共產主義戰士的身份使得她不得不克制住自己的感情,故作鎮靜,化喪夫之痛為視死如歸的勇氣,擔負起丈夫的那一份責任繼續做好地下工作。在苦難的牢獄環境中,出于對社會制度的思考和不滿,教獄友們新的制度思想,默寫《新民主主義論》和《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供大家學習研讀;為躲避重慶特務的跟蹤,拼命努力學習三個月考上號稱“民主堡壘”的四川大學;借著難友出獄的機會,帶去家書教導兒子“盼教以踏父母之足跡,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到底”。[5]江姐這個人物的豐滿過程圍繞著對革命意志的堅守,人物形象也隨著故事情節的展開逐漸明晰,一個堅韌、沉穩、勇敢的女性革命者躍然紙上。雙槍老太婆不同于江姐的是她身上的革命氣息不是知識分子的義憤填膺,而是從一個平凡的老百姓角度出發,讓我們看到了普通大眾對于革命的激情和奉獻,她是一個傳奇的女性形象,有些剛強如同男性一般,作為華鎣山游擊隊的隊長,嫉惡如仇、手持雙槍,讓敵人聞風喪膽,始終保持對黨和國家忠誠不二。在叛徒甫志高告密導致眾多革命同胞被捕時,她毅然決然的槍斃了叛徒,為保持革命隊伍的純潔絕不手軟。賦予人物傳奇和生命意義的是這個人物自身從女性主義角度出發,在與封建禮教相對抗的過程中活出了一種英雄氣概,這種氣概是在革命年代十分難得的。
(三)寫實性、真實性的英雄敘事
馬克思主義對文學的總的界說和規定提到文學是對生活的能動的反映。[8]也就是說文學事實上屬于人的一種活動,從具體的性質方面來探究,或者從馬克思主義哲學中關于存在和意識的這一基本理論入手探究,把文學活動看成作家這個主體對于客體的認識和反映。十七年文學中的關于戰爭的場面,以及塑造的英雄人物,或來自于作者宏大的模擬想象,或來自于作者的親眼所見,無可厚非所有的敘述都有歷史的影子,在作品中我們能找到被“塑造”的時代的痕跡,真實的人物事跡也隱藏在傳奇、宏大的故事情節之下。《紅巖》的作者之一楊益言先生曾經說,雙槍老太婆這個角色有三個原型,都是中國共產黨員,分別是鄧惠中、劉隆華、陳聯詩,鄧惠中是一個在封建社會被裹腳的女性,但出于對革命的一腔熱血,積極參與練兵習武,指揮軍事訓練,為起義籌備資金,聯絡武器和彈藥,是華鎣山游擊隊的主心骨、領頭羊,因上級發給她兩支槍,而號稱“雙槍老太婆”。陳聯詩和劉隆華也是構成雙槍老太婆的最主要原型,都曾率領雙槍隊參與華鎣山區的多次戰斗,傳奇經歷家喻戶曉。好的文學作品留給后世的不單是曲折離奇的情節走向和無懈可擊的藝術結構,還有字里行間透露出的歷史文明和文學精神。《紅巖》中的江姐,作者的筆下她是一個堅貞不屈的巾幗英雄,影響和激勵著幾代年輕人的愛國情懷生生不息。她的原型是革命烈士江竹筠,曾被評為“100位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年少時的江竹筠認識到自立自強的重要性,積極參加抗日戰爭的宣傳,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奮不顧身投身革命事業,在遭受國名黨反動派老虎凳、辣椒水、代詞鋼鞭、電刑等多種殘忍迫害時,仍舊堅定不移。在文學創作中記敘真實人物事跡的故事更能激蕩人心,寫實性、真實性也是十七年文學作品的一個最主要的特點。因此,我們可以說從《紅巖》中的女性形象看到十七年文學的英雄敘事樣式,是真實性、寫實性的文學寫作。
縱觀現當代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隨著時代的變遷不難發現作家在刻畫人物時有了與時代發展相照應的側重點,女性形象相較于“養在深閨人不知”的類型,出現更多的是能與男性平分秋色的新女性,尤其在新思想大量涌入的歷史時期,比如十七年時期。女性形象在介于虛構化和真實化之間,透露出時代嬗變的氣息,文學作品的敘事樣式也隨之成型。
參考文獻
[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轉引自李銀河.婦女:最漫長的革命[M].三聯書店,1997:13.
[2]李準.李雙雙小傳[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
[3]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關鍵詞十講[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4]楊沫.青春之歌[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
[5]楊益言,羅廣斌.紅巖[M].中國青年出版社,1961.
[6]老舍.語言與生活[M].北京:作家出版社,1964.
[7]熊坤靜.黨史博采.紀實(上)[J].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2):51-54.
[8]盧允慶,林志香.能動反映論的多維解讀[A].太原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9(4).
基金項目:2020年甘肅省高等學校創新能力提升項目(2020A-121)。
(作者單位:隴東學院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