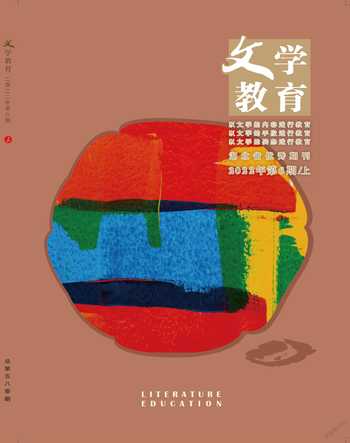論《一個(gè)無(wú)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的再改編
馬景濤 胡靜
內(nèi)容摘要:自1924年洪深改編的《少奶奶的扇子》上映后,“中國(guó)化”的改編形式初現(xiàn),改編劇不僅拉開(kāi)現(xiàn)代戲劇帷幕,更是解決“劇本荒”的不二法門(mén)。少有原創(chuàng)劇目的孟京輝在二十世紀(jì)末將達(dá)里奧·福據(jù)意大利真人真事創(chuàng)作的戲劇——《一個(gè)無(wú)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進(jìn)行改編后搬上中國(guó)舞臺(tái)。孟氏版本不僅改變了原著的劇作結(jié)構(gòu)及人物設(shè)定,且在此基礎(chǔ)上增添個(gè)人一以貫之的先鋒元素,筆者謂之“顛覆性改編”。
關(guān)鍵詞:孟京輝 《一個(gè)無(wú)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 改編 顛覆性
1998年這部由意大利戲劇家達(dá)里奧·福原著,黃繼蘇改編,孟京輝執(zhí)導(dǎo)的政治諷刺劇——《一個(gè)無(wú)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在北京兒童劇院上演。在達(dá)里奧·福獲得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的次年,一直致力于實(shí)驗(yàn)、先鋒話劇的中國(guó)導(dǎo)演孟京輝將其最具代表性的名劇搬上中國(guó)舞臺(tái)。此并非這一名劇首次在中國(guó)上演,賴(lài)聲川翻譯,表演工作坊演出的《意外死亡(非常意外!)》在基本遵循原版故事框架的基礎(chǔ)上已于1995年在臺(tái)灣上演。與之不同的是,孟京輝改編的《一個(gè)無(wú)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非但沒(méi)有貼近原著,甚至與編劇黃紀(jì)蘇版都相去甚遠(yuǎn)。現(xiàn)代劇作家李健吾曾對(duì)改編作出評(píng)論,他認(rèn)為“改編越具備再創(chuàng)造的情況,價(jià)值也就越大”,從這一角度看,孟京輝對(duì)該劇全盤(pán)的顛覆性改編似乎具有的價(jià)值更大,但至今并未得以公認(rèn),故本文不探討其改編的價(jià)值,而著重分析其在哪些方面進(jìn)行改編,何謂之于“顛覆性”。
一.劇作結(jié)構(gòu)與人物設(shè)定
無(wú)論是原著抑或孟版,都體現(xiàn)出了一定的理想主義傾向,即小人物向掌權(quán)者的權(quán)威進(jìn)行挑戰(zhàn)。達(dá)里奧·福的《一個(gè)無(wú)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開(kāi)篇以犯罪的瘋子在警察局的審問(wèn)而開(kāi)始,而后進(jìn)行一系列的由瘋子主導(dǎo)“無(wú)政府主義者意外死亡”的始末,最終在記者的追問(wèn)下,謊言一步步被戳破,真相公之于眾。而孟京輝改編版并未設(shè)定無(wú)政府主義者已經(jīng)死亡的既定前提,而是按照傳統(tǒng)的線性敘事展開(kāi)。開(kāi)局便毫無(wú)保留的講述這名無(wú)政府主義者死亡的原因,其后警察如何一步步處理這一事件的完整行為,并欲借瘋子來(lái)編排無(wú)政府主義分子的死亡全過(guò)程,以期為警察掩蓋真相。與達(dá)里奧·福原著相同的是,劇中的瘋子同樣在排演無(wú)政府主義者死亡的種種“完美”方案,欲掩人耳目時(shí)卻順藤摸瓜地進(jìn)行了一系列調(diào)查,洞悉出全部?jī)?nèi)情,并進(jìn)行了痛快淋漓的揭露與斥責(zé)。達(dá)里奧·福原著的劇作結(jié)構(gòu)的設(shè)定中,關(guān)于無(wú)政府主義者的一切皆由瘋子扮演的“法官大人”與警察之間的對(duì)話展露殆盡。而孟京輝的劇作結(jié)構(gòu),則是將無(wú)政府主義如何死亡以及警察如何處理的全過(guò)程表演出來(lái)。
原著的瘋子承擔(dān)著揭露事件真相的任務(wù),而孟版中他在警察殺害了無(wú)政府主義者后登場(chǎng),不再擔(dān)任“破案者”,而作為警察的“點(diǎn)子”式的人物出現(xiàn),他不斷幫助警察尋找向公眾解釋無(wú)政府主義者死亡的“完美方案”,徹徹底底的為警察掩飾罪行而服務(wù),顯然不是主動(dòng)對(duì)當(dāng)局的深層批判與丑惡罪行的強(qiáng)力揭露者。
達(dá)里奧·福版主要角色為七人,除瘋子外設(shè)有警察局長(zhǎng),警長(zhǎng)甲、乙,警察甲、乙以及女記者,每一個(gè)人都在“戲中”,對(duì)最終真相的和盤(pán)托出發(fā)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孟版沿襲了原著角色較少的設(shè)定,一個(gè)瘋子、三名警察與一名發(fā)廊女組成了這出意外的主要參與者。誠(chéng)然,角色的差異是孟京輝在進(jìn)行改編時(shí)一個(gè)創(chuàng)新的地方。尤其原著中女記者的改動(dòng)成為劇評(píng)人爭(zhēng)論的焦點(diǎn)。應(yīng)該看到,刪除女記者使得故事中的瘋子從始至終維持著“導(dǎo)演”的身份,無(wú)政府主義者死亡的真實(shí)經(jīng)過(guò)與警局處理此事的多種嘗試均由瘋子通過(guò)自導(dǎo)自演的一場(chǎng)場(chǎng)戲而展露無(wú)遺,其行為的荒誕與真相的殘酷性形成鮮明的對(duì)比。另一方面,取代女警察的“發(fā)廊女”在警局需要女性協(xié)助時(shí)出現(xiàn),此形象的設(shè)定將警局的虛假做作推上高峰,展現(xiàn)了警局欲在尋求最終“完美方案”的無(wú)底線丑臉。
除此之外,孟版亦有一個(gè)直觀的人物替換,即原劇作中代表社會(huì)黑暗與正義,不斷揭示社會(huì)內(nèi)在矛盾以促進(jìn)故事不斷向前發(fā)展的“畫(huà)外音”被兩名小丑所替代。彼得·格雷澤談到:“改編中最有意思的就是所謂的‘干預(yù)’”[1],由周迅與孟京輝本人飾演的小丑在劇中不斷的跳入跳出,介紹人物、朗讀詩(shī)文、播報(bào)新聞、歌唱等行為層出不窮,他們“干預(yù)”劇情發(fā)展,并不斷的提醒觀眾這是“戲”。兩位小丑并非簡(jiǎn)單的輔助故事發(fā)展,他們的出現(xiàn)給予了該劇更多的現(xiàn)實(shí)因素,且富有更為深層的含義,即他們?cè)诟嬖V觀眾“我們”此刻的角色在為人民發(fā)聲,為民主呼喚。
二.“徹底的”本土化
學(xué)者朱恒夫在總結(jié)怎樣讓西方戲劇劇目與戲曲有機(jī)地相結(jié)合時(shí),其中有一點(diǎn)經(jīng)驗(yàn)是:“讓其劇目的故事高度‘中國(guó)化’,即除了保留被改編劇目的主要故事情節(jié)與主題思想外,故事發(fā)生的時(shí)代背景、地點(diǎn)、人物都要“中國(guó)化”,最好連名字也要改成中國(guó)人的名字。”[2]此雖論及戲曲,但從“大戲劇”的概念看,與之類(lèi)比并非南轅北轍。孟京輝搬演時(shí)在其如何更好的實(shí)現(xiàn)“中國(guó)化”方面花費(fèi)諸多心思,無(wú)論出于商業(yè)利益而做出的決定,抑或從藝術(shù)價(jià)值進(jìn)行思考,不可否認(rèn)的是與其它移植劇強(qiáng)加本土化元素不同,孟京輝的本土化改編不可謂幅度不大,甚至是“徹底的”。
在北京出生的孟京輝深受北京文化之影響,首次上演便選擇北京似乎亦有某種深意,劇中諸多北京元素的出現(xiàn)便不足為奇。如,警察甲、乙審犯人時(shí),刻意地用類(lèi)似:“無(wú)政府那孫子,你丫出來(lái)嘿”、“打出你丫屎來(lái)信不信”等這種略帶粗俗的北京片兒話。不僅在語(yǔ)言上,故事講述中也充斥著北京文化的獨(dú)有印記。最為鮮明的莫過(guò)戲仿老舍先生的名作——《茶館》。這部揭示近半個(gè)世紀(jì)中國(guó)社會(huì)黑暗腐敗、光怪陸離的劇目與此次上演的《一個(gè)無(wú)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毫無(wú)關(guān)系,但孟京輝將《茶館》嵌入故事發(fā)展,將一部“意大利”戲劇加入進(jìn)老北京滿(mǎn)清貴族的一套封建生活風(fēng)貌竟毫無(wú)違和感,更是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戲劇效果。當(dāng)警察甲提著鳥(niǎo)籠,局長(zhǎng)一口“喲,這不是‘無(wú)爺’嗎”,瘋子說(shuō):“誰(shuí)呀?”局長(zhǎng)接:“小王呀,給您請(qǐng)安了”,說(shuō)著話緊趕著左手抖摟右手,用傳統(tǒng)的滿(mǎn)清貴族方式給“無(wú)爺”請(qǐng)安。二人互致請(qǐng)安禮后,局長(zhǎng)問(wèn):“您今兒個(gè)怎么那么閑在,有工夫到我們警察局來(lái)了?”瘋子回答道:“我來(lái)看看,看看你這個(gè)年輕的小伙子會(huì)不會(huì)開(kāi)警察局”。這一段發(fā)生在《茶館》中的經(jīng)典對(duì)話,被局長(zhǎng)和瘋子搬到《一個(gè)無(wú)政府主義者意外死亡》的舞臺(tái)。這段頗具諷刺性的模仿中,警察局長(zhǎng)成了裕泰茶館中見(jiàn)人請(qǐng)安、仰人鼻息的掌柜的王利發(fā),而瘋子搖身一變成了手握大把地權(quán)的秦二爺,此時(shí)的瘋子與警察局長(zhǎng)的身份、地位發(fā)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翻轉(zhuǎn),身份的隨意置換不僅展現(xiàn)出該劇荒誕的一幕,更極大的諷刺了當(dāng)權(quán)者的做派。不禁令人將意大利當(dāng)局和昏庸腐敗的滿(mǎn)清政府聯(lián)想起來(lái),唏噓不已。
劇中一些巧妙的小設(shè)計(jì)與頗具“俏皮”的語(yǔ)言包袱同樣充斥著本土的意味。例如,在全劇開(kāi)頭所有演員站在臺(tái)前共同哼唱那首“屁”順口溜——“達(dá)里奧·福,放了一個(gè)屁,崩到莫斯科,來(lái)到了意大利,意大利的國(guó)王正在看戲,聞到這個(gè)屁,很不滿(mǎn)意……”。借以小孩子哼唱的順口溜來(lái)調(diào)侃達(dá)里奧·福,令觀眾忍俊不禁的同時(shí),也似乎給本劇“徹底的”本土化改編奠定了基礎(chǔ)。更有甚者,在劇中穿插“來(lái)到了天津衛(wèi),是嘛也沒(méi)學(xué)會(huì),我學(xué)會(huì)了開(kāi)汽車(chē),我軋死了二百多……”中國(guó)傳統(tǒng)曲藝的藝術(shù)手法,其歌詞雖不甚高雅,但以其尖銳的詞句批評(píng)與諷刺了九十年代政府官員貪污腐敗的政治現(xiàn)象,讓觀眾嬉笑之余繼而產(chǎn)生對(duì)社會(huì)不良風(fēng)氣的聯(lián)想與反思。但全劇“尺度”最大的還數(shù)改編“火車(chē)向著韶山跑”這一童謠,“車(chē)輪飛,汽笛響,火車(chē)向著美國(guó)跑,越過(guò)高山越過(guò)海,迎著霞光千萬(wàn)道,嘿,迎著霞光千萬(wàn)道。”一代又一代中國(guó)兒童唱過(guò)的紅色革命歌詞,被孟京輝巧妙運(yùn)用于“窮爸爸富爸爸”[3],諷刺了當(dāng)時(shí)彌漫于中國(guó)大地的唯利是圖、崇洋媚外的社會(huì)風(fēng)氣,尤其是“美國(guó)的月亮圓又圓,美國(guó)的鈔票滿(mǎn)天飄,滿(mǎn)呀滿(mǎn)天飄”其矛頭直指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流傳的“外國(guó)一切好,外國(guó)的月亮都是圓的”這類(lèi)現(xiàn)實(shí)問(wèn)題,極大的抨擊了這種扭曲的社會(huì)言論,將當(dāng)時(shí)高干子弟的美國(guó)行為進(jìn)行強(qiáng)烈的譴責(zé)。
改革開(kāi)放后,隨著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高速發(fā)展,人民的生活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與此同時(shí),各種社會(huì)及個(gè)人層面的弊端層出不窮。孟版此番“徹底的”本土化不僅適應(yīng)中國(guó)觀眾的觀劇習(xí)慣,難能可貴的是在劇中不僅展現(xiàn)了意大利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更是將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的社會(huì)問(wèn)題融入其中,在給予觀眾代入感的同時(shí),隱喻和諷刺了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的不良風(fēng)氣和不法行為。對(duì)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直接批判在以往孟京輝戲劇中并不常見(jiàn),該劇一改其固有風(fēng)格,對(duì)此孟京輝自己也表達(dá):“這是一部‘人民戲劇’”,反映人民的感情,表達(dá)人民的心聲,直指社會(huì)的弊病。
三.先鋒的實(shí)驗(yàn)性
以實(shí)驗(yàn)戲劇起家的孟京輝在其早期戲劇作品中大膽打破傳統(tǒng),盡顯先鋒姿態(tài)。如《思凡》、《我愛(ài)XXX》等都有著顯著的實(shí)驗(yàn)性。雖在《一個(gè)無(wú)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中孟京輝將其筆墨更多的用于展現(xiàn)社會(huì)問(wèn)題與控訴現(xiàn)實(shí)的不公,但依然有著熟悉的“孟氏先鋒味”。
與主流戲劇開(kāi)場(chǎng)即展開(kāi)劇情不同,孟版的《一個(gè)無(wú)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開(kāi)頭別出心裁,連同孟京輝飾演的小丑,主創(chuàng)七人聚集在舞臺(tái)上。伴隨著音樂(lè)他們用粉筆在黑板上畫(huà)出該劇主要的人物,還將其性質(zhì),即觀眾常說(shuō)的“好人”、“壞人”之分傳遞給觀眾。雖然這種行為一改常規(guī)戲劇之態(tài),但起到讓觀眾帶著對(duì)人物形象的既定認(rèn)識(shí)進(jìn)入劇情的目的。
上文提及,作為導(dǎo)演的孟京輝飾演了一個(gè)小丑,他和另一位周迅飾演的小丑在全劇中有多處議論性的話語(yǔ)以及朗誦,加之吟唱等方式。他們介紹達(dá)里奧·福、布蘭卡·拉梅;他們朗讀意大利官方媒體對(duì)爆炸案及無(wú)政府主義者意外死亡的報(bào)道及評(píng)論;他們控訴意大利存在已久的社會(huì)暴力;他們撥弄吉他,高聲歌唱。他們甚至帶著“旁觀人”的視角,進(jìn)入故事,時(shí)不時(shí)的發(fā)表評(píng)論,如:“在米蘭的大街上要不要帶刀?”等。兩位小丑的出現(xiàn),造成“離間效果”的同時(shí),亦在推動(dòng)劇情、幫助觀眾更好的揣摩故事以及在表達(dá)作者思想傾向等方面起到不可磨滅的作用。
孟京輝一以貫之的實(shí)驗(yàn)性還表現(xiàn)在獨(dú)特的舞臺(tái)設(shè)置,一個(gè)較為空蕩的場(chǎng)地,一個(gè)裸露的話筒架、三把椅子、一個(gè)吊著的沙袋、一條繩索,在兩塊高大的鐵皮下圍起了一個(gè)封閉的舞臺(tái)。左側(cè)巨大的“達(dá)里奧·福”畫(huà)像、能夠向上攀爬的窗戶(hù),右側(cè)單獨(dú)設(shè)置的小樂(lè)隊(duì)和坐席,延伸到觀眾席的舞臺(tái)等共同構(gòu)成了整部戲劇的敘事空間。在這個(gè)空間中,演員根據(jù)劇情,時(shí)而跑去窗戶(hù)處排演無(wú)政府主義者跳窗的方式與跳落的姿勢(shì);時(shí)而跑去觀眾席中。尤其是與觀眾互動(dòng)的這一行為,它發(fā)生在瘋子不愿再繼續(xù)編造故事而藏匿于觀眾席時(shí),警察們四處尋找,瘋子請(qǐng)觀眾幫忙掩護(hù),最后兩個(gè)警察百般諂媚將他“求”回審訊室。演至此處所有的觀眾被調(diào)動(dòng)起來(lái),此刻他們不僅僅是觀眾,亦代表“人民”這一群體,集體為瘋子撐腰。英國(guó)戲劇家彼得·布魯克曾把“觀眾”作為戲劇的三要素之一,并認(rèn)為戲劇創(chuàng)作的最后一步是由觀眾完成的,孟京輝顯然將觀眾融入戲劇創(chuàng)作之中。這一方式打破“第四堵墻”,挑戰(zhàn)傳統(tǒng)的觀演方式。孟京輝對(duì)該類(lèi)觀演關(guān)系的試驗(yàn)在一年后的《戀愛(ài)的犀牛》中再度上演。值得一提的是,該劇審訊室的布局頗有寓意,整個(gè)舞臺(tái)并沒(méi)有搭建起一個(gè)專(zhuān)門(mén)的審訊室,舞臺(tái)即審訊室,令人不禁聯(lián)想到薩特存在主義戲劇《禁閉》的地獄,后現(xiàn)代主義戲劇的象征意義已不言自明。
語(yǔ)言的狂歡是孟京輝戲劇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此種頗為幽默又充滿(mǎn)著尖銳的自嘲語(yǔ)言在劇中可謂比比皆是。例如,找來(lái)瘋子排演這出無(wú)政府主義者意外死亡的劇目,當(dāng)他尋求保命的方式時(shí),警察局長(zhǎng)問(wèn)他:“那得看你鉆圈的功夫怎么樣了”,瘋子回答道:“鉆圈是咱演員的基本功啊,我在戲劇學(xué)院跟沈博士學(xué)過(guò)兩年的英式鉆法”。當(dāng)瘋子鉆完圈后,警察乙不禁感嘆道:“我靠,我一直不服啊,”警察甲同樣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緒說(shuō)道:“演員不就是敢當(dāng)中親嘴嗎?”警察乙連忙又補(bǔ)充道:“就至于拿那么多錢(qián)?”說(shuō)完二人齊聲說(shuō):“真冤枉他們了”。通過(guò)瘋子和演員的幾句對(duì)話,形象生動(dòng)的諷刺了當(dāng)時(shí)演技一般卻有不菲片酬的演員,作為演員的他們同時(shí)也是自嘲與反諷。論及反諷,不得不提劇中經(jīng)典的一段,局長(zhǎng)要瘋子做一個(gè)堂堂正正的導(dǎo)演,便指示他手中的圈就代表窗戶(hù),瘋子端詳著圈,便反問(wèn):“您要搞實(shí)驗(yàn)戲劇?”此刻無(wú)論是演員還是觀眾都哄堂大笑,瘋子扔掉圈,情緒激昂的說(shuō):“其實(shí)我頂看不上那幫先鋒派,在舞臺(tái)上擺十個(gè)八個(gè)電視、十個(gè)八個(gè)破紙盒子,把舞臺(tái)搞的廢品站不是廢品站,收購(gòu)站不是收購(gòu)站,如今還有人在舞臺(tái)上砌水池子的,還有人把屋頂都搬上了舞臺(tái),分明是現(xiàn)實(shí)主義功力不夠,所以才嘩眾取寵”。在這里,孟京輝用“先鋒”的戲劇形式對(duì)“先鋒戲劇”品頭論足,將在中國(guó)逐漸流行開(kāi)來(lái)的實(shí)驗(yàn)戲劇進(jìn)行一番挖苦與諷刺,當(dāng)然也是孟京輝本人的自嘲。
孟京輝《一個(gè)無(wú)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在原著上做出了顛覆性的改編,在給觀眾帶來(lái)搞笑戲謔、荒誕滑稽的同時(shí),更將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的諸多問(wèn)題融入其中,在笑聲中留有思考,在戲謔中直指社會(huì)弊病。雖然這種顛覆性的改編引發(fā)社會(huì)上不小的爭(zhēng)論,但是導(dǎo)演的創(chuàng)作個(gè)性與深層思考無(wú)疑深嵌其中。孟京輝在考慮商業(yè)利益的同時(shí),對(duì)于社會(huì)的思考與激烈控訴卻絲毫未有減弱之勢(shì)。改編國(guó)外戲劇,無(wú)論質(zhì)量?jī)?yōu)劣都存在些許的爭(zhēng)議,究竟是忠實(shí)于原著還是將其重新詮釋?zhuān)靡匀碌膽騽”磉_(dá),一直是討論的焦點(diǎn)。孟京輝改編的《一個(gè)無(wú)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無(wú)疑選擇了后者,即在原著的故事上加以本土化,繼而融入導(dǎo)演的個(gè)性與風(fēng)格,連帶將國(guó)內(nèi)社會(huì)的弊病進(jìn)行一番控訴,雖與原著顛覆較大但有著極強(qiáng)的現(xiàn)實(shí)意義與時(shí)代意義。
參考文獻(xiàn)
[1]呂同六.一個(gè)無(wú)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M].南京:譯林出版社,1998.
[2]孟京輝.先鋒戲劇檔案增補(bǔ)版[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3]管玲玉.孟京輝先鋒戲劇的接受研究[D].揚(yáng)州:揚(yáng)州大學(xué),2016.
[4]李莎.當(dāng)代中國(guó)導(dǎo)演對(duì)西方戲劇經(jīng)典的四種誤讀[J].戲劇,2001(03).
[5]黃德海.意大利的節(jié)慶狂歡和中國(guó)的滑稽傳統(tǒng)——一個(gè)無(wú)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的原作和改編[J].中國(guó)比較文學(xué),2003(04).
注 釋
[1]李亦男:《“劇本改編課程淺談——美國(guó)加州大學(xué)伯克利分院戲劇系主任格雷澤教授訪談錄”》,《戲劇》2012年第二期,第50頁(yè)。
[2]朱恒夫:《中西方戲劇理論與實(shí)踐的碰撞與融匯——論中國(guó)戲曲對(duì)西方戲劇劇目的改編》,《戲曲研究》2010年第一期,第30頁(yè)。
[3]羅伯特·清崎以親身經(jīng)歷的財(cái)富故事展示了“窮爸爸”和“富爸爸”截然不同的金錢(qián)觀和財(cái)富觀。本書(shū)1999年4月在美國(guó)出版。
(作者單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學(xué)藝術(shù)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