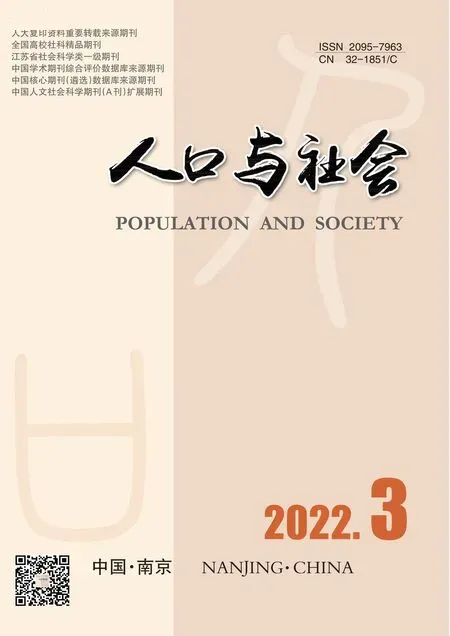城市落戶門檻對流動人口犯罪率的影響
章 平,楊 帆
(深圳大學 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廣東 深圳 518000)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口開始出現大規模的流動。對于流入地而言,這一過程不僅會對勞動力市場帶來沖擊,也帶來了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的問題。一般來說,對勞動力有較高需求的地區會吸引大量流動人口流入。流入地的落戶門檻體現了該地的戶口人數狀況以及經濟發展狀況,流動人口融入流入地的過程也是對當地落戶門檻認同的過程。
城市落戶門檻是導致勞動力回流的重要因素,尤其對低技能、跨省流動、農村戶籍和健康狀況較差的群體有顯著影響[1]。有研究發現,城市落戶門檻過高會抑制流動人口的創業、阻礙農民工子女隨遷、加劇收入不平等[2-4]。但目前已有文獻大多聚焦在城市落戶門檻對農民工及其下一代的影響上,較少研究其對流動人口個體行為方式的影響。事實上,落戶門檻的變化會導致流動人口對該地區身份認同的變化。在落戶門檻較低的地區,流動人口落戶比較容易,對當地有著更高的認同感。在落戶門檻較高的地區,流動人口落戶比較困難,進而降低他們對該地區的認同感。值得關注的是,大規模人口流動是導致中國犯罪率急劇上升的“主要原因”[5]。隨著中國省域間人口的不斷流動,各地區人口的戶籍多樣性增強,加大了本地人口與流動人口之間的身份認同差異。在中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各地區的落戶政策也在變化。落戶門檻的高低變化與流動人口的身份認同之間的碰撞是否會影響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犯罪行為的發生?本文以落戶門檻與流動人口犯罪率為切入點,來考察流入地區落戶門檻對流動人口在該地區犯罪行為的影響。
中國流動人口規模龐大,截至2016年底,中國流動人口總數已經達到了2.45億人,比2009年增長了2 500萬人。流動人口犯罪率也逐年上升,據統計,2016年全國每萬人流動人口犯罪率為29.3%,比2009的22%增長了7.3%。這給社會穩定和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帶來了嚴重的不確定性,也造成了巨大的社會損失。我們認為區域落戶門檻的高低與流動人口對該地區的認同及社會融合之間的沖突可能是導致流動人口犯罪率不斷升高的原因之一。
二、文獻綜述與理論假說
近幾年來,國家出臺了新一輪的戶籍制度改革政策,持續放寬了對落戶的限制。但是從改革效果來看,落戶難題正從落戶難轉變為落戶意愿和落戶條件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想落而無法落與能落而不愿落的現象并行。已有研究發現落戶門檻高并不能夠逆轉人口向大城市集聚這一趨勢,反而會造成留守兒童數量增加,并且加劇了收入不平等現象在代際間的傳遞[4]。近年來,開始有文獻關注落戶門檻對流動人口的影響,有研究發現落戶門檻與流動人口創業行為之間存在顯著負相關關系[2]。此外,也有學者研究指出,取消部分中小城市落戶限制對當地人口增長并不會產生很大的影響[6-7]。
犯罪率是用來衡量社會穩定的重要指標之一,生理、心理、社會因素、文化環境等都是影響犯罪行為發生的重要因素[8]。Mauricio Leiva通過對智利各市的數據進行研究發現,移民數量的增加和大多數類型犯罪的犯罪率的提高并沒有直接關系,移民數量與故意搶劫罪之間存在著負相關的關系[9]。Christian Gunadi通過對美國臨時合法化政策進行研究,發現這一政策的出臺提高了犯罪的機會成本并且會減少財產型犯罪行為[10]。近年來,有文獻開始關注犯罪行為的男女性別差異,Tony Beatton通過對澳大利亞犯罪數據的分析發現,犯罪行為性別差異顯著但呈現縮小的趨勢[11]。中國對于流動人口犯罪率的研究主要包括:(1)最低工資上調使流動人口的失業率上升,而失業會提高流動人口犯罪的可能性[12];(2)人口流動和犯罪有較高的關聯度,尤其與較嚴重的犯罪產生更緊密的關系,主要是受居住狀態等因素影響[13];(3)宗族文化與城市犯罪率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的關系[14]。目前關于落戶門檻與流動人口犯罪率之間關系的研究較少。
與已有文獻相比,本研究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不同:第一,以往研究大多關注地區經濟水平與流動人口犯罪率的關系,本文側重研究流入地政策對流動人口犯罪率的影響;第二,以往研究主要以農民工為對象,本文則以流動人口為對象;第三,本文分析了落戶門檻對流動人口犯罪率的影響,并驗證了身份認同影響流動人口的犯罪率這一關鍵機制;第四,構建“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這一新的變量,為后續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通過對中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CMDS)和中國裁判文書網數據進行分析,發現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對流動人口犯罪率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在控制了是否有犯罪前科、收入、受教育水平、民族和年齡等一系列變量后,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對流動人口犯罪率的負向作用仍然顯著;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通過改變流動人口的身份認同感來影響流動人口犯罪率。落戶門檻對流動人口犯罪率的影響路徑可能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落戶門檻通過影響流動人口的收入而對犯罪行為產生影響。無收入或收入低導致流動人口犯罪的機會成本降低,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流動人口犯罪率的提高。流動人口流動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收入,流入地通常是經濟發達、地區生產總值較高的地區。當流動人口面臨經濟困難又沒有好的解決方法時,則容易產生犯罪的念頭和行為。
第二,劉琪等人研究指出,農民工對城市的認同有利于其積極尋找工作、消除心理危機以及改變消費模式,從而促進其制定長久發展規劃以及融入城市[15]。包括農民工在內的流動人口身份認同感的提升,能提高其工作積極性。當他們在城市受到社會歧視,身份認同感低時,犯罪的可能性提高。
第三,流入地的相關政策會對流動人口的犯罪率產生影響。根據張丹丹等的研究,最低工資上調使流動人口失業率上升,而失業會提高外來務工人員犯罪的可能性[12]。流入地的落戶政策對流動人口犯罪行為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落戶門檻較高的地區人口密度通常較高,流動人口基數大,犯罪率也會提高。本文的理論假設如下:
H1: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對流動人口犯罪率起著顯著抑制作用;
H2: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對流動人口在流入地受到的社會歧視有正向影響;并且流動人口受到的社會歧視程度越高,在流入地的犯罪率越高。
三、數據、變量和模型選擇
在借鑒已有實證研究的方法和模型設計的基礎上,根據本研究所選取的變量具體情況結合本研究實證目的進行對應的模型設計。模型設計主要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和中介效應模型,研究各省市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對流動人口犯罪率的影響,最后通過剔除典型省市數據進行穩健性檢驗。
(一)數據來源
本文所使用的數據來源于中國裁判文書網所公開的2000—2018年323 454條裁判文書數據,同時還使用了國家衛健委流動人口數據平臺所公布的2017年中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A卷),西南財經大學經濟與管理研究院、公共經濟與行為研究平臺、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于2021年3月公布的2000—2016年中國城市落戶門檻指數。該機構所公布的數據將2000—2016年劃分為兩階段:2000—2013年為第一階段,2014—2016年為第二階段。本文所使用的省級落戶門檻指數為各省所含市級落戶門檻指數的均值。本文根據各省市的年度統計年鑒,選取按照綜合指數標準核算的落戶門檻指數。
(二)變量選取與描述性分析
1.變量選取
(1)流動人口犯罪率
在對流動人口犯罪行為的研究中,本文基于中國裁判文書網公布的數據,按照犯罪者的戶籍特征,得到2000—2018年我國流動人口犯罪總數,并按照各省市的年末總人口,計算出2000—2018年各省區市的流動人口犯罪率。由于年末落戶戶口數的范圍為2009—2016年,因此在回歸分析中選取2009—2016年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犯罪數據,共計318 753條。
(2)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
本文的解釋變量是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是根據各省市落戶門檻指數和各省市年末落戶戶數計算得來,即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各省市在統計年份的年末落戶戶口數/該年的落戶門檻指數,并將此解釋為各省市的落戶門檻指數對該省省級落戶戶數的影響效應指數。這里的落戶門檻指數采用綜合指數標準,包含了投資、購房、人才引進以及普通就業,通過投影法計算得出。之所以選取“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作為“落戶門檻”的代理指標,主要原因有:
第一,西南財大團隊公布的落戶門檻指數按照時間分成了2000—2013年、2014—2016年兩個階段。如果直接采用,各個年度的落戶門檻指數取值只有兩種情況,2000—2013年為取值1,2014—2016年為取值2,這與本文所要觀察的每年度連續動態變化情況不符,而且直接進行計量回歸,會因為取值單一且無變化降低計量分析效果。
第二,選用各省市在統計年份的年末落戶戶口數來除以該年所在統計時段的落戶門檻指數,并將其作為解釋變量,可以反映在各時段內每一年的年末落戶戶口數在落戶門檻指數影響下的變化程度。在計量回歸的技術處理上,根據年末落戶戶口數的連續動態變化,將落戶門檻在每年的動態變化予以度量處理,從而使計量回歸分析更有說服力。
(3)中介變量
考慮到流動人口的社會歧視感、收入困難等問題會影響流動人口犯罪行為的發生,所以為了更好地考察落戶門檻與流動人口犯罪之間的關系,本文選取2017年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問卷中流動人口對“我感覺本地人看不起外地人”的回答來衡量流動人口感受到的社會歧視程度,社會歧視感強,身份認同感低,反之亦然。1代表“完全不同意”,2表示“不同意”,3表示“基本同意”,4表示“完全同意”。
(4)控制變量
為了盡可能減少遺漏變量導致的回歸偏差,本文參考已有的研究設置了其他影響流動人口犯罪行為發生的控制變量,主要包括各省區市的地域特征、流動人口個體特征兩個維度。各省區市的地域特征包括各省區市的地區生產總值、人均地區生產總值、人口密度、各地區(東部、中部、西部、東北)的虛擬變量;流動人口個體特征包括受教育程度、民族、年齡、是否為初犯等(見表1)。

表1 變量描述
(三)模型設計
本文使用固定效應模型來估計落戶門檻對于流動人口犯罪的影響。主要估計模型如下:
crij=α1lnhuzhiij+α2REij+α3IDij+εij
(1)
被解釋變量為流動人口的犯罪率,主要解釋變量為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REij表示地域特征的控制變量,IDij表示流動人口個體特征的控制變量。
在研究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對流動人口犯罪率的影響機制時,本文主要采用中介效應模型。參考Baron對中介效應檢驗的理解[16],在研究作用機制時,選用中介效應模型進行實證分析。主要回歸模型為第(1)式、第(2)式以及第(3)式
Mechanismij=β1lnhuzhiij+β2REij+β3IDij+εij
(2)
crij=γ1lnhuzhiij+γ2Mechanismij+γ3REij+γ4IDij+εij
(3)
式(2)、(3)中,Mechanismij表示社會歧視影響流動人口犯罪率的作用機制,其他變量的定義與式(1)相同。
四、落戶門檻對流動人口犯罪率的影響
根據被解釋變量的實際情況和研究目的,采用固定效應模型檢驗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對流動人口犯罪率的影響。為了克服主要變量之間的潛在內生問題,本文主要采用替換變量法進行穩健性檢驗。
(一)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對流動人口犯罪率的基準回歸
表2呈現的是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對流動人口犯罪率的面板數據回歸結果:

表2 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對流動人口犯罪率的面板數據回歸結果
由表2可知,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對流動人口犯罪率的影響系數為-0.106 8,在5%的水平上顯著;加入地區特征控制變量后,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對流動人口犯罪率的影響系數為-0.283 1,在5%的水平上顯著;加入地區特征控制變量和流動人口個體特征控制變量后,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對流動人口犯罪率的影響系數為-0.288 2,在1%的水平上顯著;加入地區特征控制變量和流動人口個體特征后,再加入流動人口是否存在收入困難,結果顯示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對流動人口犯罪率的影響系數為-0.316 1,在1%的水平上顯著,即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對流動人口犯罪率依然起著反向作用。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越高,犯罪率越低;勞動年齡段的流動人口犯罪率較高;累犯再犯的比率低;漢族流動人口犯罪率高(跟流動人口多為漢族有關);流入地區人均生產總值越高,流動人口犯罪率越高。當流動人口存在收入困難時,犯罪的可能性會提高;沒有收入困難的流動人口數量越多,犯罪率就越低。
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的衡量會受到兩個因素的影響,即基年落戶門檻指數的大小,以及基年的新增落戶戶口數的多少。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提升時有下面幾種情況:
(1)年末落戶戶口數提升,落戶門檻指數下降;
(2)年末落戶戶口數保持不變,落戶門檻指數下降;
(3)年末落戶戶口數降低的比率低于落戶門檻指數降低的比率;
(4)年末落戶戶口數提升的比率高于落戶門檻指數提升的比率;
(5)年末落戶戶口數提升,落戶門檻指數保持不變。
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降低時有下面幾種情況:
(1)年末落戶戶口數降低,落戶門檻指數提高;
(2)年末落戶戶口數不變,落戶門檻指數提高;
(3)年末落戶戶口數提高的比率低于落戶門檻指數提高的比率;
(4)年末落戶戶口數降低的比率高于落戶門檻指數降低的比率;
(5)年末落戶戶口數降低,落戶門檻指數不變。
從數據來看,各省市落戶門檻變動的比率只出現于兩階段間隔年間,各省市落戶戶口數的變動比率和幅度都較一致,沒有出現特別異常的典型省市,故未對各種增減情況進行詳細說明。
當某一省市的落戶門檻指數提高時,年末落戶戶口數的情況為降低或者不變,即使年末落戶戶口數提高,但提高的比率低于落戶門檻指數提高的比率時,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仍降低。較低的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與較高的流動人口犯罪率呈正比。而當某一省市的落戶門檻指數降低時,年末落戶戶口數的情況為增加或者不變,即使年末落戶戶口數降低,但降低的比率低于落戶門檻指數降低的比率時,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仍提高。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提高,但年末落戶戶口數提高的比率高于落戶門檻指數提高的比率時,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仍然提高。較高的落戶戶口數與較低的流動人口犯罪率呈正比,假設1得到證實。
(二)機制分析
1.社會歧視與犯罪率的關系
表3是引入社會歧視變量后的回歸結果。

表3 加入社會歧視中介變量后的回歸結果
根據表3,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對流動人口犯罪率的影響系數為-0.106 8,在5%的水平上顯著;加入社會歧視作為中介后,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對流動人口犯罪率的影響系數為-0.427 6,在1%的水平上顯著;加入地區特征和流動人口個體特征控制變量后,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對流動人口犯罪率的影響系數為-0.352 2,在1%的水平上顯著;在已加入地區特征和流動人口個體特征控制變量后,再加入流動人口是否存在收入困難,這時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對流動人口犯罪率的影響系數為-0.367 6,在1%的水平上顯著。可見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對流動人口犯罪率起著抑制作用。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通過影響社會歧視程度而影響犯罪率,社會歧視程度高會提高流動人口犯罪率。假設2得到證實。
2.是否存在收入困難與犯罪率的關系
根據前文的結果,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與流動人口的犯罪率之間為負相關關系,流動人口社會歧視與流動人口犯罪率之間為正相關關系。當某一省市的落戶門檻較高且沒有其他促進流動人口落戶的相關政策時,此時年末新增落戶戶口數較少,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較低,較低的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對應著較高的流動人口犯罪率;當落戶門檻較低且沒有其他限制落戶的相關政策時,此時的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較高,較高的落戶戶數對應著較低的流動人口的犯罪率。在落戶門檻較高的地區,流動人口在什么情況下會選擇去犯罪?在前文表1到表3的回歸分析中加入流動人口是否存在收入困難這一控制變量后,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對流動人口犯罪率的影響系數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即流動人口存在收入困難的比例越高,流動人口的犯罪率越高。
(三)穩健性檢驗
流動人口犯罪在受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的影響之外,還可能受省市級的地理位置及城市規模等因素的影響。因此,為了驗證省市級地理位置以及城市規模因素是否會對上述結果有影響,這里使用剔除了北上廣后的其他省市級數據進行檢驗,驗證剔除北上廣典型數據后,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是否會對流動人口犯罪率起著相同的作用。剔除北上廣數據后的回歸結果見表4。

表4 剔除北上廣數據后的回歸結果
由表4可見,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對流動人口犯罪率的影響系數為-0.169 8,在1%的水平上顯著;加入地區特征控制變量后,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的影響系數為-0.619 1, 在1%的水平上顯著;加入地區特征控制變量和流動人口個體特征控制變量后,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的影響系數為-0.232 9,在1%的水平上顯著;在考慮了地區與個體特征后,加入流動人口是否存在收入困難這一變量,這時的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對流動人口犯罪率的影響系數為-0.258 0, 在1%的水平上顯著。剔除北上廣后的數據與包含北上廣的數據有著相同的作用結果。因此得出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與流動人口的犯罪率之間具有反向相關的關系。在剔除了北上廣的典型數據后,檢驗社會歧視是否依舊對流動人口犯罪率起著顯著的中介效應,詳見表5。

表5 對社會歧視中介效果的檢驗
根據表5,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對流動人口犯罪率的回歸系數為-0.138 5,在1%的水平上顯著;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對流動人口社會歧視的回歸系數為0.886 3,在1%的水平上顯著;加入了社會歧視作為中介后,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對流動人口犯罪率的回歸系數為-0.627 9,在1%的水平上顯著。可見流動人口社會歧視的中介效應在剔除了北上廣典型數據之后仍然存在。
加入地區和流動人口個體特征控制變量后,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對流動人口犯罪率的影響系數為-0.255 3,在1%的水平上顯著;社會歧視對流動人口犯罪率的影響系數為0.226 7,在5%的程度上顯著。在考慮了地區和流動人口個體特征后,再加入流動人口是否存在收入困難的變量,這時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對流動人口犯罪率的影響系數為-0.273 3,在1%的水平上顯著;流動人口收入困難對犯罪率的影響系數為-0.088 5,在1%的水平上顯著。可以發現,在剔除了北上廣典型數據后,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與流動人口的犯罪率之間的反向相關關系仍然存在,社會歧視作為中介機制對流動人口犯罪率產生影響。
五、結論與討論
本文引入社會歧視作為中介變量探究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對流動人口犯罪率的影響機制,認為流動人口落戶門檻體現了流入地的政策和對流動人口的包容程度,通過影響流動人口的社會認同感和感受到的歧視程度而影響犯罪率。流動人口落戶門檻高,指數戶數比低,會增加流動人口感受到的社會歧視程度,使流動人口增收困難,降低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犯罪的機會成本,從而提高了流動人口犯罪率。
流動人口落戶門檻指數戶數比受各省份年末落戶戶口數以及各省份在統計年的落戶門檻指數的共同作用,且各省份年末落戶戶口數一定程度上受到該省份的落戶門檻的影響。近年來各地爭奪人才日益激烈,部分城市不斷放開落戶條件,落戶門檻一方面為高知和高技術群體降低,另一方面其變化對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影響較小,落戶門檻對于他們來說仍然很高。因此在關注政策推出過程中社會層面可能發生的不平等問題的同時,也要關注到政策對于流動人口個體的影響。對于流動人口個體而言,落戶門檻的降低使其經濟收入水平、生活水平以及社交群體圈層等方面得到改善,而這些改善在一定程度上會抑制犯罪行為的產生。
如何減少因流入地與流出地之間的文化沖突而產生的社會歧視問題,提高流動人口的身份認同感,降低流動人口的犯罪率?我們認為,首先在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的過程中,應加強對失業及待業流動人口的勞動技能培訓,同時為他們提供工作信息,從而提高他們的社會勞動參與率。其次,需要進一步加大普法工作力度,通過宣傳、教育等方式提高社會成員的法律意識,樹立行為準則,從個人意識層面減少流動人口犯罪行為的發生。最后,流入地城市的社區及街道應大力促進外來流入人口的社會融入,通過積極開展文化宣傳活動以及社會互動等推進流動人口與當地居民之間的溝通合作,減少對流動人口的社會歧視,預防和減少流動人口犯罪行為的發生,維護社會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