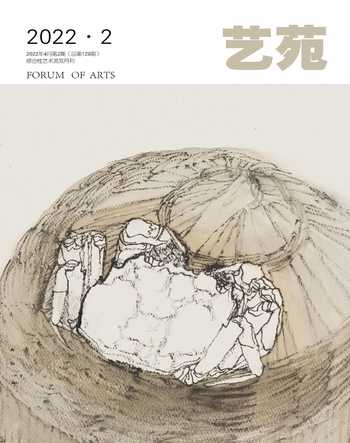諜戰(zhàn)劇中的“雙重文本”與“角色-觀眾”間的隱性置換
周粟
摘 要: 借用約翰·費斯克的受眾主體性理論分析,在以《潛伏》為代表的經(jīng)典國產(chǎn)諜戰(zhàn)劇中,存在著一對相互對立的“雙重文本”:觀眾在表層意識文本中解讀出了“信仰”,同時在深層無意識“潛文本”中解讀出了當下自身的現(xiàn)實生活困境與內(nèi)心渴望,這種內(nèi)心渴望轉(zhuǎn)而在諜戰(zhàn)劇中獲得替代性滿足。這種于潛文本層面的“隱性置換”,存在著一種心理學上的轉(zhuǎn)化公式,即無論觀眾在諜戰(zhàn)劇的“顯性文本”中解讀出了“信仰”“理想”還是其他的“上層建筑”,他們在“潛文本”層面永遠會不自覺地解讀出更深一層的“渴望”,這兩種極端的轉(zhuǎn)化公式取決于一個變量,即觀眾在潛文本中看到的對象是弱者還是強者。對經(jīng)典諜戰(zhàn)劇文本特征和題材特性層面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挖掘當年“現(xiàn)象級”諜戰(zhàn)劇引發(fā)收視熱潮的深層原因,進而對當下國產(chǎn)電視劇的創(chuàng)作與研究產(chǎn)生啟迪。
關鍵詞:電視劇;諜戰(zhàn)劇;《潛伏》;約翰·費斯克;屏幕理論
中圖分類號:J90 文獻標識碼:A
諜戰(zhàn)題材電視劇,主要指以間諜活動為表現(xiàn)主題,以極強懸念、較快節(jié)奏和嚴密邏輯為主要創(chuàng)作特征的電視劇類型。諜戰(zhàn)電視劇的題材優(yōu)勢,決定了其既不同于家庭倫理劇中充分貼近觀眾熟悉場景的現(xiàn)實性,也不同于古裝武俠片中徹底遠離觀眾認知范疇的奇觀感,也即優(yōu)秀的諜戰(zhàn)題材電視劇創(chuàng)作者,往往能在電視文本生產(chǎn)者和觀看者之間建立一種符合觀看主體產(chǎn)生意義的“適當場所”[1],進而通過諜戰(zhàn)劇特有的“腦力游戲”特質(zhì)征服觀眾,使他們在產(chǎn)生“智商提升”的象征性快感后,形成對劇集中沉著冷靜智力超群的魅力角色的高度崇拜,進而獲得由諜戰(zhàn)敘事這一“高級思維游戲”引發(fā)的特殊審美意趣。
本文選擇考察諜戰(zhàn)劇《潛伏》,主要考慮到其在觀眾中的特殊影響力。從受眾角度看,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諜戰(zhàn)題材電視劇呈現(xiàn)出廣泛的傳播趨勢;而在傳播效果研究中,對于觀眾的受眾研究不失為一種獨特的研究視角。以下試圖批判性地從約翰·費斯克的觀眾主體性理論角度切入,分析以《潛伏》為代表的21世紀國產(chǎn)諜戰(zhàn)題材電視劇受眾心理、身份價值等觀眾主體性因素及其效果,進而考察觀眾在讀解過程中如何創(chuàng)造意義并建構自身價值,剖析《潛伏》文本在受眾傳播中的內(nèi)在驅(qū)動力,從而為理解21世紀中國諜戰(zhàn)劇的社會影響力狀況提供一種解答。
一、費斯克的電視受眾主體性理論特征
以約翰·費斯克的電視屏幕理論看,觀眾在觀看情節(jié)緊張、故事離奇的電視劇時,往往會獲得隔絕于家庭之外而又保留家庭主體性的“生活在別處”的審美快感。觀眾于熟悉的家庭環(huán)境中,邊忙手頭事邊對屏幕內(nèi)諜戰(zhàn)劇驚險情節(jié)的隨眼“一瞥”,可能就決定了電視文本與觀看者之間恰當“共謀”關系的瞬間生成。回顧21世紀的頭十年,國產(chǎn)諜戰(zhàn)題材電視劇的播映熱度曾一直居高不下。這其中,《潛伏》作為當年“霸屏”的諜戰(zhàn)經(jīng)典,時至今日仍“潛伏”在眾多諜戰(zhàn)迷的作品排行榜之中。探討諜戰(zhàn)劇《潛伏》中的受眾主體性特征,首先需要就電視主體性理論做出必要的特征辨析。
在斯圖爾特·霍爾與大衛(wèi)·莫雷的研究基礎上,約翰·費斯克重點提出了觀眾主體性的概念,其通過對電視文化的研究方式進行分析,亮明自身的觀點:電視觀眾是具有積極性的意義生產(chǎn)者。綜合來看,費斯克對于電視受眾的主體性理論,重點貢獻在于以下兩點:
首先,費斯克是在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基礎上,明確觀眾主動性地位的電視研究開拓者。費斯克強調(diào)受眾“積極”地構建與電視文本之間的關系,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具備建構自身意義的自主權力。費斯克對于受眾主動性的重視,是對之前電視研究理論中過于強調(diào)文本力量的重要回應。
其次,費斯克指出電視受眾獲得快樂的深層原因。相比之前的電視研究理論,費斯克關于電視受眾如何理解電視文本,以及如何從中獲得樂趣的觀點十分新穎。費斯克指出,觀眾對電視文本的解讀立場,來自于電視文本的意識形態(tài)代碼,以及這些文本代碼傳遞給觀眾所形成的電視代碼。當觀眾所運用的解碼方式與電視文本編碼者所持的意識形態(tài)相符,受眾立場就容易倒向電視文本的常規(guī)道德立場。
費斯克指出,以電視文本的多義性也即意義的多樣性為根基,電視受眾在觀看電視過程中具有“生產(chǎn)”出多樣性的潛在意義的可能性,而這種被生產(chǎn)出的“可以實際體驗的意義”[1],也依托于不同觀眾主體的社會特征。綜合來看,費斯克的觀眾主體性理論對于挖掘電視劇受眾的主體性特征、展現(xiàn)電視劇文本輸出的“意義”具有很強的理論指導作用。
同時,需要注意的是,正如凱爾納對于費斯克的批判所指出的那樣,費斯克的理論具有“膜拜受眾”和“膜拜抵制”的傾向,這導致其在文本研究中漏掉了諸如社會體制、文化生產(chǎn)語境、政治體系等影響因子,從而這種過于強調(diào)接受者的受眾理論,難免具有形成“新教條主義”[2]的傾向。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后文將力求避免費斯克主體性理論中“唯受眾是舉”的立場,兼顧諜戰(zhàn)劇《潛伏》受眾的同時,客觀論述電視劇文本生產(chǎn)者的作用與地位。具體來看,后文將沿承費斯克在《電視文化》中對于“心理分析與主體”的論述方式。[1]費斯克在“心理分析與主體”部分的論述具體方式是,既承認體驗電視文本的主體是多種社會主體(而非單一接受者的心理分析主體),又指出電視文本建構了這些主體。他在論述心理分析與主體的關系時強調(diào)家庭中的電視觀眾是社會化之后的產(chǎn)物,因而需要獲得由“社會轉(zhuǎn)化而來”的一種主體理論。[1]以下將嘗試將電視受眾主體性理論與以《潛伏》為個案的諜戰(zhàn)劇分析進行內(nèi)在結(jié)合。
二、從主體性角度看《潛伏》受眾的五點特征
在統(tǒng)計當年《潛伏》的諸多受眾反饋數(shù)據(jù)時,筆者不禁產(chǎn)生這樣的疑問,為何當時數(shù)量眾多的劇迷,似乎普遍對于《潛伏》中的反面角色關注度高于正面角色?為何當時網(wǎng)絡上形成了眾多針對四位反派角色吳站長、李涯、陸橋山、謝若林的“二創(chuàng)作品”?為什么不是余則成所代表的象征崇高信仰的正面英雄人物,反而是吳站長所代表的反面人物贏得了相對更高的關注度?或許,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有助于深入叩探21世紀頭十年諜戰(zhàn)劇收視火爆的深層社會心理緣由。
通過應用受眾主體性理論對《潛伏》受眾進行初步分析,本文大體可以得出以下五方面思考:其一,受眾特別是《潛伏》的年輕觀眾,對于傳統(tǒng)意義上“男性氣概”包含的“信仰”“堅韌”等精神力量充滿期待;其二,具備“迷”特質(zhì)的觀眾會對劇中所迷戀的角色產(chǎn)生二度“創(chuàng)作”的沖動,體現(xiàn)出麥特·西爾斯所述“創(chuàng)造性自我表達”的粉絲特性;其三,觀眾會通過辨認電視文本中自身“熟悉”的話語,感受到《潛伏》對于自己的話語“尊重”,進而獲得影像文本的解讀快感;其四,在觀看《潛伏》時,受眾通過“權力”“信仰”等內(nèi)在符碼與社會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協(xié)商與碰撞過程,獲得身份的彰顯與意義的“再生產(chǎn)”成果;其五,《潛伏》所特有的壓抑情感,與中國人傳承下來的壓抑記憶產(chǎn)生了“共謀”,“壓抑”成為獲得了觀眾同感的《潛伏》成功秘訣之一,也即《潛伏》中特有的劇場式的安靜基調(diào)氛圍,與諜戰(zhàn)環(huán)節(jié)緊張刺激的敘事節(jié)奏反差,使得費斯克所述的“快樂”源泉得以產(chǎn)生。諜戰(zhàn)劇電視觀眾的快感,就來自于這一反差張力達成統(tǒng)一的程度和情節(jié)彌合熒屏內(nèi)外思維鴻溝的力度。正如費斯克理論指出的那樣,電視觀眾通過辨認出他們熟悉的內(nèi)容,在電視文本的解讀中獲得了文本“尊重”他們的熟悉“話語”,由此獲得了快感,并獲得了繼續(xù)積極創(chuàng)造自身社會經(jīng)驗以及“再生產(chǎn)”“再編碼”的動力源泉。
例如,在相關學者所論述的“泛俗化”卡里斯馬幻象這一概念中,吳站長這一角色形象,很大程度上充當了現(xiàn)實社會話語體系中觀眾眼中的“卡里斯馬”幻象。在如今男性特征式微的社會現(xiàn)象下,吳站長、李涯、余則成這樣具備男性魅力、權威感、神秘感以及已有或者具備潛在權力屬性的角色,成為觀眾對于傳統(tǒng)男性形象呼喚的復歸。
三、《潛伏》中“潛伏”的“雙重文本”
不妨這樣來看,《潛伏》好比是一部包含“雙重文本”的電視劇文本:它的表層意識文本的主旨在于“信仰至上”,這以余則成為突出代表;其深層無意識文本的主旨在于“活著至上”,這以吳站長為代表。“信仰至上”,要求為崇高信仰而敢于犧牲一切;而“活著至上”,則相反要求為活下去而可以犧牲道德、義務、責任、承諾及信仰等。如果這種假定是有合理性的,那么可以看到,觀眾在收看這部諜戰(zhàn)劇的過程中,已經(jīng)身不由己地投射進自己的意識和無意識心理:在意識層面,他們可以為余則成等人物的崇高的犧牲精神而深深感動;而在深層無意識層面,他們則會不知不覺地為吳站長等人的生存行為及其法則而深切地投入。而這種深層無意識心理頗為耐人尋味:觀眾已經(jīng)于不知不覺中將自身的現(xiàn)實生活情境投射進電視劇的角色中,并且完成了一次銀幕與現(xiàn)實之間角色的隱性“審美置換”[3]。
進一步看,《潛伏》的影像文本層面,實際上存在著一對相互對立的“雙重文本”(也即“雙重本文”),正如有學者所述,“雙重文本”不僅可以作為“一切本文共有的特性,也可以被視為文化的一種修辭術……文本總是由意識文本(表層結(jié)構)和無意識潛文本(深層結(jié)構)組成的”[3]。觀眾在諜戰(zhàn)劇《潛伏》的表層意識文本中解讀出了“信仰”,又同時在其深層無意識“潛文本”中解讀出了自身的當下現(xiàn)實生活困境與內(nèi)心渴望,這種內(nèi)心渴望轉(zhuǎn)而在《潛伏》中得到替代性滿足。雙重文本之間具有一種張力結(jié)構,可以令觀眾產(chǎn)生“信仰至上”還是 “活著至上”的選擇困境。對于《潛伏》來說,上述雙重文本之間是結(jié)合得如此緊密而又融洽,以致觀眾常常會忘記掉兩者之間可能存在的這種緊張關系。這部諜戰(zhàn)劇的美學成功就在于,它巧妙地讓上述雙重文本融合于敘事結(jié)構的多義性構造之中,讓觀眾游刃有余地在其中投入地觀看,既可以投射進崇高的理想主義信念,也可以投射進現(xiàn)實的享樂主義情懷。
四、“雙重文本”背后的“隱性置換”
更進一步,在觀眾的無意識潛文本層面,也存在著兩種渴望。正如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所述,“最低層次的生理需求”與“最高層次的自我實現(xiàn)”需求分別代表這兩種渴望的兩極:一極為意欲“取代對方”成就自身欲望的“最低需求”,另一極為“同情對方”幫助他人崛起的“崇高道德”。[4]兩者相互轉(zhuǎn)化,互為因果。例如,反面人物中,觀眾普遍對于吳站長的關注度很高,這體現(xiàn)出觀眾在無意識潛文本層面,為“活下去”而寧愿放棄道德、承諾與歸屬感的“本我”式渴望:觀眾在潛意識中渴望“代替”吳站長進而“化身”吳站長,他們在觀看《潛伏》時下意識地將自身生活情境中的困苦與無奈的身份,與熒屏中深諳生存之道的吳站長形象進行了對調(diào),完成了潛文本層面的隱性“審美置換”;與此同時,觀眾在潛文本中也飽含著“同情弱者”的“超我”式“崇高道德”,根據(jù)相關調(diào)查可知,不同性別觀眾對《潛伏》中女性角色晚秋呈現(xiàn)完全相反的態(tài)度,男觀眾最喜歡的女性角色就是“晚秋”,而女觀眾最討厭的女性角色恰好也是“晚秋”。
具體分析,在潛意識層面,男性眼中的晚秋是絕對的弱者,他們面對熒屏中晚秋這一類型角色激發(fā)出潛意識中強烈的同情心與保護欲,渴望成為她的寬厚的肩膀,因此,男性觀眾在解讀《潛伏》的潛文本層面,實際已與劇中那些配得上晚秋的強悍男人完成了身份對調(diào),形成了“隱性置換”。而溫柔的晚秋在女性觀眾眼中,則被下意識歸為可憎的競爭對手,她們眼中的晚秋是具備“溫柔”這一女性殺手锏的“強者”,因此女性觀眾內(nèi)心那份“本我”層面的“不擇手段”被強烈激發(fā),“馬斯洛最低需求”中最原始的“情欲”需求開始肆意生發(fā)。在潛意識中,女性觀眾更喜愛對自身不具有威脅感的“傻大姐”翠平,她們在觀看并“解碼”《潛伏》的過程中,實際上已經(jīng)完成了與傻大姐翠平角色的“隱性置換”,因為在潛文本中她們渴望打敗翠平的情敵“晚秋”,為“情欲”需求這一馬斯洛理論中的最低層次需求去不斷奉獻自己的“本我”本能。
《潛伏》提供的這種觀眾在潛文本層面的“隱性置換”,實際上存在著一種心理學上的轉(zhuǎn)化公式,即無論觀眾在諜戰(zhàn)劇的“顯性文本”中解讀出了“信仰”“理想”還是其他的“上層建筑”,他們在“潛文本”層面永遠會不自覺地解讀出更深一層的“渴望”,并且如上文所述,這種渴望包含著兩個極端,即對“超我”般高尚道德的追尋以及對“本我”式“活下去”本能的訴求。這兩種極端的轉(zhuǎn)化公式取決于一個變量,即觀眾在潛文本中看到的對象是弱者還是強者。
總體而言,正因“當代影視媒介覆蓋面廣、信息傳遞快捷、生動多維,它是以具體直觀的感性情態(tài)進入千家萬戶的”[5],所以《潛伏》為代表的21世紀諜戰(zhàn)劇,在恰到好處地滿足了觀眾對于潛文本層面上的心理補償?shù)耐瑫r,也更加提升了21世紀頭十年,電視劇對當下電視劇創(chuàng)作理念與發(fā)展實踐的“經(jīng)驗反哺”。
五、經(jīng)典諜戰(zhàn)劇對當下創(chuàng)作的啟發(fā)
綜合來看,國產(chǎn)諜戰(zhàn)題材電影已經(jīng)取得豐碩的成績,比如《風聲》《秋喜》《東風雨》《聽風者》,以及《觸不可及》《密戰(zhàn)》《懸崖之上》《蘭心大劇院》等,在電影題材類型表現(xiàn)上得到觀眾的喜愛。相比而言,盡管國產(chǎn)諜戰(zhàn)電視劇的發(fā)展時間不如諜戰(zhàn)電影那么長,但近年來諜戰(zhàn)電視劇也形成了諸多優(yōu)質(zhì)的內(nèi)容呈現(xiàn),滿足了大眾的內(nèi)在文化與心理需求,且不時會出現(xiàn)“爆款”諜戰(zhàn)劇。
例如,近期播映的《對手》別出心裁、 跨越時空與《潛伏》形成了模式與結(jié)構上的相得益彰。《潛伏》描述的是我黨潛伏人員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的諜戰(zhàn),而《對手》表現(xiàn)的是敵特長期潛伏于我們和平建設時期的間諜活動。作為國民黨間諜,《對手》中的主角生活看似司空見慣,其內(nèi)里卻“潛伏”著跌宕起伏的豐富的身份挪移和情感變遷,也許這種呈現(xiàn)正反角色間“隱性置換”的新形態(tài)也是吸引當下受眾的重要因素。
因此,對經(jīng)典諜戰(zhàn)劇進行文本特征和題材特性層面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挖掘當年“現(xiàn)象級”諜戰(zhàn)劇引發(fā)收視熱潮的深層原因,進而對當下國產(chǎn)電視劇的創(chuàng)作與研究產(chǎn)生新的啟迪。如何敏銳把握和利用好這一觀眾解讀中的“隱性置換”公式,使其為電視劇的創(chuàng)作者所用, 這正是以《潛伏》為代表的21世紀早期優(yōu)秀諜戰(zhàn)劇作品群帶給當下電視劇創(chuàng)作者的重要啟示。
參考文獻:
[1]約翰·費斯克.電視文化[M].祁阿紅,張鯤,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2]陸道夫.文本·受眾·體驗——約翰·菲斯克媒介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郵電大學出版社,2008.
[3]王一川.中國現(xiàn)代卡里斯馬典型[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4]馬斯洛.動機與人格[M].許金聲,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
[5]周安華.詢喚當代影視批評的價值感和美學蘊含[N].中國藝術報,2021-09-08.
(責任編輯:萬書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