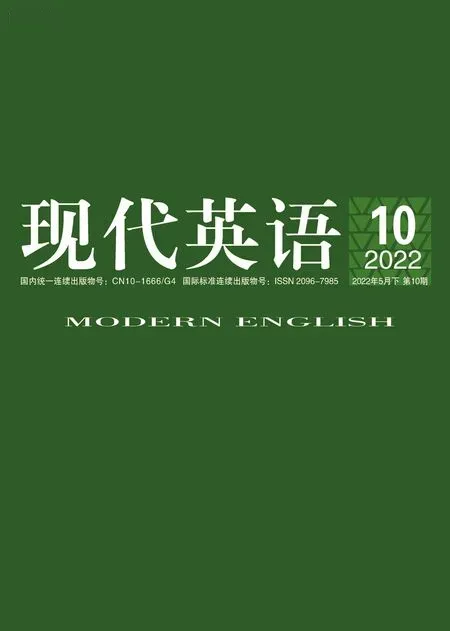5E模式在高校英語聽力課堂教學中的應用研究
郭 杰
(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外國語學院,河南 鄭州 450046)
一、引言
“5E”模式是由美國生物學研究會提出的一種教學程序,因其包含五個環節,且每個環節均以字母E開頭:引入(engagement)、探究(exploration)、解釋(explanation)、遷移(elaboration)和評價(evaluation),所以稱為“5E”模式。[1]這種探究式教學模式最初在生物課程設計中應用,它描述了一種能用于具體學科課程或某一節課的教學程序。
高校英語聽力課程目標主要是培養學生對不同聽力材料的理解能力,幫助學生掌握針對不同材料的聽力理解所需要的聽力技巧和方法。通過理論和實踐教學,提高學生聽力的綜合概括能力、細節分析能力和跨文化交際能力。傳統的英語聽力課堂教學重講授,輕實踐;重做題練習,輕能力培養。學生在課堂上的學習興趣不高,主動學習意識薄弱,學習效果不高。文章把“5E”教學模式引入英語聽力的課堂教學,改革該課程的課堂教學程序和模式,以求激發學生主動學習的積極性,提高課堂教學效果,提升學生英語聽力綜合能力。
二、“5E”模式的基本內涵
“引入”環節是該模式的開始階段。為吸引學生對學習任務產生興趣,該模式強調通過創設問題情境來激發學生的學習積極性。[2]這里的問題情境應盡量與現實生活(特別是學生的生活)聯系起來,并與課程內容和教學任務聯系起來。[3]
“探究”環節是該模式的中心環節。教師可根據上一環節產生的認知沖突,引導學生進行探究。在探究過程中,學生是主體,教師的作用是引導和幫助。在這一階段,教師需要向學生提供一些必需的背景知識,教師所采取的是“支架式”的幫助模式。[4]
準確稱量50 g各干燥模式下最終毛葉山桐子,放入小型榨油機進行壓榨,收集毛油,測定各組中毛葉山桐子果實榨取的毛油質量,重復3次,按照公式(4)計算出油率,并進行對比。
在圖2中比較了ESD和MSD的計算復雜度與Rx-SD,Tx-SD的計算復雜度.圖中的復雜度定義為Cre(%)=100×(CML-CSD)/CML[9],表示SD相對于ML檢測減小的相關復雜度.圖2(a)中可以看出,在相同的頻譜效率(頻譜效率為6 bps/Hz)下,Nt>Nr時,改進算法比ML檢測和經典的SD檢測具有更低的計算復雜度,尤其是在信噪比較低的情況下優勢更加明顯,在信噪比為3dB時,ESD和MSD的相對復雜度降低了33%.圖2(b)中,Nt≤Nr時,與Tx-SD進行比較,MSD的相關復雜度降低了20%以上.此外,在相同條件下ESD與MSD相比,ESD能夠降低約2%的相關復雜度.
英語聽力課程是外國語言文學類專業、英語、翻譯專業的基礎課,是這些專業的人才培養方案目標達成的重要支撐課程,一般在大學一年級和二年級本科生中開設,是提升英語五項基本技能之一“聽”的能力的必修課程。
對于傳統的冗余保護,常采用故障發生后冗余設備啟動并進行自動切換。為保護電網供電安全,DNV規范要求DP-ER電力系統的的冗余發電機應處于熱備機的保護模式(Standby Start and Changeover)。當電力系統正常工作時,電網會根據負荷的大小自動分配在網發電機組臺數,滿足功率匹配。當電力系統發生故障導致在網發電機不能正常工作時,冗余發電機組能夠快速切換入網,使故障對電網的沖擊降到最低,滿足失電保護功能。同時,當系統執行完失電保護功能后,系統的冗余組件仍應滿足n+1和n-1原則。
“評價”階段是“5E”模式的最后一步,旨在強調教師和學生用正式或非正式的方法,評價學生對新知識的理解及應用能力。教師可以采用紙筆測驗或通過觀察學生表現,給出客觀全面的評價和建議。
“解釋”階段是“5E”教學模式的關鍵環節。這一階段應將學生的注意力集中在對探究過程和結果的展示及分析方面,學生陳述對概念的理解,技能的掌握和方法的運用。[5]教師在此階段可以借助于課程目標來幫助學生更加深入地理解新知識。
三、高校英語聽力課程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遷移”環節又叫“拓展”環節。在該環節中,教師引導學生繼續對概念進行深入理解和應用,擴充概念的內涵與外延,用新的概念或技能解釋新的情境或新的問題。[6]通過遷移或者拓展訓練和實踐,學生逐步強化和內化新概念或技能。
雖然英語聽力課堂教學改革已經做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弊端或問題依然存在:課堂上還是做練習—對答案—看文本—聽材料的單一教學模式;課堂教學上仍然以教師講授為主,學生被動接受聽力訓練;學生的課堂活動參與度不高,存在感不強;課堂教學氣氛沉悶,學生主動學習的熱情不高;課程評價模式單一,過程性評價體現不明顯,未能全面客觀評價學生的學習效果等。
結合城市自然生態結構與城市發展進程中的問題進行綠道規劃是發揮綠道生態保護功能的重要前提。臨安地處杭州西部,城市境內三面環山,境內有青山湖和苕溪等五大水系,是典型的浙北山區城市,具有特殊的城市自然生態基底。
(1)從全球高程異常模型(EGM96 、OSU91A模型)中查取,也可以從國家高程異常值圖上得到,這兩種方式的精度通常在分米到米級之間,遠遠不能滿足實際生產的需要。(2)從地區似大地水準面精化模型中得到,河北省似大地水準面精化分辨率為2.5′×2.5′,城市、平原地區的精度能達到±5.0 cm以內,山區、高山區的精度能達到±15.0 cm以內。
目前英語聽力課程的教學方法以交際式教學法和合作式學習為主,通過教師課堂上播放英語音視頻材料,學生完成教材設計的任務。檢查方式以回答教材上的問題為主,輔以學生小組討論指定話題,交流并形成小組意見和觀點,進行課堂展示。教學內容依賴于教材,受限于教材,其難易程度無法改變,課外補充材料有限;課程評價仍以終結性評價為主,忽略了過程性評價。
四、“5E”模式下英語聽力課程的教學程序
“探索”環節是“5E”模式的核心環節之一。在此環節,教師主要向學生布置學習任務,提出任務完成形式和要求,必要時給學生提供完成學習任務的背景知識等。學生在本環節占據主導作用,探索教師布置任務的完成方式。在播放音頻之前教師提出聽力要求,思考“概括新聞主旨大意”這一任務如何完成。
(一)“引入”環節
該環節是實現課程教學目標關鍵的一步,也是整個“5E”模式教學環中核心環節,因為該環節是學生探究結果的呈現階段,是學生接受新概念和新技能的環節,同時也是教師給予學生探究結果是否正確或合理的評判時機。

表1 “引入”環節教學程序
這則新聞報道了亞馬遜在公司原有業務基礎上又拓展了新的業務:快遞配送。學生在思考教師所提出的問題“亞馬遜公司是什么公司?”時,教師聽完學生的答案反問“事實真如此嗎”。學生的好奇心很容易被激發,因為學生很難想象到亞馬遜公司如新聞介紹的是一家“科技公司,網絡出售商品只是它的業務之一”。這就會產生“信息差”,與原有認識“亞馬遜是一家出售圖書為主的公司”產生認知沖突,這樣更容易對接下來的聽力內容產生興趣。
(二)“探索”環節
“5E”教學模式強調了在該學習環中五個階段的連貫性、統一性和持續性。因此,文章以英語聽力課程中“培養學生聽力概況能力”為教學目標,以“英語新聞概括大意”為教學案例,以VOA慢速新聞2019年5月14日的“Amazon Pays Employees to Start Businesses”[7](原新聞內容見參考文獻所附的網址)為教學素材,具體闡釋“5E”模式在英語聽力課堂教學中的實踐與應用。

表2 “探索”環節教學程序
以上述新聞素材為例,在該環節,學生主要任務是總結概括新聞主旨。學生需獨立思考或小組討論以下問題:“英語新聞主旨大意概括時應包含哪些方面?”依據已有的知識和概念儲備,把亞馬遜公司新的業務拓展“快遞配送”這一要點信息抓住,補充相關支撐信息,形成初步的答案。在這一探究過程中,給學生造成困難的應該是新聞中出現的一些關鍵詞或術語表達,例如“delivering Amazon packages(配送亞馬遜包裹)”“launched the program(項目啟動)”等,這時教師給予解釋,協助學生完成探究過程。
(ⅱ) f=ξη。即證對任意x∈X,f(x)=ξη(x)=ξ({x}-)。由Y為T0空間,只需證clY{f(x)}=clY{ξ({x}-)}。注意到clY{ξ({x}-)}=clYf({x}-)。又只需證clY{f(x)}=clYf({x}-)即可。
(三)“解釋”環節
在“5E”模式的初始環節,教學設計的關鍵是創設與學習任務相關的問題情境,幫助學生了解背景知識,學習要求和任務完成形式,最關鍵的是讓學生在頭腦中建立“信息差”,以激發學生的興趣和好奇感,將學生“引入”新技能或新概念的學習情境中去。以上述新聞素材為例,在該環節,教師和學生分別有不同的行為和作用,具體如下:

表3 “解釋”環節教學程序
在“解釋”環節,教師需要一定的邏輯方式講解“新聞主旨大意概況”的方法,并給出充分原因。例如,教師可以用“who, what, why, when, where,how”這六個詞作為提綱,為學生解釋新聞主旨大意的概況方法和技巧。雖然這一環節教師需要耗用一定時間給學生講解新技能,但是學生的陳述和解釋仍然占主導地位。在學生“解釋”新技能或概念的過程中,教師應該給以及時的糾正和補充。
(四)“遷移”環節
本環節又可以理解為“拓展”環節,是前一階段的升華。在此環節,學生需要把前三個階段所獲得的新概念或新技能投入新的情境中加以驗證,拓展學生認知范圍,加深新概念和新技能的理解與內化,做到學以致用,舉一反三。

表4 “遷移”環節教學程序
在知識“遷移”或“拓展”階段,教師根據學生所掌握新技能的情況,選擇一篇在速度、長度和難度跟前一篇新聞相似的新聞報道,布置同樣任務。鼓勵學生把新學的六要素法運用在新的聽力任務訓練中,以此來驗證該方法的合理性。
(五)“評價”環節
“評價”環節為“5E”教學模式的結束環節。這一環節主要目的在于采用多種評價方法,對教師教學效果和學生學習成效開展評估。該環節的評價模式既可以是正式的考試或隨堂測驗,又可是非正式的口頭點評。

表5 “評價”環節教學程序
針對“新聞主旨大意概括能力”的培養,評價可以發生在“5E”模式的任何一個階段,評價方式也不局限于一種。例如,在“引入”階段,教師可以評價學生對“亞馬遜公司的了解”以及“新聞主旨概括”的方法熟知程度;在“探究”階段可以觀察學生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表現等。這一評價環節,不僅可以檢測學生學習新技能的情況,也可以為教師提供教學反饋,更好地設計教學任務和活動。
五、結語
在英語聽力課程教學中,以“5E”教學模式為指導,通過教師引導、學生自主探究、解釋、驗證和評價等環節,幫助學生實現了英語聽力技能的理解、掌握、內化與實踐,激發了學生學習興趣和主動性,鍛煉了學生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由于“5E”教學模式誕生于自然學科領域的課程教學實踐,而在人文學科領域的教學實踐研究較少,可借鑒的經驗有限,因此文章的研究成果是否能在人文學科領域其他課程教學中推廣和應用還有待進一步研究和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