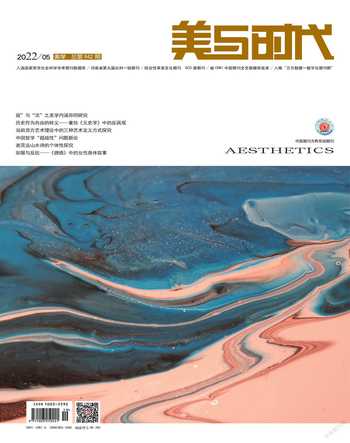黃庭堅題畫詩畫論觀初探
摘 ?要:黃庭堅題畫詩數量多,內涵豐富,現存題畫詩約有一百九十余首,涉及畫科包括道釋、人物、龍魚、山水、畜獸、花木、墨竹、果蔬等。這些題畫詩體現了他獨特的論畫觀點。在創作理論方面主張師法造化,輕傳移模寫;提倡形神兼備,重視氣韻生動。在品評鑒賞方面,推崇以“禪”論畫;重視畫家所畫之物妙然相成與靈機天賦、人品結合。這些觀點與他的交友、仕途經歷以及儒道禪融合下的處事態度有密切關系。黃庭堅的畫論觀產生于北宋文人畫思潮這一大背景下,對北宋及后世的文人畫、禪畫的創作和鑒賞產生了積極影響。
關鍵詞:黃庭堅;題畫詩;畫論觀
清代喬億說:“題畫詩三唐間見,入宋寢多。”由此可見,宋代題畫詩十分繁榮。黃庭堅是宋代題畫詩發展的集大成者,他創作的題畫詩數量繁多,且題畫畫科豐富,其中一部分包含著對繪畫藝術創作理論和品評鑒賞的獨特審美傾向。從中可以窺探宋代繪畫的美學思想的趨向,了解北宋文人畫家參與繪畫的新的審美趣味。當前學術界對于黃庭堅題畫詩多從詩學、書學、文學、美學思想及藝術價值和文藝批評理論等幾個方面進行研究,因此對于山谷獨特的論畫思想及品評觀念有必要做深入研究。
黃庭堅一生創作了一百九十余首題畫詩,其內容豐富,涉及到了多種畫科,筆者進行整理,具體內容詳見表1。
此表將黃庭堅題畫分為十種畫科,其中題詠墨竹詩的就有二十七首,由此可見此時墨竹已從花鳥畫科中分離出來,山水畫也日趨成熟,其創作也符合北宋繪畫發展的整體趨向。黃庭堅有極高的藝術素養,雖無流傳的繪畫作品,但他的論畫與鑒賞觀確為精到。南宋鄧椿在《畫繼》中對山谷評價頗高:“予嘗取唐宋兩朝名臣集,凡圖畫紀詠,考究無遺,故于群公略能察其鑒別,獨山谷最為精嚴。”[1]一語道出黃庭堅具有極高的品評鑒賞水平。
一、創作理論
黃庭堅題畫詩內容豐富、題材廣泛,對繪畫的創作得失深得體會,所以他的題畫詩許多著眼于創作理論。
(一)尚師法造化,輕傳移模寫
元符二年(1099),此時的黃庭堅接連被貶,但其心境趨于好轉,直面現實,無所畏懼。山谷在戎州遇到黃斌老,此人為著名畫家文同之內侄,善畫墨竹。山谷常與之唱和,并借斌老所畫墨竹抒發其內心之感慨,胸中之郁懣借此橫竹發而抒之[2]。正是此年,他的題畫詩創作數量達到了一個高峰,表達對畫作筆法和風格的思考,也透露出他對于貶謫生活的思考。《次韻謝黃斌老送墨竹十二韻》中云:“古今作生竹,能者未十輩。吳生勒枝葉,筌寀遠不逮。江南鐵鉤鎖,最許誠懸會。燕公灑墨成,落落與時背。譬如刳心松,中有歲寒在。湖州三百年,筆與前哲配。”[3]11397“有來竹四幅,冬夏生變態。預知更入神,後出遂無對。”[3]11381黃庭堅指出古往今來繪竹者屈指可數,吳道子擅長繪竹葉,而黃居寀遠不如他;南唐后主李煜世傳江南李主,其作竹極擅長“鐵鉤鎖”畫法,自言惟柳公權有此筆法;燕肅作竹揮毫灑墨而成,“磊落不凡,畫風與時相背”。此后間三百年唯有文同所畫墨竹可以與前輩相比。文同用鐵劃銀鉤的筆法畫竹,雖然不被世俗審美所接受,但其畫作卻展示出蒼茫的氣勢。黃斌老畫竹師法文同卻又有所超越,四幅墨竹圖繪分為春夏秋冬,形態多變。黃庭堅在品鑒畫家時推崇對于客觀對象的描繪,強調師法造化的正確性。正如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對于燕肅的記載:“澄懷味象,應會感神,蹈摩詰之遐蹤,追咸熙之懿范。”[4]112
黃庭堅對黃子舟所畫墨竹極為稱贊,鄧椿《畫繼》中載:“山谷以其尚氣,故取二器以規之,自后折節遂為粹君子,舉八行終朝郎郡倅,山谷用贈斌老韻謝子舟為余作風雨竹兩篇,誰言湖州沒筆力,今尚在而與可每言所作不及子舟。”“摩拂造化爐,經營鬼神會”,道出山谷對于師造化的重視。以此為法方可“意出筆墨外”,也道出山谷推崇畫家不僅要有精湛的筆法,更應有像松竹一樣不懼歲寒,擁有堅毅的品格。
在師法造化的理論導向中,山谷進一步強調既要師法前人,更要變法。《和子瞻戲書伯時畫好頭赤》中云:“李侯畫骨不畫肉,下筆生馬如破竹,生字下得最妙,胸有全馬故由筆端而生初非想象描模也。”可見李公麟畫馬師法前人而又能變法,他主張“領略古法生新奇”。金代詩論家元好問在《奚官牧馬圖息軒畫》云:“曹韓畫樣出中秘,燕市死骨空千金。息軒筆底真龍出,凡馬一空無古今。”[5]曹霸、韓干是唐代宮廷馬畫家,其畫作被后代皇室所收藏,后被歷代宮廷御馬畫家所臨摹。但在元好問看來,傳移模寫曹霸、韓干的畫是完全缺乏生機的,不復師法的價值。而元代畫家楊邦基以真馬為描摹的對象,對于畫面上的馬僅僅只是借鑒,并非臨摹,因此其所畫馬匹動勢逼真,具有如真龍一般的氣勢。
(二)形神兼備,氣韻生動
東晉顧愷之提倡“以形寫神”,這里的“形”為外象、“神”為內涵。“形”與“神”是相互依存,對立統一的關系,二者缺一不可。黃庭堅的論畫觀及其論畫詩也體現了這一審美思想。題畫詩《題徐巨魚》中云:“徐生作魚,庖中物耳。雖復妙于形似,亦何所賞,但令饞獠生涎耳。”[3]11300山谷認為,徐生所畫之魚取材于供人食用的魚,雖然形象逼真,但卻沒有真正的意味。觀賞者很難從中獲得審美享受以及與畫家的共鳴,最多是引起食欲,因此只是形似而非神似。如若不拘于“形似”,充分發揮自己的想象,則可獲得世俗之畫所難以取得的審美效果。通過遷想而達到主觀體的統一,才能妙得到對象的形神氣質,繼而寄情于思。
然而,形神兼備并不是繪畫的高境界,黃庭堅承主前人以“韻”論畫之說。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中說:“人品既已高矣,氣韻不得不高;氣韻既已高矣,生動不得不至。”[4]234“氣韻生動”是中國畫學上的重要原則,歷代畫論家都認為其為“六法”中的第一要義。郭氏在此認為作品中的生動與畫家的人品以及氣韻的高低有著必然聯系,是一種全新的審美趨向。對于山谷畫論思想的道出,可以參考徐復觀對于“韻”的詮釋,他說:“他指的是一個人的情調、個性,有清遠、通達、放曠之美,而這種美是流注于人的形相之間,從形相中可以看得出來的。把這種神形相融的韻,在繪畫上表現出來,這即是氣韻的韻。”[6]332文人作畫的態度不再局限于為藝術而藝術,更重要的是自身體驗,即“高雅之情,一寄于畫”。山谷提出的畫品以人品為本的思想是當時文人畫思潮的一個重要方面。他強調畫家的人品修養對于繪畫創作起決定作用,因而要求畫家注重道德品格修養和文化積累。山谷一生家庭不順,事業多舛。生活閱歷使他飽嘗人生的滄桑和人世的苦難,為了排解苦悶,他一方面參悟禪宗思想,另一方面受潛意識的支配,苦悶轉化為內在的性格張力,得以在他的書學上以及畫學思想上抒發。《題摹燕郭尚父圖》云:“凡書畫當觀韻。”山谷重視繪畫作品中的“神”和“韻”。《和子瞻戲書伯時畫好頭赤》云:“李侯畫骨不畫肉,筆下馬生如破竹。”山谷認為藝術重現應不重視畫面的再現,而是要盡脫俗塵,唯顯本真的氣韻。
他的這一畫論思想與時代美學思潮以及當時文化背景都有著密切的聯系。山谷以儒學思想自居,又力圖兼容佛、道兩家,構成其獨特的畫論思想。宋代繪畫藝術更加注重文人理想人格和理想社會的展現,精神世界的建構就顯得尤為重要。山谷的這些觀點對于后世文人畫的理論與創作的影響深遠。南宋趙希鵠《洞天清祿集》云:“胸中有萬卷書,目飽前代奇跡,又車轍馬跡半天下,方天下筆。此豈賤者之事哉?”可從中窺探出山谷留下的畫論遺韻[7]。
二、品評鑒賞
山谷的一些題畫詩重在鑒賞,是站在文人畫派的立場上立說評價的。
(一)以禪論畫
黃庭堅生活在宋代禪宗興盛時期,佛教禪宗思想對于其繪畫美學思想影響深刻,他一生中結識眾多禪宗詩友。嘉佑七年,山谷在此年結識俞清老,并自稱清風客;治平四年,山谷在結識江西老禪惠南等人。黃庭堅論畫中常滲入禪理,表現理趣。他熱衷于描寫日常的生活,不注重繪畫寫實與臨摹,參禪而論畫。他的題畫詩中滲入禪理,表現理趣又與其他詩歌有所不同。山谷題畫詩《題竹石牧牛圖》中云:“子瞻畫叢竹怪石,伯時增前坡牧兒騎牛,甚有意態,戲詠。野次小崢嶸,幽篁相倚綠。牧童三尺棰,御此老觳觫。石吾甚愛之,勿遣牛礪角。牛礪角猶可,牛斗殘我竹。”[8]蘇軾與李公麟作《竹石牧牛圖》,子瞻畫叢竹怪石,李公麟畫前坡牧童和牧牛。“牧童三尺棰,御此老觳觫”中“觳觫”代指牧牛,“牧牛”是一個典故,來源于當時興盛的禪宗,以牧牛來比喻調心。山谷又說道“石吾甚愛之,勿遣牛礪角”,即是心性難以馴服。最后,山谷寫到“牛礪角猶可,牛斗殘我竹”,反其意而用之,意思是:石頭是我喜歡的,但不要讓牛兒在上面磨角,牛打斗起來,要殘損我的竹子。竹子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一種高風亮節的人格象征,是古代文人的精神追求,所以山谷在這里強調,心性難以馴服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有失氣節。整首詩充滿禪理,也是子瞻和李公麟創作時想表達一種安靜祥和的光景,但是山谷卻從畫中得到了很多禪意,其題畫詩也為畫面增加了很多理趣。
黃庭堅是以“禪”鑒畫的集大成者,繪畫、禪學、詩學互為相通,將北宋繪畫的品評鑒賞理論推向一個新的高度,這一鑒賞觀同時也介入到畫家的藝術創作中。南宋時期畫家梁楷擅畫禪畫,與僧人智愚、妙峰等人交往密切。其所畫《潑墨仙人圖》是一幅充滿禪理的畫,采取大寫意的畫法。后來牧溪和玉潤學習到了梁楷的減筆畫畫法,以寥寥幾筆來抒寫情感。牧溪喜畫龍虎猿鶴、蘆雁山水及樹石人物,皆隨筆點染而成;法常的《叭叭鳥圖》畫八哥鳥立于松上,簡單數筆,使得畫面境界空靈;玉澗禪師擅長潑墨山水,畫法極簡。南宋時期的藝術創作通過大面積留白來展示對空靈之美的追求。由此可見,禪宗尚“簡”理念與南宋禪畫的留白寫意之風不謀而合,士人思想與禪畫思想高度結合。宋代禪畫的發展受到黃庭堅等人的影響,一定程度上促進畫家思維的發散,這一思想到明清時期深深影響到了董其昌、四僧等人,將禪畫藝術推向了高峰。
(二)重天機
黃庭堅喜用“天機”“造化”“妙”等詞來評畫,這也是山谷對于品評鑒賞的一個重要美學命題,其所賦予的內涵大致有二:
一是指所畫之物得妙于心。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中有關于妙的闡述:“但命物之意審的先決條件,乃在由超越世俗而呈現出的虛靜之心,將客觀之物,內化于虛靜之心以內;將物質性的事物,于不知不覺中,加以精神化;同時也是將自己的精神加以對象化。”[6]233繪畫先成于胸,超越骨法用筆、經營位置等技法,進入物我兩相忘的神妙境界。又如山谷題畫詩《戲詠子舟畫兩竹兩鸜鵒》中云:“子舟之筆利如錐,千變萬化皆天機。未知筆下鸜鵒語,何似夢中胡蝶飛。”山谷認為黃子舟筆下的竹子和鸜鵒給人一種極高超的畫技卻又不露一絲痕跡的表現出平淡天真的意境的畫作。“千變萬化皆天機”,正如石濤在《苦瓜和尚畫語錄》中云:“至人無法。非無法也,無法而法乃為至法。”
二是指畫家本人的靈機天賦。《觀劉永年團練畫角鷹》謂其“旁觀未必窮神妙,乃是天機貫胸臆”。與《詠伯時畫太初所獲大宛虎脊天馬圖》中“筆端那有此,千里在胸中”及《答王道濟寺丞觀許道寧山水圖》中“許生再拜謝不能,原是天機非筆力”合觀,知“天機”是畫家的天賦靈機,山谷常以此評畫。山谷認為畫家的藝術作品往往能反映出其人格和品味,這在很大程度上與一個人的修為學養有關。早在唐代,張彥遠便在《歷代名畫記》謂之:“自古善畫者,莫匪衣冠貴胄高逸之士,振妙一時,傳芳千祀,非閭閻鄙賤之所能為也。”[9]
三、結語
綜上所述,黃庭堅的論畫鑒賞理論既繼承前代重表現藝術家心理情趣的繪畫理論,又汲取歷代論畫鑒賞家的獨到見解,以北宋文人畫派的身份結合論畫詩繼而進行創作。其創作理論中的尚師法造化,輕傳移模寫,形神兼備、氣韻生動等,在前人立說的基礎上有所拓展,極具價值。其品評鑒賞中的以禪論畫、重天機在汲取了儒、釋、道三家思想基礎上形成了超塵絕俗的品評標準。黃山谷這些文人畫論觀對北宋以及后世文人畫創作和鑒賞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參考文獻:
[1]鄧椿.畫繼[M].明津逮秘書本,卷八.
[2]鄭永曉.黃庭堅年譜[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306.
[3]北大古文獻研究所.全宋詩[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4]郭若虛.鄧白,注.圖畫見聞志[M].成都:四川美術出版社,1986.
[5]郭元釪.全金詩[M].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六十八:735.
[6]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
[7]黃寶華.黃庭堅評傳[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415.
[8]孫紹遠.聲畫集[M].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七:89.
[9]張彥遠.俞劍華,點校.歷代名畫記[M].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4:25.
作者簡介:顧冉冉,河南大學美術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