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庵夢憶》于文學選本中的經典化探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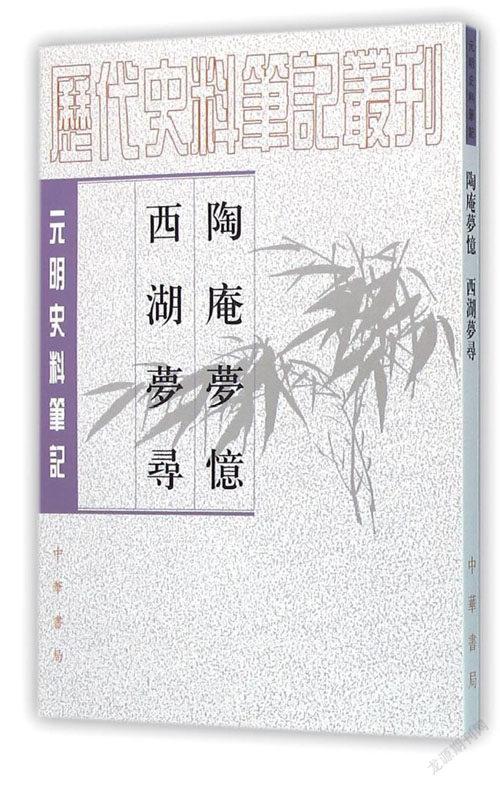
摘 ?要:《陶庵夢憶》的部分篇章已成為現當代各種古代文學選本的必選篇目,然而在清代,即便是專錄小品的文選,也不曾選錄此書中的文字。除了書本流傳有限等因素以外,最根本的原因是清人多將此書當作史料對待。20世紀二三十年代,新體散文的發展促進了周作人等作家對此書的重新定性,書中的很多篇章也在那時奠定了其經典地位。這些名篇在行文風格上類似言談,在表達上注重意象與感受的傳遞,在內容上尚奇,表現了率真的人生態度和追求“雅”的趣味,并有著復雜的闡釋空間。這些特性與現代散文特點的高度契合,是原本被清人視作史料的張岱的文字,在近現代被選為經典古代散文的重要原因。
關鍵詞:陶庵夢憶;經典化;文學選本
《陶庵夢憶》是張岱的代表作之一,建國以來的各種文學作品選、教材,大都會選錄其中的篇章。據筆者粗略統計,1949年以來至少有130余種古代文學作品選、語文教材錄入了《陶庵夢憶》中的作品。其中,選入《西湖七月半》的選本高達86種,入選次數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分別是入選了46次的《湖心亭看雪》和入選了35次的《柳敬亭說書》。文學選本的編纂歷來是文學批評和文學傳播的重要方式,對文學作品的流傳影響深遠。然而與當下的傳播情況截然相反的是,有清一代,張岱的散文是鮮有選本問津的。筆者檢閱了《中國古籍總目》中所有可致的明清古文選集共56種,其中并無一種著錄了張岱的文章,即便是搜集廣博的選本如《明文海》、專錄小品的選集如《怡情小品》,這樣情況亦無例外。
眾所周知,當下張岱散文地位的確立,離不開上個世紀30年代和90年代的兩次對張岱文集的出版和研究熱潮。但在清代兩百多年的時間里,文學選本為何會長期忽視張岱的文字?張岱的散文又因何在兩百多年后的民國突然煥發活力,一躍成為中國古代散文的代表?《西湖七月半》等文作為經典選篇的出現正代表了這種文學接受的過程。本文希冀通過對此過程的梳理,探尋張岱文章在清代和民國截然不同的接受情況的內在邏輯。
一、被湮沒于清代的“史文”
從現有資料來看,《陶庵夢憶》似乎并非出于一種文學家的創作,而更多地出于一種史家的記錄,這也構成了其文湮沒于清代的根源。雖然如今的文學史談到《陶庵夢憶》和《西湖夢尋》,多會將它們和晚明小品文相聯系,但兩書中的文字是否能夠作為晚明小品的代表是值得商榷的。對此潘承玉《別一時代與文體視野中的張岱小品》一文對其創作動因進行了十分充分的論述,他認為“兩夢”是一種“特殊‘史文’”[1]。張海新在《水萍山鳥——張岱及其詩文研究》一書中也提到應該將二書看作一種“筆記”,而不是“小品”[2]。二者皆從張岱的創作心理出發,認為將二書目作“史料”更加符合張岱的創作期待。
而從清人接受的角度來看,這樣的觀點也是可以得到印證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將《西湖夢尋》放入史部地理類山川之屬,已經能夠代表清人的官方態度;清代學者在提及《陶庵夢憶》時,亦多以史料目之。如乾嘉年間的學者陳琮所著的《煙草譜》,便引用了《陶庵夢憶》中的《蘇州白兔》,將其記載作為一種史料用以說明煙桌為何物。其后方濬師、王維翰、俞樾等人在《兩浙輶軒錄》《湖山便覽》等書中亦多次引用二《夢》中的文字,但皆緣于其史料價值而非文學價值。清代現存唯一對《陶庵夢憶》的評點來自于乾隆年間的王文誥,從其評點之中,我們也不難看出《夢憶》是被當作“史”而非“文”。開卷評《鐘山》,王評即言“首敘鐘山,亦猶《禹貢》之首敘冀州也”[3]3,將《陶庵夢憶》與“記言之祖”《尚書》相類比;其評《嚴助廟》則云,“記事古奧,如讀《汲冢周書》”[3]347;評《目蓮戲》則云,“可抵一篇《鬼方記》”[3]363。雖然在評語當中,王文誥多次贊揚其敘述描繪之精妙,但毫無疑問,評者并未將《夢憶》當作小品文章來對待。
另一方面,自清初始,晚明文風便開始受到猛烈抨擊,黃宗羲直言公安竟陵詩文“根孤伎薄”[4],四庫館臣評更是對晚明文風表現出一種近乎鄙薄和漠視的態度,這種態度也代表了大多數清代古文選本的態度。總體來看,眾多文選,無論是清初的《古文輯略》《文津》,還是乾嘉以后的《國朝文征》《國朝古文選》;無論是選時文還是古文,無論是桐城選者還是非桐城選者,他們所尊崇的,皆是一種醇雅的文風。即便是陳繼儒、袁宏道、鐘惺等已頗有名氣的作者,也少有選集對他們的作品進行刊選,遑論隱居山中,“間策杖入市,市人有不識其姓氏者”[5]170的一介遺民張岱所作的被目為史料性質的文字呢。
二、被現代作家“發現”的“小品”
近代是文章劇烈變動的時代,“文”的概念及功用發生了根本的轉變,文章的范疇不再囿于傳統的載道古文,其面貌開始變得多元化。而在這個過程中,原來被劃分為“史”的張岱的文字也獲得了一個“古文小品”的身份,并進一步升格為古代散文的代表。
這種轉化是由周作人等散文作家開啟的,他們對晚明小品大力提倡,而這種提倡,又源自周作人等人對新的文學體式——“小品散文”的探索與創新。1922年,胡適對當時的文學發展成就總結道:“這幾年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6]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小品散文”與晚明的“小品”并非同一文體概念,它是指周作人等人基于外國散文的范式對白話文所作的一種新嘗試。周作人在1921年5月發表的《美文》 [7]29中介紹了西方美文的概念并首次表達了一種創作“小品散文”的倡議。夏丏尊1919年于長沙第一師范任教時所作的寫作課講稿于1922年刊成了《文章作法》一書,其書最初將文章分為“記事文”“敘事文”“說明文”“議論文”,刊行的那一年卻又增添“小品文”一類,似乎亦受到了當時作小品文倡議的影響。其書對當時的小品文定義道:“現在所謂的小品文實即Sketch的譯語,大概都是以片段的文字,表現感想或現實生活的一部分。”[8]從這些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小品散文”是由西方文學的范式所引發的對白話文學的新嘗試。
但是,從根源上來講,周作人、俞平伯等人作為飽受古典文化熏陶的作者,其目光在面向西方范式的同時關注古典的范式,則是一種必然的趨勢和結果。由于他們有著融通中西古今的眼光,故能突破原有的學科界限,僅從文字文學性的角度對古代的材料進行文學發現。周作人1922年2月發表的《國粹與歐化》一文便已經展現出了這種態度,他說:“我卻以遺傳的國民性為素地,盡他本質上的可能的量去承受各方面的影響,使其融合沁透,合為一體。”[9]而作為張岱同鄉的他年少時便有閱讀《陶庵夢憶》的經歷。那時他接連經歷了破家亡父之痛,與張岱有著相同的感慨,故他本就有著將這種雜史筆記作為自己情感寄托的傾向。在1923年的《地方與文藝》中他進一步提道:“王(思任)張(岱)的短文承了語錄的流,由學術轉到文藝里去,要是不被間斷,可以造成近體散文的開始了。”[10]在這里,周作人第一次提出了張岱文字的“文藝”特性,言其從“學術”轉向“文藝”,已開啟了近代將張岱的文字目為散文的肇端。其后,周作人與俞平伯這對師生就古代散文的問題,有著頗多的交流,俞平伯還曾向周作人報告他讀張岱文字的感受。那時俞平伯一方面作著新詩,一方面從事著古典文學的研究和出版,在周作人的介紹下,他重新點校了《陶庵夢憶》一書,并于1927年4月刊行。
毫無疑問,周作人和俞平伯對《陶庵夢憶》等書的發現是靈活而頗具創見的,在這之前,此書仍是作為一種史料流傳著。1906年的《雁來紅叢報》曾刊錄過《陶庵夢憶》,將其歸錄到“稗史類”[11];到了1925年,《京報副刊》刊登過《有志研究中國史的青年可備閑覽書十四種》[12]一文,從此報我們可以看到,《陶庵夢憶》作為“史”的身份在當時仍未改變。從1920年到1927年刊行的多部中國文學史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當時的文學史中,是毫無張岱的影子的;1921年劉貞晦等人編寫的《中國文學變遷史》中明代文學到介紹到公安派和竟陵派便休止了;凌獨見的《新著國語文學史》、李振鏞《中國文學沿革概論》、顧實《中國文學史大綱》等,雖體例不一,但情況亦大同小異。而1927年俞平伯點校的《陶庵夢憶》的刊行,可以說是張岱于近代傳播的一個里程碑,此書由樸社發行,還請周作人作了序,周序對張岱多有贊許,并第一次明確地稱張岱的文字為“文章”,言“《夢憶》可以說是他文集的選本了”[5]171。此序發表在了當時著名的《語絲》雜志上,影響頗廣。自此之后,文學界便出現了一股出版和編選古文小品的熱潮,到30年代甚至出現了關于明代小品文的論爭,張岱從寂寂無名的古書作者變成了一個文學選本繞不過的人物,《西湖七月半》與《瑯嬛文集》也相繼出版。他經典的地位,便是這一時期奠定的。這些前人已多有介紹,茲不贅言。
三、契合現代散文特性的“經典古文”
嚴格來說,雖然張岱已經是文學史無論如何也繞不開的作者,其最為經典的文章也大都出自于《陶庵夢憶》,但我們并不能簡單地將此書稱作一本經典的散文集,成就張岱散文地位的實則是近代以來被選入眾多文學選本中的經典篇目,而非《陶庵夢憶》全書。
通過對各種古文選本中篇目的對比,我們大致可以確定,《陶庵夢憶》的“經典篇目”,在建國以前已大體定型。1927年俞平伯點校的《陶庵夢憶》刊行以后,此書中的篇目便開始進入各種選本。自1932年汪倜然所編的《明代文粹》、沈啟無所編的《近代散文抄》錄入其作品后,共有12種文選錄入了張岱的文字。這些文選自然有不同的編選標準,如胡行之的《古代幽默文選》專收幽默活潑的文章,葉楚愴的《歷代名家筆記類選》則主要選錄筆記,但《陶庵夢憶自序》《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柳敬亭說書》等篇仍舊是這些選本中被選頻率最高的篇目。以1929年到1949年出現的14種古代文選為例,14種選本當中有9種都選錄了《西湖七月半》,另外有6種選錄了《陶庵夢憶自序》、有5種選錄了《湖心亭看雪》。被選錄次數較多的還有《閔老子茶》《柳敬亭說書》《彭天賜串戲》《西湖香市》等12篇文章,建國以后的作品選所選篇目也大都不出前人選篇的范圍。
如果說俞平伯點校的《陶庵夢憶》的大量刊印是對張岱的重新發現,那么這些篇章重復地出現在各種古文選本中,則是一種對張岱文字的重新定性。在古代文選中本為史料的文章并不少見,《陶庵夢憶》這些篇目的特殊處在于,它們進入古文選本時,現代文已經較為成熟,文學與史學、文章與史料在學科分類上的界限已經相對明晰,它們能夠進入古文選本,與先秦兩漢諸子、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并列,很大程度上是現代作家和文選家,以現代的趣味、現代的審美對其進行的一種發現。那么張岱的文字又體現了怎樣的現代審美趣味呢?筆者認為有如下幾點:
(一)《陶庵夢憶》雜史的身份使其有一種“以說話行文”的特性,其經典篇目便是建立在這種特性的基礎之上的,而這與現代的小品散文是相通的。林語堂說:“中國好的散文,大部全在白話小說……聊有西洋小品閑談風味。”[13]可見在他的文學觀念里,“閑談風味”是好散文的要素之一。古代散文總體是有其固定的形式的,無論是對“文以明道”“文以載道”的追求,還是“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的強調,文章與言談無論是在內容上還是在形式上都是存在距離的。而張岱的文字由于這種雜史的身份,沒有了游記、人物傳記等格式束縛,便更加接近言談。無論是《湖心亭看雪》《西湖七月半》等廣為流傳的名篇,還是《日月湖》《越俗掃墓》等熱度稍次的篇章,張岱始終都在以一種介紹者的口吻,敘述其所經歷的人與事。另一方面,這種類似言談的行文風格,導致文章無論是在內容上還是在行文形式上,都有一種“尚奇”的追求,其內容的核心,不在于思想的傳遞,而在于奇聞奇事的表現,這是他的文字能夠被目為文學散文的重要原因。《陶庵夢憶》所記之事、所寫之人,皆新穎奇警,這根源于張岱本人廣泛的興趣愛好,尤其是對獨特的審美體驗的熱愛與癡迷。無論是金山半夜看戲、還是人鳥聲俱絕時在湖心亭看雪,或是毫厘不差地辨別水源自何處,皆非尋常事,亦非尋常人能有之情。而在周作人等人對《陶庵夢憶》進行推崇之前的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正是這種尚奇的特性使它得以傳播和保存。
(二)《陶庵夢憶》對意象與感受的傳遞十分精確,其經典篇目在這一點上表現得尤為明顯,而這與現代散文的核心追求十分契合。在古典文學中,意象與感受的傳遞本是詩歌的專職,而傳統古文,即便是描繪景物的游記,大都有著傳遞思想與哲理的癖好。但現代散文將這種界限打破了,周作人在提倡美文時便指出它是“詩與散文中間的橋”[7]29,沈從文亦言“敘事如畫,似乎是當時一種風氣”[14]。可見現代散文自誕生之始,便有著重意象與感受傳遞的特征。張岱有著極強的洞察事物典型特征的能力,并能將這種典型特征精確地描繪出來,感受的傳達本身即是其文字的核心目的。試觀其《金山夜戲》之寫月光一段:“月光倒囊入水,江濤吞吐,露氣吸之,噀天為白……林下漏月光,疏疏如殘雪”[5]13,環境之靜謐,月色之皎潔,皆不言而出。其描寫似乎能夠使人看到一個動態的景色變化過程,露氣哪會“吸之”?江濤哪會“吞吐”?但經此一描繪,仿佛一切意象都自動浮現眼前,甚至不須讀者動用頭腦去想象。另一方面,為了更為精確地傳遞某些感受,張岱往往使用一些新奇夸張的句式和修辭,形成了一種活潑諧謔的獨特文風,這種文風實則又與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林語堂等人所倡導的幽默相通。如前文所舉“露氣吸之,噀天為白”諸句,夸張的修辭除了給讀者新奇的感受之外,還給意象增添了一種滑稽感。這些形容配以靈活而富有節奏的句式,不僅使文字對感受的傳達準確新奇,也更能使讀者映像深刻。尤為典型的是《陶庵夢憶序》中的描繪:“以笠報顱,以簣報踵,仇簪履也;以衲報裘……以囊報肩,仇輿從也。”[5]1“報”字和“仇”字的使用多少帶有一點游戲的意味,但這種用法使原本靜態的意象活動起來,在最大程度上調用了讀者的感觀,故新奇諧謔之感便油然而生。在上世紀30年代林語堂大力提倡“幽默”,而那時也正是《陶庵夢憶》以文學作品的身份進入大眾視野、確立其經典地位的時期。
(三)在思想內核上,《陶庵夢憶》的經典名篇集中表現了張岱崇高而獨特的審美追求,這種審美追求與現代散文,尤其是周作人等人所倡導的小品散文,具有相當程度的一致性。這種追求首先體現為對“雅”的肯定和推崇。無論是雪夜里到湖心亭看雪,還是俗人散盡以后方盡興賞月,抑或是夜半在寺中張燈唱戲,所表現的皆是一種對“雅”的極致追求,這與周作人等人的散文追求是相呼應的。周作人評價俞平伯的散文是“最具文學意味的一種”[15],而他所言的文學意味便是“雅”的趣味。這種追求與工業社會帶給人們的高速度而模式化的生活有關。1935年《申報》月刊社出版的《小品文選》的“序言”對當時小品文得以流行的原因作了這樣的闡釋:“都市里面的人雖不一定都是過著高速度生活的人,然而這高速度的旋律卻多多少少波及他們的頭上……必然有供給給這些人的精神食糧”[16]。現代都市浮躁與喧囂,讓人們對高雅趣味和獨特個性有了更多的渴求。張岱在《陶庵夢憶》中所傳達的,正是這樣一種超越塵俗的態度和精神,他對生命感官價值本身的肯定,對生命美的表現,正好契合了現代人的心靈渴求。另一方面,張岱所追求的“雅”并非是附庸風雅,而是率真地對美好審美體驗的表達,所透露出的是一種真性情,這不僅符合現代散文作家的文學創作觀,也符合生活在浮躁壓抑的城市環境中的讀者的期待視野。另外,由于《陶庵夢憶》中還摻雜著國破家亡的悲恨,這種對美好審美體驗的追求與描繪,便不再僅僅是對享樂生活的追求與描寫,而是增添了一層反思時代與人生的深沉意味,這種性質的變化也給予了這些篇章更多的闡釋空間。
四、結語
童慶炳在《文學經典建構諸因素及其關系》一文中提出了六種使文學作品得以經典化的要素,即“藝術價值”“可闡釋空間”“意識形態和文化權力變動”“文學理論和批評的價值取向”“特定時期讀者的期待視野”“發現人”[17]。以這六個標準來看,《陶庵夢憶》中的這些篇章準確傳遞了特定的審美意象與感受,所描寫的也大都是獨特而新奇的內容,本身就具備著一定的藝術價值。又由于張岱國破家亡的生活背景和獨特的審美追求賦予了這些文字“可闡釋空間”,并順應著當時追求“雅”的趣味和“以說話行文”的“意識形態和文化權力變動”,也有著林語堂、周作人等人提供的“文學理論和批評的價值取向”的支撐,并且與現代的“讀者的期待視野”相符合,還有著魯迅、周作人、俞平伯、林語堂等一大批“發現人”,故在近代大環境的變遷下,這些文章變成經典篇目是一種必然結果。從湮沒于清代藏書館閣中的史料,到被現當代文學批評家所推崇的經典古代散文,張岱這些作品的文學地位的變化,為我們看待文字作品在不同時代的價值流變提供了一個典型的樣本。通過對這個經典化過程的分析我們也可以看到,作品的藝術價值本身,尤其是準確傳遞意象與感受的價值,在這個過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而這些價值也并不會被人們給文字打上的分類標簽而埋沒。
參考文獻:
[1]潘承玉.別一時代與文體視野中的張岱小品[J].文學遺產,2006(1):116-123+160.
[2]張海新.水萍山鳥張岱及其詩文研究[M].上海:中西書局,2012:281.
[3]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續修四庫全書(第1260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黃宗羲.寒邨詩稿序[M].北京:中華書局,1985:5.
[5]張岱.陶庵夢憶[M].北京:中華書局,2008.
[6]龔海燕.海上文學百家文庫[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0:509.
[7]周作人.談虎集[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8]夏丏尊,劉薰宇.文章作法[M].北京:中華書局,2013:85.
[9]周作人.自己的園地[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1.
[10]周作人.談龍集[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4.
[11]佚名.雁來紅叢報[J].1906(6).
[12]顧頡剛.有志研究中國史的青年可備閑覽書十四種[J].京報副刊,1925.
[13]林語堂.閑情偶寄[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92.
[14]沈從文.文學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266.
[15]周作人.苦雨齋序跋文[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22.
[16]申報月刊社.小品文選[M].上海:申報月刊社,1935:3.
[17]童慶炳.文學經典建構諸因素及其關系[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5):71-78.
作者簡介:劉艮,湖南師范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