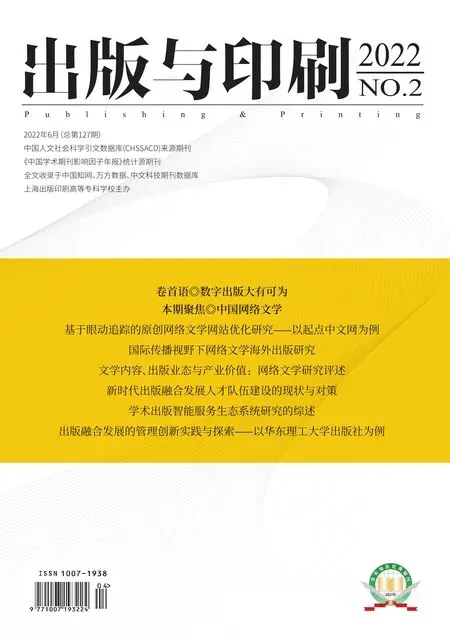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研究的綜述 *
徐潤婕 王鵬濤
一、引言
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新技術,驅動人類社會由農業化到工業化、再到信息化,并朝著智能化方向發展,出版業迎來了廣闊的發展空間。處于內容供給方的學術出版積累了海量內容數據,在智能技術應用中具有先天優勢,在智能化轉型中大有可為。[1]462,[2]34處于內容需求方的用戶,面臨內容資源無限增長性和時空有限制約性的矛盾,在學術創新與再創造過程中產生專業化、個性化的服務需求,從而成為學術出版服務智能化轉型的根本動力。[3]50我國在國家層面高度重視和支持學術出版發展,科技強國、科教興國戰略以及國家科學技術學術著作出版基金、國防科技圖書出版基金等項目[4],為學術繁榮和科技創新提供了強大支撐。
學術出版是學術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環節,能夠積累研究成果,促進學術交流與發展,是科研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推動力量,對學術研究及科技發展具有重要意義。[5]一方面,健康繁榮的思想市場是科技文化發展的保障,學術市場是思想市場的關鍵部分,其活躍與有序依賴于學術出版的繁榮和規范。[6]另一方面,學術出版培育和服務于強大的科研隊伍,為科技強國積蓄后備力量和主力軍。[7]此外,服務于國家重大戰略、推動學術成果的交流和轉化是學術出版的重要使命。
智能技術深入學術出版領域,呈現出構建全新的學術出版生態模式的趨勢,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成為實踐和學術研究的焦點。在實踐領域,英國皇家化學會(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英文縮寫RSC)基于本體和唯一的化合物標識符,使內容數據成為機器可讀的形式,進而與學科知識環境(如RSC化學結構數據庫ChemSpider等)關聯、進行結構化描述與標記[8],實現全文嵌入式HTML功能,從而構建語義出版生態系統,改變發現、分析、解釋和重用科學信息的方式[9]293。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圍繞語言、專業知識、出版信息、學術項目等搭建學者服務平臺,探索為學術研究提供全方位、高附加值解決方案的數字學術出版服務模式[10]9。在學術研究中,形成了以智能技術在出版領域的應用實踐[2]35,[11],[12]1091和以服務主導邏輯取代商品主導邏輯[13]19,[14]16為基礎,以學術生態化與出版生態化[10]8,[15],[16]78為過程,以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17]34,[18]913,[19]249為高潮的研究結構,知識服務、智能出版、開放科學成為研究熱點,研究內容涉及信息技術、經濟管理、信息管理、新聞出版等多個領域。例如,劉平等[1]463、張承兵等[20]17探索智能技術優化學術出版的路徑和措施,構建學術出版新模式;阿爾特曼(Micah Altman)等[21]4發現將學術知識生態系統的治理交由經濟市場,會影響技術帶來的學術公平和民主;朱純琳[22]、孫建輝等[23]42從圖書館角度對運用智能技術構建學術服務生態系統進行了研究。
梳理現有文獻發現,國內外學術出版服務生態系統的研究各有側重,國外研究側重于從宏觀視角探討學術出版生態系統中的公平和效率,國內重點研究生態系統中各參與者的行為。總體來看,理論研究仍需加強。因此,十分有必要針對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構建這一領域的文獻進行梳理,系統化地對相關研究進行溯源和總結,提出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研究的主題、理論框架,指出未來研究方向,以期為科技強國戰略下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的學術研究和實踐貢獻思路。
二、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的研究脈絡
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的研究集中了多個學科領域的思想,如數字技術與智能技術、服務主導邏輯與商業生態系統、生態學等,這些思想匯聚于學術出版領域,推動學術出版研究向下深入和向外擴張。
1. “生態系統”思想進入出版領域
“生態系統”(ecosystem)是生態學領域的關鍵概念,一些學者發現自然生態與社會生態存在許多相似之處,“生態系統”思想逐漸廣泛應用于管理學領域[24]。坦斯利(Arthur George Tansley)[25]提出,生態系統是在一個特定地點由生物和與之相關聯的物理環境所組成的社群或集合,奠定了生態系統的思想[26]148。1993年,穆爾(James F. Moore)率先將生態的概念引入管理學研究,提出了商業生態系統的概念[27],并將其定義為由商業環境中的組織與個人相互依賴、相互作用形成的“經濟共同體”[28]。隨后眾多學科運用生態系統思想來揭示各自領域的理論與實踐問題,涌現出“企業生態系統” “創新生態系統”“平臺生態系統”等多種研究。它們都是商業生態系統的衍生,具有由生態系統本質所決定的共同特征[29],即不同主體相互依賴、參與者跨產業邊界、主體間存在非契約安排;但研究重點分布于單個企業、企業間的互動或眾多企業共同搭建的平臺。類似地,“生態系統”還被應用于政府領域[30]610和學術領域。圍繞生態系統的研究既分散又融合,有待對其進行進一步理論開發與檢驗[31]。
2. 出版業服務主導邏輯的興起
商品和服務的主導地位之爭由來已久,以“經濟學之父”斯密(Adam Smith)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對此進行了討論,但都將商品和服務分開對待[32]2。商品主導邏輯成為許多學者分析問題的主要思想。互聯網的興起模糊了商品與服務的界限,從資源觀的角度來看,知識、信息等無形資源在生產活動中日益重要,甚至超越有形資源處于主動地位[33]。自2004年起,瓦戈(Stephen L. Vargo)和勒斯克(Robert F. Lusch)在一系列研究成果中,建議用服務主導邏輯(service-dominant logic)取代傳統的商品主導邏輯,以重新審視商品和服務,[32]3并形成了以操作性資源和競爭優勢為基礎、以市場交易機制和價值共創模式為核心、以服務生態系統為歸宿的服務主導邏輯理論體系[32]5。在服務經濟背景下,社會經濟活動的參與者進行資源整合和價值共創,由此拓展出服務生態系統概念[26]148。學術界從不同角度進行探討,涌現出大數據服務生態系統[34]、信息服務生態系統[35]、企業服務生態系統[36]等相關研究。出版業的內容產品集合了物質和非物質要素,其內容價值的實現取決于讀者或用戶根據自身處境對其作出的闡釋,向服務導向轉型是出版業的必然選擇[14]17。進入大出版時代,出版企業與包括讀者或用戶在內的其他利益相關者合作形成了出版服務生態系統[13]21,各主體從生態系統中整合與調動資源、共同創造價值,這是服務主導邏輯與出版業結合的必然延伸。
3. 智能技術與學術出版的融合
人工智能技術與出版業的深度融合,推動了出版服務的智能化、場景化和精準化[12]1095。學術出版擁有海量知識內容、精準的用戶群體和明確的市場需求,有望率先實現智能化轉型。[2]34學界探討智能技術在出版服務中的應用,主要有兩個視角:從內部探究對出版流程的重構;從外部討論對出版知識服務的優化。向颯[12]1093、李媛[37]、劉銀娣[38]等學者討論了智能技術在文獻出版、傳播、存儲、評價等環節的應用,有助于學術出版實現自動化質量檢測、精準內容分發、智能學術搜索和文獻計量。出版流程智能化帶來了學術出版方式的重大變革,出版服務模式向知識服務轉變。張承兵等[20]18、李玲飛[39]78、鄧逸鈺等[17]35揭示了運用智能算法實時捕獲并引導用戶需求、精準匹配服務供給與需求、高度共享學術內容資源,為科研用戶的研究與創新提供智能化、場景化和精準化服務。智能服務貫穿于科學研究全生命周期,學術出版各主體功能在技術賦能下得到橫向拓展和縱向延伸,傳統鏈式結構的產業鏈轉變為多維立體的生態系統[40]45。
三、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的研究視角
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的研究更新了傳統的學術出版對作者、出版者、讀者以及出版環境的認識,研究成果涉及信息科學、管理學、經濟學以及出版學等學科理論與實踐。下面將從技術、管理和環境等視角對現有研究進行梳理。
1. 技術視角
研究者主要通過技術視角來探討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構建的可行性,包括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學術資源整合平臺建設、智庫建設等,并將數字出版的“技術決定”特征轉化為“技術創新管理”,最終目的是提供有效服務。劉平等[1]463將“人工智能+出版”的出版形態定義為智慧出版模式,人工智能技術優化和升級了學術出版的選題策劃、內容生產、編輯加工、傳播推送、閱讀體驗、內容服務等流程,以提供高效、精準、場景化和定制化的服務。基德(Richard Kidd)[9]293指出,以英國皇家化學會為代表的研究機構致力于建立適用于所有主題領域的通用標識符,以增強學術文本語義,實現知識單元的關聯和重用。在此基礎上,建立學術資源整合平臺可以“分步走”,后端整合出版產品,中端基于出版資源研發知識服務產品,前端針對用戶需求提供個性化服務[41]。尤哈斯(Gabriel Juhas)等[42]248將內容資源視為廣義上的“數據”,構建了科學數據生態系統的子系統——科學出版生態系統(scientific publishing ecosystem,英文縮寫SPE),它不僅供學者發布研究成果,還可以集合研究中的數據、表格和算法,通過知識挖掘等手段建成出版智庫[43]。
2. 管理視角
管理視角主要探究在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構建過程中面臨的制度困難,并試圖通過變革制度和機制來尋求解決方案。學者們的研究范圍突破單個主體、技術或信息對象,而擴展至信息生命周期及生態系統[21]2。在這個生態系統中,參與者主要包括科研人員、大學和研究機構、出版商、圖書館、學術團體或協會、政府等[19]249,[44]8。參與者通過資源流動、契約、信任、共享的價值或愿景等相互聯系[45]60,共同完成學術作品的創作、審查、發行、存檔和使用等工作[44]8。尤哈斯等[42]247指出科研工作者在學術出版環節中承擔了絕大部分工作。他們不僅是學術作品的創作者和讀者,還要在正常工作之外完成學術項目和學術成果的質量管理。[19]250“唯論文”“唯影響因子”等考核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科研工作者的研究熱情,并使其追求論文而忽略了書籍、專利等同樣具有社會意義的高質量成果創作[19]251。格林(Lucy Santos Green)[18]914、尤哈斯等[42]247論述了學術評審制度的不合理性:一方面,為防止剽竊,論文發表前只允許審稿人閱讀,造成論文審查的不透明性和主觀性,甚至侵蝕公眾信任;另一方面,在現行同行評審制度下,期刊傳達的信息僅限于其發表的論文達到了可接受的標準,難以反饋論文是否具有更高水平,這導致學者傾向于提交剛好符合期刊可接受標準的作品,而不愿意提供更高水平的成果。
如何變革制度和機制來構建高效有序的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阿爾特曼等[21]5強調審稿人要自我約束,以讀者需求和稿件質量為擇稿標準,并建立問責制進一步規范審稿人行為。常唯等[46]、尤哈斯等[42]249探索了同行評議新模式:一是人工智能參與稿件預評審、審稿人識別與推薦;二是同行評議權限應打破出版商審稿人的界限,建立隨時開放的同行評議制度,并由學術期刊、研究機構、讀者等主體共享,提升其效率以及透明性、公平性和權威性,為學術交流提供雙向反饋渠道[30]611-612。尤哈斯等[42]248還提出可以使用網絡和云存儲技術改善學術出版常規流程,將原本相互獨立的論文轉變為可動態編譯的文檔,作者可以根據建議隨時在論文中增加新的內容或更正不當內容。由于論文變成了增量文檔,再加上學術成果分發渠道的拓展,“唯期刊/論文影響因子論”也應被多樣化的學術成果評價體系代替[16]80。
3. 環境視角
環境視角揭示了如何為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創造積極有益的社會環境,為生態系統中各主體有機運行提供能量。傳統出版社是學術成果質量的過濾器,通過為學術作品的創作和傳播提供高質量的增值服務,樹立起公眾信任[47]339。大量商業出版商的涌入重構了學術評價體系[48]61,一些學術出版商過度商業化和利益化的定位偏差會阻礙學術出版質量的提升[49]。桑迪(Heather Moulaison Sandy)等[47]346發現,作為學術信息中介的圖書館正承受著訂閱成本上升和預算縮減的雙重壓力,正在努力探索新的學術出版服務生態系統,以取代商業出版商地位。孫建輝等[23]44基于知識鏈視角,建立了以學術交流為驅動的學術圖書館出版服務模型:圖書館采取自建出版社、與出版社合作、開放獲取出版等模式,向產業鏈上下游延伸以開展出版服務。開放科學降低了學術內容成本,激勵知識信息生產和流通,實現了更廣泛的學術共享[50]。初景利等[51]主要圍繞學術圖書館給出了圖書館出版的定義,即圖書館所主導的支撐學術性、創新性、教育性成果的創作、傳播與管理等一系列活動。與之不同的是,部分學者認為不應將商業出版商排除在外。方卿等[52]從學術出版發展史和現實需求出發,論證優化學術出版服務方式和投入結構是學術出版變革的關鍵,特別指出學術出版體系不應將傳統商業出版商排除在外,而應讓多主體共同發揮作用。叢挺[53]在知識鏈理論基礎上,構建了科學數據和用戶行為數據驅動的,為用戶提供知識獲取、知識挖掘、知識內化、知識共享、知識評價與知識外化等服務,以出版機構、圖書館、科研機構為主要參與者的服務模型。各主體借助信息生態位進行定位[40]47。袁小群等[16]82也認為要拓展學術出版產業鏈,推動學術期刊出版自主平衡學術與商業功能。
科利爾(Fran M. Collyer)[48]69、莫里(Akira S. Mori)等[54]揭示了全球范圍內學術界的不平等現象,大型學術出版商集中在發達國家和地區,其出版行為能夠協助構建知識網絡,但也使非主流的知識生產邊緣化,學者不得不迎合出版商的偏好來選擇研究內容,這對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成果發表形成了巨大的障礙。馬光明[55]5立足我國學術界嚴重依賴歐美學術交流平臺的實際,指出應打造專業化的國際科技信息交流平臺,以國內“出版——傳播——評價”的內循環體系帶動學術交流走向國際。吳芹[3]51強調學術出版在從外部環境中獲得智力、技術和資金支持的同時,要反哺科技與經濟發展。如今部分國家和地區已經建立起學術信息共享流通體系,如美國的聯機計算機圖書館中心(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英文縮寫OCLC)、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英文縮寫NLA)、中國國家數字圖書館等[56]。
四、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研究的理論構建
1. 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的內涵和外延
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但目前成果尚未形成完整的概念基礎和系統理論。通過梳理以上三個視角,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的關鍵特征已經顯現,基于此可以明確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的操作性定義。
首先,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是由相互依賴的出版機構、圖書館機構、研究機構、科研人員等組成的資源整合系統。學術作品的價值是由整個價值鏈創造而非單個主體,整體功能的有效發揮有賴于各參與者的優勢互補和協作[30]618。連接生態系統要素的使能技術極大提升了資源共享和協同質效,傳統鏈式結構轉變為多維立體生態系統。擁有強大資源整合能力的出版企業在生態系統中占據主導地位。
其次,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依靠制度組合來完成內容的生產、審查、傳播、存儲和使用。瓦戈和勒斯克[57]將服務生態系統定義為“一個相對自足的、自我調節的系統,由共享的制度安排和通過服務交換創造的價值將資源整合參與者連接起來”。該定義為這一特征界定提供了啟示。從管理視角來看,各參與者處于松散耦合狀態,動力機制、分配機制、協調機制和監管機制等一系列制度組合是生態系統自我運行、調節、創新和完善的基礎[19]250-251。最后,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的目標是為用戶提供有效服務,以實現整個生態系統的利益共贏。服務主導邏輯與出版業的結合昭示了出版生態系統必須以用戶需求為導向,日益專業化和個性化的服務需要多方共同開發。生態系統是各參與者在與環境的相互作用和相互適應中形成的,反哺社會是出版業長遠發展的必然要求。因此,本文將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定義為:出版企業主導的能自我調整的資源整合系統,參與者在智能技術加持下依靠共享的制度和協議來完成服務的設計與傳遞,通過協作精準地適配用戶在具體場景下的服務訴求,在此基礎上實現整個生態系統的利益共贏。
2. 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的研究框架
明確了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的內涵和特征,可以進一步建立研究框架。(見圖1)在這個框架中,生態系統的運行以借助智能技術構建的資源整合平臺為基礎,以動力機制、分配機制、協調機制、監管機制等為作用機制,以制度導向、價值主張、用戶需求等為促進因素,最終實現價值共創和服務創新的目的和效果。

圖1 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的研究框架
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的主要參與者有科研人員、出版機構以及圖書館機構,它們作為服務生態系統的功能單元相互作用,并通過信息、行動和交易建立起聯系[58]。科研人員既是學術作品的創作者,又是學術內容資源的消費者。作為消費者時,他們通常不直接從出版機構消費內容,而是依賴圖書館或數據庫等信息中介和服務提供者來獲取資源和服務,即學術出版內容的購買和消費分離。[30]606出版機構承擔起學術內容資源的過濾和整合功能,部分出版商建立并運營資源整合平臺,供生態系統的參與者使用。[21]7圖書館機構是重要的信息資源中介,負責信息資源的保存并將其提供給科研人員使用。戰略管理邏輯認為生態系統是由具有不同屬性、決策原則和信念的行動者組成的多層社會網絡,可以根據“組織邊界”理論來界定其邊界。[45]56,60“組織邊界”理論區分了組織和環境,并將組織看作是與其所處環境互動的系統。[59]85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具有開放性和動態性,其邊界也日益模糊和可變,隨著數據庫集成商、商業出版機構大量涌入,重新劃定各參與者以及生態系統的邊界,對企業明晰自身定位、規范生態系統發展方向和進程、增強生態系統專業性和創造力具有重要意義。
運行基礎、作用機制和促進因素是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運行的關鍵,其優化和完善是生態系統健康持續運轉的保障。學術資源整合平臺集合了學術傳播、學術存取等功能,語義技術的興起使得知識挖掘與知識服務成為平臺建設的重要方向,這些功能為生態系統的建立和運行奠定了基礎。馬光明[55]5強調平臺的學術傳播功能平衡了學術成果的首發權和傳播效果的關系,能夠有效解決當前學術出版模式問題。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的作用機制是生態系統動態有序運行的重要因素,促進因素為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的運轉提供了方向,并與作用機制共同構成了生態系統實現最終目標的保障。施超凡等[40]47-48運用信息生態理論得出,出版企業智能管理要通過價值機制、反饋機制和監管機制引導企業發展,并通過數據檢測進行企業治理和風險規避。奧利維拉(Marcelo Iury S. Oliveira)等[30]617-618強調了資金、設備、人力、工具等基礎材料的重要性。基于此,本文確定生態系統作用機制包括:為其提供物質和能量來源的動力機制;對資源進行再組織的分配機制;引導各主體有序發展的協調機制和監管機制。基于服務主導邏輯的觀點認為,各參與者可以通過共建的制度和規則來規范和協調價值共創的過程。巴倫(Steve Baron)[19]250-253提出生態系統運行依賴規范、規則、意義、符號等制度組合,它們與信息政策和標準一同為生態系統提供方向指導。價值主張是參與者之間為達到共同利益點的互惠協議,他們通過固有資源創造和提供價值主張,相互連接并維持生態系統的穩定。[59]87因此,挖掘和匹配用戶需求,開發有吸引力的價值主張,為其提供專業化、場景化、個性化的服務,是價值共創的先決條件。[13]21
價值共創和服務創新是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的最終目標。基于服務主導邏輯的基本命題表示,價值共創和服務創新是服務生態系統的目標,生態系統參與者通過資源整合和服務交換,在作用機制和促進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實現服務創新和價值共創。[26]151具體來看,學術出版內容價值的實現依賴用戶協作,服務是出版業應有之義。[14]17智能技術帶給出版業全方位變革,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應關注如何更好地為用戶帶來新價值。
五、結論與展望
本文強調了開展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構建研究的必要性,回顧了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的研究脈絡,從技術視角、管理視角、環境視角梳理了現有文獻。在明確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內涵的基礎上,構建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的研究框架。該框架有助于出版生態系統中各參與者明確自身定位,參與生態系統運作并創造價值;同時為智慧時代出版業創新發展研究提供思路。
盡管研究者對構建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的呼聲熱烈,并且從不同角度進行了探討,但部分領域還有較大的研究空間。本文提出以下幾點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①結合中國情境探討如何建立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一方面,制度在服務生態系統中發揮協調和約束作用,不同環境下的制度具有其特殊性。[26]155另一方面,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科技創新和科技強國戰略置于國家發展的核心地位,學術出版所具有的集聚關鍵核心及前沿成果的優勢,與建設科技強國戰略規劃密不可分。因此,探究中國情境下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的建設具有現實意義。②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中的參與者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今后可以基于參與者角色的轉變對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進行創新。目前已有學者開展了學術圖書館出版、開放獲取(open access,英文縮寫OA)等新模式研究,這些新模式為傳統學術出版困境提供了解決思路,但這些模式是否具有長遠發展的可能,還值得進一步思考。③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具有開放性和動態性,隨著用戶需求與智能技術的更新,未來可能出現新的參與主體和交流平臺,如基于Web 3.0出現的學術社交網絡與媒體[60],原有的參與者對此如何作出應對是需要重視的問題。④討論學術出版應用智能技術存在的威脅和解決辦法。智能技術是推動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構建的重要引擎,但也給出版業帶來了隱私、版權、倫理等諸多風險。出版學界與業界不能盲目跟隨“人工智能熱”[39]81,而應從技術、管理、資金等多方面考慮應用智能技術的可行性。⑤開展學術出版智能服務生態系統的實證研究和案例研究。當前該領域的理論研究居多,案例研究較少;由于理論研究尚未系統化,因而實證研究罕見。未來可以圍繞作用機制和促進因素建立模型開展研究,還可以選擇具體的學術出版企業深入探索其智能服務生態系統模式的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