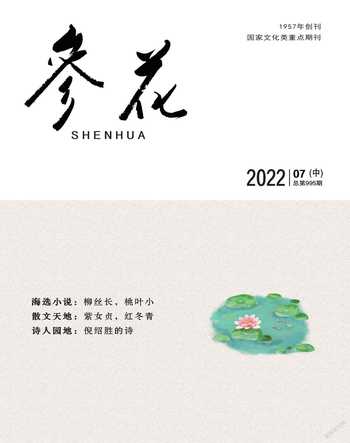《文城》對余華創作的接續與延伸
一、引言
距離余華上一部小說《第七天》出版已有九年,《文城》一經出版就引起了文壇的熱議,從人物形象、情節設置,再到主題表達,這部非傳統意義上的傳奇小說與作者以往的小說創作既有所承接,又帶來之前少有涉及的一面。提起《文城》的創作契機,余華說:“是一個錯誤的契機,大概1998年的時候,二十世紀快要過去了,我想寫《活著》以前的故事,因為《活著》是從四十年代開始寫的。我們這代作家有種揮之不去的抱負……哪怕不是在一部作品里寫完,也要分成幾部作品寫完。”在余華筆下,主人公林祥福從北方一路南下,執著地尋找一個叫“文城”的地方,展現了普通人在動蕩年代中的艱難選擇與生存,講述了一個人和他一生的尋找。
這部作品從構思到完成,用了整整二十一年的時間,不管是從內容、形式還是主題思想等方面看,都是余華創作的一種“綜合性”呈現。小說中的幾個主要人物的形象都帶著作者以前小說中的人物的影子:帶著女兒踏上路途的林祥福有著楊金彪、宋凡平般的樸實與謙卑,有時又帶給人們一種福貴的錯覺;在困頓中依然對外鄉人慷慨相助的陳永良夫婦與李月珍一家別無二致。在《文城》中還可以看到余華在各個時期的不同敘事風格:如《現實一種》《河邊的錯誤》等早期作品中的暴力與沖突,在《文城》的亂世中得到再現;《活著》《第七天》等作品中的溫情與暖意,在《文城》中得以延續,甚至成為全書的基調。在小說中,依然存在作家先前作品中頻繁出現的要素,但關于血性與反抗的重新書寫不失為余華對以往創作的一種超越與延伸。
二、現實與救贖:冷酷背后的溫情
余華用24萬字寫盡了世間的生離死別和求而不得,對人世現實進行零度展示一向是他擅長的,他從來都不吝于向讀者展示生活的殘忍與痛苦,在《文城》中,余華展示了各種各樣的現實:林祥福幼時喪父,后又被小美背叛欺騙;小美受盡婆婆為難,最后仍逃不過和離的命運;陳耀武在少年時就被土匪割去了一只耳朵,與林百家青澀的感情也無疾而終;整個溪鎮也一直匪禍不斷。
關于現實中的痛苦,《活著》描述的是沉默而平靜的忍受與吞咽;《第七天》則設置了“死無葬身之地”,選擇走向更渺茫的虛無;而在《文城》中,人們面對現實時擁有了一往無前的勇氣和拼死一搏的決絕。如果說《活著》只是為了活著而活著,那么《文城》描寫的正是“活著”之外的種種追求。余華選擇將故事設置在19世紀和20世紀交替時期,并安排了一系列天災人禍來形成一種情節張力,呈現出眾多人物生生死死的浮沉命運。難以被苦難抹去的是每個人身上閃爍的人性光芒——信義、情義、慈愛與堅韌。
《文城》是余華展示出的某種詩意,現實世界中的一切苦難、暴力、背叛都只是背景和襯托,作者真正想展現的,是他的詩意想象和生命原力,是苦難之后人性的救贖。余華早期的先鋒小說似乎是在刻意地展示這個世界不可理喻的非理性和人性的冷酷無情,但從《活著》開始,溫情的色彩越來越重,和解的意味也越來越濃,包括后來的《兄弟》《第七天》,余華都沒有離開這個基調。《文城》同樣如此,故事雖然以一場欺騙和傷害開始,但緊接著展開的卻是一場尋找與救贖。整個故事的核心依然是親情的缺失和補償,人性的寬和與包容,對一些人物的描寫甚至達到一種近乎“神”的意味。
余華在小說補篇中解釋了小美背叛林祥福的緣由,并在最后為小美設計了一個充滿象征意味的死亡場景,讓小美和阿強在漫天飛雪中完成了贖罪,得到救贖——當小美和阿強在雪地長跪不起,他們是否洗凈了身上的愧疚與歉意?這一場景正是作者在道德兩難的境遇下,不自覺流露出的寬容與悲憫。林祥福一直都在尋找的“文城”,又何嘗不是他在苦難中的慰藉與救贖。在這里,文城其實被寄予了一種烏托邦式的想象與向往,就像是《第七天》中的“死無葬身之地”一樣。“文城作為一個虛化的地名,承載著主人公的希望和信念”,而林祥福尋找它的過程也正是他獲得救贖的過程。還未踏入溪鎮時,一場龍卷風將林祥福與他襁褓中的女兒吹散,從以為失去女兒的痛苦絕望再到失而復得的滿心歡愉,在這大悲大喜中,他重新找到了生命的意義。在霞光里,他不是一個從災難里走來的人,而是一個滿心歡喜的父親,在那一刻,林祥福完成了對自己的救贖。
三、尋找與錯過:詩意的悲劇感
從《活著》到《第七天》,共存的一個基本主題就是“失去”,這一主題在《文城》中也依然得到保留,并延續了《第七天》中“尋找”的主題,只是從“尋父”變成了“尋母”。林祥福是一個北方人,由北入南,女主角紀小美則是南方人,由南向北,故事就從這一南一北的追尋中發生展開,所有的故事也都與“文城”有關。
林祥福認為與“文城”相似而選擇留下的溪鎮其實并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江南小鎮,他在初入小鎮時遇到的那場飛沙走石的狂風,還有后來整整持續了十八天的大雪,似乎更具有北方特色。小說最開始也不叫《文城》,而是叫《南方往事》,“文城”只是一個被虛構出來的地方,在現實中根本就不存在,但在小說中,“文城”又是無處不在的。它在想象和象征的層面提供了一個行動的方向,正是因為有了尋找文城的欲望,林祥福才開始了他向南方的“出門遠行”,才有了新的人生和故事,但隨著故事的展開,他實際上是一步步放棄了文城,最終踏上了歸途。
在整個故事中,“文城”的代指并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情節發展,其被作者賦予了三重不同意蘊:第一是林祥福一直執著尋找的小美的家鄉,這種不顧一切的尋找,明顯帶有一種理想主義色彩,“文城”在林祥福心中不只是一個追尋的目標,更是一個完整美好的家庭;第二是“信義”,是溪鎮兵民所守護的小鎮,雖然他們經歷了無數次的災荒兵亂,但是仍不愿離開自己的故鄉;第三是小美和阿強落腳的上海、北方、定川,在亂世中,他們所追求的自由和幸福只是一個虛無縹緲的幻境,阿強隨口說出的“文城”可能也曾是他心中的故鄉與遠方。對于余華而言,“家”始終是他創作的一個核心主題。他在一次訪談中曾提到:在他書寫人物命運的時候,“家”這個概念,始終盤踞在他腦海里最重要的位置。在《文城》中,“家”是易碎的,它會被龍卷風掀走,會被暴雪壓塌,會被土匪破壞,但“總會有一個地方叫文城”——在小說結尾處,余華寫下了這樣一句話,由此,“文城”從抽象變為具體,從地理名詞化作寓言空間,從想象落到現實之中。
余華在《文城》中把林祥福與小美的故事完全分開,并采用了補敘的方式將小美這條線索進行單獨敘述。林祥福尋找小美這一情節,曾一度淪為背景,溪鎮獨耳民團與土匪的生死斡旋逐漸成為中心情節,直到補篇,林祥福與小美的故事才重新被聚焦,在他們死后,這兩條故事線才真正合在一起。在城隍閣祭拜蒼天時,紀小美因雪凍而死,背負著對女兒的罪與愛迎接死亡,一直執著尋找的林祥福錯過了與自己咫尺之隔的女子。十七年后,裝著林祥福尸身的那副棺材與紀小美的墳塋在西山腳下擦肩而過。一個把他鄉活成了故鄉,一個把故鄉活成了他鄉,這兩個精心設計的巧合與錯過雖然有一些刻意之嫌,但仍在苦痛之中生發出無限的溫情與悲憫,具有強烈的浪漫主義色彩。
從《活著》到《文城》,主人公都在兢兢業業地按照正常的生活邏輯步步前行,但命運卻早已安排了結局。《文城》中的每一個人物都各有所求,但終其一生都求而不得。溫和與良善不能如愿以償:林祥福南下千里,苦苦追尋小美,卻得了個錯過一生的結局;田大一心等待主人回家,卻在接到書信后,亡故在接其歸家的途中;陳耀文與林百家青梅竹馬、兩相愛慕,卻礙于世俗禮道而天各一方。正是這種人與命運的沖突與掙扎帶來的一種洶涌澎湃的生命熱力,才能如此震撼并引起人們的強烈共鳴。
四、完滿與殘缺:小人物的“信義勇”
學者丁帆曾將長篇小說價值判斷的三個關鍵詞重新進行了調整,調整后的順序為“人性的、審美的和歷史的”,可見人性的重要性。價值觀是認知世界的前提,任何一個作家都會在他的創作中或直接或隱晦地表達出這一價值觀。在《文城》中,余華描寫了眾多形形色色的小人物,他們的肉體雖然有所殘缺,但卻展現出一種令人動容的,在亂世下的人性光輝。
溪鎮遭遇匪禍,前后被綁走了二十三個人,在這二十三個人里,除了唐大眼珠被槍殺,剩下的二十二個都因贖金送得不及時而被土匪割掉了一只耳朵,這些失去耳朵的人歷盡千辛萬苦回來后,卻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平衡感。其實丟失的外耳并不能使人失去平衡,讓人傾斜的實際上是劫難之后的惶恐與不安,被割掉的耳朵正象征著每個人在土匪手下所遭受的折辱與踐踏,不僅是肉體,更在于精神。這些獨耳人如何重新找回平衡的過程,正是他們如何找回自尊和生命價值的過程。
教書的王先生從土匪手中逃回溪鎮后,站在講臺上都會不自覺地左偏,后來,他在稚嫩的讀書聲中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尊嚴與風骨,走路教書都不會再左偏,仿佛被割掉的耳朵又重新長了出來。這是一種無法言說的新生與蛻變,雖然他在身體上仍是殘缺的,但是在精神上他又重新成為一個完滿的、真正的人。
還有徐鐵匠和其他十八位獨耳人,他們一同參加了顧益民組建的護衛民團,在面對窮兇極惡的土匪時,他們也曾害怕過,但這種恐懼很快就被仇恨所取代,每一個人都在浴血奮戰,直到全部壯烈犧牲,為整個故事增添了一份無法言說的悲壯。他們雖然是殘疾人,卻更加高大。
林祥福在表面上看,雖然是一個健全的人,但是實際上他也是一個“獨耳人”,他所丟失的是精神上的“外耳”——曾經的妻子小美。讓林祥福不顧一切去尋找小美的,或許不僅僅是出于一種情感,而是一個無法放下的執念。他不僅僅是在尋找一個人,也是在追尋一個問題的答案,在“她為什么離開”的偏執中傾斜了。小美的離開就像是外耳的缺失,是導致林祥福傾斜的不完滿,但其實真正導致其傾斜的,是林祥福自己的執念,這份執念最終在尋找的途中以及和陳永良夫婦的相處中逐漸消失散淡,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林祥福重新成為一個完滿的人。
在小說中,多次出現身體殘缺而精神完滿的人。擺船的曾萬福雖因戰時被流彈打斷手指,但也只有他愿意為帶槍贖人的林祥福擺渡。曾經作為土匪的“和尚”在與張一斧的決戰中被砍掉左臂,流著鮮血在雪地昂首而立,這個姿勢仿佛與古典小說中的英雄好漢的悲壯姿勢重合了,也正是在這個時候,他從一個滿手血腥的土匪真正成為一個有著“信義勇”的完人。“《文城》的所敘時間固然是百年前的……但因為有了這種對普遍人性的深刻描摹,它又直指當下的時刻,它并非固態靜止的歷史演義,而是以鏡像和幽靈的形式活在我們身邊的故事。”或許正是在這種矛盾中才展示出余華想要說的:健全者未必完滿,殘缺者未必遺憾,盈滿則虧,而殘缺卻有再次完滿的可能。
林祥福雖然失去了妻子,但卻得到了女兒、遇到了朋友、收獲了財富;顧益民失去了一個兒子、健康和家產,卻獲得了對“義”的全新理解和人生的新的感慨;土匪“和尚”失去了生命,卻獲得了人的尊嚴。現實和身體上的殘缺卻帶來精神與感情的完滿,這種矛盾的得失正是余華想為人們展現的生命原力。“還人性于江湖,成為小說主題的一種隱藏的重要內核。”《文城》充滿對人的追問,對命運的思考,展現了余華一直以來的創作追求——“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五、結語
余華在《文城》中描寫了兵荒馬亂中的民不聊生與愛恨情仇,展示了販夫走卒的赤膽精誠與人物命運的顛沛無常,而貫穿其中的正是作為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仁、義、禮、智、信。小說中深刻的苦難意識、無可改變的宿命力量以及充斥其中的血腥暴力都被愛與溫情所消解,使整部作品具有更廣闊的意蘊空間。“《文城》是我最接近完成、又最難完成的作品”,雖然《文城》仍存在這樣那樣的缺憾,但是余華仍為人們帶來一種新的思考與體驗。
參考文獻:
[1]丁帆.如詩如歌 如泣如訴的浪漫史詩——余華長篇小說《文城》讀札[J].小說評論,2021(02):4-14.
[2]洪治綱.尋找詩性的正義——論余華的《文城》[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1(07):66-78.
[3]孟覺之,胡小蘭.先鋒作家的“出城”記——從《文城》看余華創作的再轉型[J].南方文壇,2021(06):182-186.
[4]叢治辰.余華的異變或回歸——論《文城》的歷史思考與文學價值[J].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1(05):100-111.
(作者簡介:李依林,女,碩士研究生在讀,沈陽師范大學,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
(責任編輯 葛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