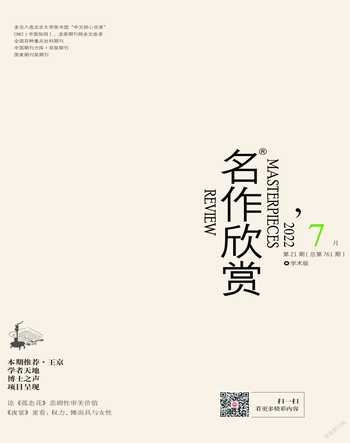“白蛇傳”故事中“白蛇”形象的歷史演變
楊會 冉寧
關鍵詞:“白蛇傳”故事 “白蛇”形象 多維演變
在故事類文體中,經典作品的流傳往往與作品所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有密切關系。如《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之杜十娘、《西游記》之孫悟空、《紅樓夢》之林黛玉等。在一定程度上,一個成功的人物形象可以成就一部文學作品或影視作品。這些人物形象構建了一個經典的形象譜系,存在于中國文學的人物畫廊中,“白蛇”形象是其中之一。
“白蛇傳”不僅是中國古代四大愛情悲劇之一,同時也是中國四大民間傳說之一,是為數不多的從古至今一直流傳較廣的民間故事。該故事由民間口頭傳說,逐漸定型為文本形態,逐步熒幕化,從而實現了從口頭到文本再到影音的演變過程。現代文學及影視記憶中的“白蛇”形象,往往與溫柔賢淑、賢惠能干、端莊大方等贊美之詞相聯系。魯迅對“白蛇”贊譽有加,在《論雷峰塔的倒掉》中抨擊了迫害白蛇娘娘的法海:“可有誰不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a縱觀“白蛇”形象的歷史演變發現,“白蛇”形象經歷了動態的過程,其形象并非一開始就呈現為“善”的特征。
“白蛇”形象最早見于唐傳奇《李黃》,“白蛇”化身為白衣女子出現在該作品中,成為后世“白蛇”形象的原型。“白蛇傳”故事雛形出現于話本小說《清平山堂話本》中的《西湖三塔記》,并且具備了一定的情節。發展至明清逐漸成熟定型,故事定型的標志性作品是馮夢龍《警世通言》中的《白娘子永鎮雷峰塔》。該版本在前期故事情節發展脈絡的基礎上,增添了借傘還傘、盜取官銀、白蛇現形、鎮壓塔底等故事情節。“白蛇”形象隨著“白蛇”故事的復雜化逐漸呈現出多元樣貌,同時受社會歷史背景的變化及媒介手段的影響,“白蛇”形象的演變呈現出階段化的特征。
一、唐宋時期“惡”的“神秘”本相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蛇通常是邪惡與淫蕩的化身,多以消極、負面形象示人。與蛇有關的成語、諺語有“佛口蛇心”“蛇蝎心腸”“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等,顯示了人類對蛇的畏懼和厭惡,而對蛇的此種認知正是“白蛇傳”故事中前期“白蛇”形象塑造的依據。在唐宋以前的文學作品中,蛇也大多以“惡”形象出現。《搜神記》記錄了一系列與蛇有關的故事,《李寄》篇中的蛇專吃女童,《壽光侯劾鬼》篇中的蛇精附身婦人危害身體等。至唐宋時期,“白蛇”形象成為“純粹的妖,是情欲和邪惡的化身”b。作者借“白蛇”這一“惡”本相來警醒世人,切勿貪圖美色,不要被外表的事物迷惑心智,典型作品有唐傳奇《李黃》和宋話本小說《西湖三塔記》。
《李黃》以李黃的視角引出“白蛇”,“因見白衣之姝,綽約有絕代之色”c,“白蛇”以美貌吸引了李黃的注意。盡管白娘子“前事李家,今身衣李之服”d,李黃仍主動求娶,卻不知白蛇在美麗的皮囊下,實則暗藏禍心。最后害得李黃雖然能說話,但是身體逐漸消失,只剩下了頭。李黃最終因貪圖美色,結局悲慘。
宋話本《西湖三塔記》中的“蛇”也是“惡”的形象。“綠云堆發,白雪凝膚。眼橫秋水之波,眉插春山之黛。”e“白蛇”以美色成功誘惑奚宣贊,等其成為“舊人”再取心肝。奚宣贊思歸,想回家看望老母親,“白蛇”聽后大怒:“鬼使那里?與我取心肝!”f白衣婦人數次要吃掉奚宣贊的心肝,但未得逞,奚宣贊最終也意識到白衣婦人是一個真正的“蛇蝎美人”。
唐宋時期“蛇形象”之所以呈現出邪惡的一面,主要在于蛇的“本相”帶給人的恐懼感。一般認為,蛇外貌丑陋,并具有強烈的攻擊性,常直接或間接地帶給人們不幸。“白蛇”形象的邪惡還與氏族社會的更替有關系,母系氏族社會賦予蛇以女性的身份,“女性”常與“神性”“生殖”“權力”等相聯系,并占據主導地位。進入父權社會,男女兩性的社會地位發生了變化,男性話語權占據主導地位,女性的話語地位逐漸喪失。女性話語地位的低下與蛇形象“惡”之文化內涵的確立有一定的關聯。
二、明清時期“善惡交織”的“世俗”形象
明清時期,《警世通言》中《白娘子永鎮雷峰塔》標志著“白蛇傳”故事發展到新階段。此階段的蛇形象充滿“鮮明的世俗社會生活氣息,形象更加美麗,性格愈加豐滿”g。“白蛇”開始向人的形象靠近,日常生活及心理等都越來越具有人的特征。此時期的“白蛇”
故事,情節設計更加完整,“白蛇”形象隨著故事的豐富而豐盈起來。
《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中“白蛇”脫去了早期的神秘色彩,成為世俗化的形象。“白蛇”與許仙(許宣)在斷橋相遇,“借傘還傘”的情節設計讓二人產生了交集,從而為二者情感的產生創造了條件。因白娘子贈銀,許仙招了官司,被發配到蘇州牢城營,白娘子不遠千里第一次尋夫;許仙到承天寺看佛會,因白娘子給其打扮的衣物再次招惹官司,再次被發配,白娘子又一次尋夫。“白蛇”兩次尋到許仙,而許仙惡語相向,但作為蛇的白娘子,不但沒有顯露蛇的本性吃掉許仙,反倒耐心解釋事情緣由。
《雷峰塔奇傳》中許仙因白珍娘連吃兩場官司,白珍娘兩次尋夫;許仙懷疑“白蛇”的身份,更是誘騙她喝下顯露原形的符水。當面對許仙的不信任,白珍娘非但沒有責怪許仙,反而略施巧計化解危機。作為蛇的白娘子,面對許仙的質疑,仍選擇和他在一起,且忠貞不渝。
明清時期“白蛇”形象的世俗化還體現在居住環境和飲食方面。《西湖三塔記》中只寫了“金釘朱戶,碧瓦盈檐。四邊紅粉泥墻,兩下雕欄玉砌”h,沒有詳細敘述室內環境。而《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中對“白蛇”的住所有詳盡描述:“四下排著十二把黑漆交椅,掛四幅名人山水古畫。”i居住環境的具體化使“白蛇”形象更具真實感。此外,吃食的世俗化,強化了“白蛇”
形象的“人性”特征,唐宋時期的“白蛇”更具有蛇本相的特點,生猛殘忍,直接剖開肚皮,吃“舊人”的心肝;而明清時期的“白蛇傳”故事中,“白蛇”的吃食已經由“舊人”心肝換成了人類日常飲食。衣食住行是人類生活賴以生存的基本需求,文本中對居所以及飲食的描寫明顯體現出“白蛇”形象的世俗化。
明清時期“白蛇”具有了“善”的品質,但同時又兼具“惡”的特征。她贈予許仙的銀子和衣物,都是通過盜竊的手段獲得;當許仙因這兩件事招惹官司,“白蛇”棄他而去;“白蛇”兩次尋到許仙,用謊言回應許仙的質疑;許仙找來捉蛇先生,“白蛇”露出本相威脅許仙:“你若和我好意,佛眼相看;若不好時,帶累一城百姓受苦,都死于非命。”j員外見“白蛇”美貌而心生淫意,“白蛇”露出兇相嚇退員外。
此一時期“白蛇”的“惡”程度較唐宋時期有所減輕。唐宋時期,奚宣贊沒有傷害白衣姝的實際行為,但白衣姝要剖他的心。而此時期許仙找來捉蛇先生、禪師來捉拿白娘子,但白娘子始終沒有“殺生害命”,即使最后復了原形,也只是昂頭看著許仙。蛇雖“惡”,但已具備“善”的某些品質。
《雷峰塔奇傳》中,“白蛇”有了明確的名字——白珍娘,她是青城山修行一千多年的蛇精。許仙進房“開帳看見一條白蛇,驚死在地”k,小青本想吃了他,白珍娘怒道:“既與官人結為夫婦,豈忍用此心腸。”l救活許仙后,設下巧計瞞過許仙。城內名醫得知許仙幫助知府夫人順利分娩雙胎,怒氣沖沖,想出“賽寶”的計謀算計他。白珍娘早已預料到此事,命小青偷來寶物,幫他解決難題,更是幫助許仙一起經營藥鋪。員外見白氏美貌超群,便和家仆商議占有白氏,但白氏始終對許仙忠貞不二。此時的白珍娘已經褪去蛇的妖性,不再具有蛇的惡、淫,儼然是人間賢淑的普通女子,成為丈夫眼中的賢妻。“白珍娘”為許仙誕下子嗣——文曲星許夢蛟,成為母親的角色,使得“白蛇”更加人性化。
明清時期,“白蛇傳”故事的發生地被固定在江南一帶,資本主義最早從這里開始萌芽。新的觀念、思潮開始萌發,對傳統的封建禮教造成一定的沖擊。市民階層與市民文化興起并發展,影響文人創作,由此導致《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中的“白蛇”形象呈現出世俗化的傾向。
三、當代社會及媒介語境下“向善”的形象轉變
“白蛇傳”故事經過不斷加工改編,白娘子的形象也由“惡”轉向“善”,由蛇妖變為蛇仙。“白蛇”形象發展至現當代時期,徹底脫去妖性,以人的形象出現在大眾視野中。“白蛇傳”故事以田漢先生的改動最為經典,他筆下的“白蛇”形象更加人性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戲劇創作領域也進行了相應的革新。田漢多次改編“白蛇傳”故事,以《白蛇傳》(1955)的影響力最大。田漢先生塑造的“白蛇”剔除了故事中的封建色彩,給“白蛇”增加“反抗”的性格特點。白素貞與法海的斗爭,正是妖與佛的對抗。“白蛇”雖為妖,卻行善,法海雖為人,卻為惡,二者形成鮮明對比,諷刺現實社會中人性的復雜。
在影視技術的支持下,20 世紀80 年代,經典文學作品的影視化成為潮流,《西游記》《紅樓夢》《三國演義》《聊齋志異》等作品的影視改編帶動了古典文學作品從文字到圖像的轉變。“白蛇傳”故事的傳播也由傳統的紙質文本逐漸走向影視化,通過影視進入大眾視野,“白蛇”形象以更加直觀生動的方式呈現在觀眾面前。如《新白娘子傳奇》(1992)中白素貞助許仙開藥鋪,治病救人;《白蛇傳》(2006)中白素貞替天行雨,拯救蒼生。她雖是蛇身,但毫無“惡”的特征,反而充滿了心懷百姓、心腸慈悲等“善”的特質。
此時期“白蛇”形象向“善”轉變的原因,首先是文藝作品要肩負的塑造正面形象的時代任務,加之田漢先生本人的浪漫化創作風格,使得“白蛇”形象具有正面的意義。二是影視化“白蛇傳”傳播效果的考量,使“白蛇”形象更多地彰顯出“善”的氣質。與紙質文本接受不同,影視傳播的受眾范圍更廣,且不受文化水平限制。影視是聲音與圖像、視覺與聽覺多方面的結合,更加具有感染力,因此,影視作品更加注重弘揚“正能量”。
四、女性主義視角下“復雜化”的形象
“白蛇”形象的演變過程伴隨著性別書寫,封建社會的“白蛇傳”故事,顯示出兩性關系不平衡的狀態。女性話語權的缺失,是造成女性形象妖魔化的原因之一。在部分文學作品或影視作品中,女性被建構為美麗、聰慧、妖嬈等形象,用文字或者鏡頭語言對女性的身體部位甚至是敏感部位進行描寫,這樣的語言模式讓女性處于一種男人看/ 女人被看的狀態。女性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盡管身處男權話語的包圍下,但隨著女性意識的不斷覺醒,更多的女性參與到女性運動中,女性形象發生了變化,女性越來越具備反抗性,作為女性身份的“白蛇”形象也發生了變化。
“白蛇”形象的轉變是“人們文化心理認知以及社會結構的變化”,“白蛇”為了愛情,勇于向以法海為代表的占主導地位的男權挑戰,體現了女性意識的覺醒以及女性地位的提高,傳統男性主導地位逐漸衰弱,這使得“白蛇”形象越來越“人性化”。法海將許仙關在金山寺,并拒絕白素貞放過許仙的請求,導致白素貞水漫金山,奮起反抗封建禮教。她具有強烈的反抗意識,不依附世俗倫理,勇于追求自己的愛情,突破了固有的傳統女性形象。
由徐克執導的電影《青蛇》改編自香港作家李碧華的同名小說《青蛇》。該小說與以往白素貞的視角敘事不同,以青蛇的視角去寫白素貞的故事。“《青蛇》不僅解構了男性敘事形式,使故事出現了性別差異,而且張揚了商業語境下的女性意識形態。”n作者用筆去探索人類內心深處的靈魂,建構出一個具有現代意識,卻是一個回歸傳統倫理道德的白素貞。《青蛇》則是顛覆了傳統的男性敘事文本,從女性視角出發的由女性創作的新故事。
作為民間傳說的經典,“白蛇傳”故事經歷了由雛形到定型的演繹,“白蛇”形象也隨之發生改變,唐宋文學中的白蛇被塑造為“惡”形象,其存在是為了警醒世家子弟切勿貪圖美色。“白蛇”形象于明清發展至定型,呈現出世俗化傾向,具備普通人的特質,表現出“善惡交織”的特征。至當代,“白蛇傳”故事超越了文本、戲曲形式,在新媒介技術的支持下,被改編成影視作品。影視化之后的“白蛇”受媒介效果等因素的影響,實現了由“惡”向“善”的轉變。此外,受女性主義思想的影響,“白蛇”形象也被賦予了新的思想內涵。由此可見,文學形象的塑造與社會語境具有密切的關系,同時也與媒介的嬗變相關。“白蛇”形象的呈現,反映了不同時代不同社會的價值觀念,還從側面體現出媒介的塑造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