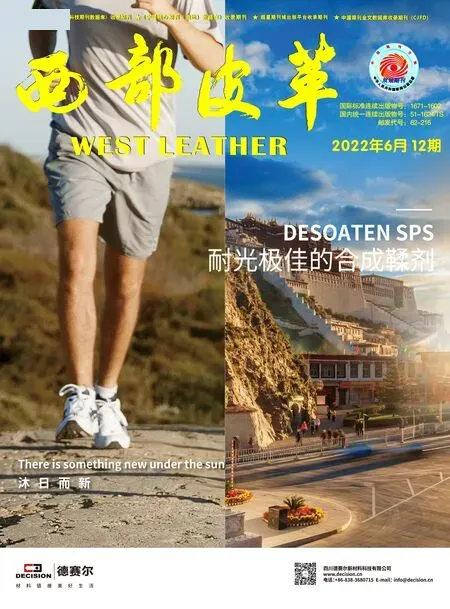五十年代女裝設計特點及其審美價值
羅渝慧
(蘇州大學,江蘇 蘇州 215100)
1 五十年代女性服裝的主要審美特點
20 世紀五十年代正是二戰剛剛結束以后,突破傳統的禁錮、追求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和人類的共同愿望,女性服裝在此背景下呈現出了與以往完全不同的格局,表現出了獨特的審美特點。
1.1 中國政治化服裝時尚達到頂峰
圖1 與圖2 中的“列寧裝”“布拉吉”是該時期中國女裝的典型代表。20 世紀五十年代,體現“布爾什維克”精神的“列寧裝”從蘇聯傳到中國。由于“列寧裝”等同于新中國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念,符合國家的崇儉理念和革命精神,迅速在中國流行。“列寧裝”在蘇聯是男士的著裝,傳入中國后卻受到女性的追捧。大掩襟、大翻領、雙排扣并束有腰帶的裝束在體現女性的身體線條時,更顯得精干大方,不僅具有獨特的美感,更是革命精神與思想進步的象征。蘇聯領導人來華訪問之后,在政府部門的倡導下,“布拉吉”連衣裙也得到中國女性的認可,迅速流行起來。“布拉吉”的迅疾流行始于中蘇兩國在政治層面的親密合作交流[1]。更重要的是,“布拉吉”連衣裙款式簡潔大方、便捷輕巧、節省布料、變化豐富,適合各個年齡階段的女性穿著。
此時的中國女性飽含對革命追求、社會主義熱愛的感情,在審美取向上趨于一致。“列寧裝”與“布拉吉”連衣裙兩款女性服裝相繼流行,經濟實用的同時又美觀大方,不僅滿足了當時中國女性的美感追求,更彰顯出了時代所賦予的特殊政治意涵,展示出社會主義建設者女性的美麗健康新風貌。
1.2 西方對女性魅力的極致追求
二戰結束后西方國家的人們精神面貌多是萎靡不振的,但內心依舊保留對美的渴望。到五十年代,西方女裝設計呈現出了對浪漫優雅的女性魅力的極致追求。
五十年代中后期,隨著西方女性社會地位的變化,女性開始擺脫社會與家庭的束縛,展現其自身的優雅形象和獨有的藝術風格。這一時期的西方女裝主要分為日裝和晚裝,晚裝主要是束腰造型,而日裝則采用束腰與大廓形的造型,其中裙裝與套裝多為束腰修身造型,外套則多偏向大廓形的造型。可以看到這一時期的女裝在廓型上有著明顯的特點,造型張弛有度,其可謂是廓型的時代,也是女性的身體被修飾得極為優雅的時代。從具體來看,迪奧的設計在這一時期占有極為重要的位置,其設計出的女裝內部結構線條簡潔利落,形成優雅舒展的線條關系,“花冠形”“郁金香形”“Y 形”“紡錘形”……每一個樣式無論從整體還是內部結構來看都具有相當獨特的風格,同時保留住了優雅的女性之美。如圖3、圖4,從整體來看,這一時期的女裝大多圍繞腰部的松量進行變化,借鑒19 世紀維多利亞、愛德華時期的精湛復雜的構造技巧,強化女性豐胸圓臀、窄腰柔肩的外形特點,形成簡潔但不簡單的輪廓造型,從而形成高雅低調的性感形象,唯美浪漫中帶有理智,尋回了女性特有的優雅氣質。
盡管二戰期間的動蕩不安和布料缺乏給西方女裝設計帶來了致命打擊,但隨著戰爭的結束,樸素實用主義很快向浪漫優雅風格轉變。這種對女性魅力的極致追求滿足了戰后西方女性對美麗優雅形象的需求。
2 五十年代女性服裝的審美價值
《設計美學》中這樣解釋設計審美:設計審美既是物質活動又是精神活動,以“人與物的和諧關系”為中心[2]。就服裝設計而言,審美價值就在于人與物——身體與服裝的和諧關系之中。服飾是人們思想的表達方式,而且常常和更深層次的道德或者社會價值的根本變化密切相關[3]。盡管中西方五十年代的女裝設計與流行上有著顯著的區別,尤其是在形式表現上呈現出完全不一樣的狀態,但深究其中,從這些“物”的形象上面可以發掘出共通的“精神”的意象來,從而體會五十年代女裝的審美價值內核。
2.1 對和平與發展的精神追求
五十年代時二戰剛剛結束,整個世界還處于百廢待興的階段,深受戰爭荼毒的世界人民對和平與發展的渴望前所未有的強烈。西方女裝對女性魅力的極致追求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是比較奢侈的,并且受到了一部分民眾的抵制。因為那些大廓形的充滿女人味的款式造型需要用到非常之多的布料,一套晚裝甚至會用掉二十幾米的布料。但戰后的女性亟須這樣一種可以擺脫戰爭陰霾,和平時期才能有的悠然華美的姿態與形象。正是源于她們內心深處的這種渴望,超越當時社會經濟所支持的這種奢侈化設計才受到法國女性乃至世界女性的追捧。而處在新中國建立之初的中國女性們,飽含革命熱情,對國家發展與社會主義發展充滿激情。這一時期,服飾穿戴是展示社會主義社會優越性的形式,是人民群眾精神面貌的體現[4]。她們將這種和平發展的理想完全融入服裝中,繼而形成了當時時代典型的服裝產物。
2.2 新時代對突破傳統的渴求
二戰結束后,世界開始向全新的時代邁進,社會面貌日新月異,五十年代處于一個承上啟下的階段,交雜著多元的交融設計,人們希望突破傳統,開始了傳統復古與創新前衛的碰撞。正如前文提到,這時的西方女裝常常借鑒19 世紀維多利亞、愛德華時期的構造技巧,但在材質、廓形、剪裁、結構等多個設計與工藝方面推陳出新,設計制作出來的服飾更加實用舒適。比如廓形在五十年代之后的演變和應用常以“古典元素+現代裝飾”的形式呈現[5]。而此時的中國女裝對傳統的突破更加劇烈。在民國時期,外來文化已對中國傳統文化形成沖擊,傳統的中式服裝、西化的中式服裝與純粹的西式服裝在中國交替并行。到五十年代,在中蘇兩國友誼的影響與國家政策的號召之下,蘇式服裝在中國代表著新時代進步思想,當時的女性為了追求這種進步象征,認可并追捧起“列寧裝”“布拉吉”這樣的蘇式服裝。
2.3 女性主義思想觀念的表現
女性主義來源自西方國家,最早的時候是出現在法國[6]。二戰期間女兵的出現挑戰了西方女人不能穿褲子的傳統,為戰后女性服裝的解放奠定了基礎、創造了條件。受女性主義的影響,女性開始通過服裝來表達自身的想法,尤其是在五十年代中后期,女性主義的思想觀念在服裝的表現上形成重要的審美因素。在西方,“New look”“緊身胸衣”“風衣外套”……這些服裝都蘊含著女性主義思想觀念。一直到六十年代“吸煙裝”的出現,女性對服裝的選擇從附屬男性審美到表達自我魅力的轉變。在中國,毛澤東于1955 年提出“婦女頂半邊天”,尤其是到“大躍進”時期,中國婦女就業迎來第二高峰期,中國的女性主義思想開始了“本土化”發展。“布拉吉”連衣裙的審美風尚承接“花衣運動”之路,即美觀是女性著衣的第一要素,凸顯了女性強烈的社會性別表征。通過服裝時尚的變革,滿足了女性對表達自我表達美麗的訴求,從中可以看到中國女性在那個時代為自由與獨立的努力。
3 影響五十年代女裝審美價值的時代因素
在審美價值形成的過程中,不同時代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都是影響因素,五十年代女裝所呈現出的特點深受當時時代性的各因素影響,并形成了特殊的審美價值。
3.1 經濟影響與政治影響
在不同的社會階段,經濟因素可以在一定條件內決定或影響服裝審美風格與審美變化[7]。正如唯物主義歷史觀所指,經濟基礎決定意識形態,審美意識形態也受到物質生活水平與科技水平會的制約和引導。同時,人們對服裝的審美觀還會受到政治變動與社會變革的影響,尤其是在一些特殊時期,政府可以通過賦予服裝特別的思想以達到其思想統治的政治目的。就五十年代女性而言,剛剛經歷了世界戰爭,百廢待興,經濟和政治自然成為重要的影響因素。中國剛剛開始建設發展,物質資源較匱乏,但在政府推動以及中蘇政治交往的影響下,崇儉而極具政治化的服裝成為必然產物。各西方國家在經歷了戰爭的破壞后,普遍進行了經濟的調整與轉軌,政治上相對比較穩定,和平與發展的政治要求為女裝進行變革與創新提供了必要條件。可以說,當時時代的經濟因素決定了設計的可能性,而政治因素又起到了極大地推進或限制作用。
3.2 文化影響與社會影響
文化與社會的影響是潛在的、更為深刻與不可缺少的影響因素。審美意識不僅受到政治經濟的制約,特定時代形成的文化氛圍對審美意識的形成和發展變化起著很大的作用[8]。同時,設計本身是一種人類的社會行為,美的根源也來自社會實踐。那么,“審美”這種人類行為既具有“人文性”,也具有“社會性”[9]。二戰后五十年代的西方文化強調個人價值、民主自由,同時女性主義思想正在醞釀發酵,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強調女性本身美好的服裝設計趨向誕生了。而由于“道家”思想的影響,中國傳統文化中對服裝的審美觀點傾向于精神之美,是一種非具象的、寫意的美,所以在五十年代女性們會把自己在精神上的革命熱情移植到服裝上,形成一種高度滿足精神需要的審美價值。而社會是生物與環境的總和,它包括了政治、經濟、文化,但不僅限如此,還涵蓋了人類的生產、消費、教育、生存環境等等各種因素,帶給設計的影響是更復雜的。五十年代之時,正是隨著女性的社會地位逐漸提高,其特有的魅力與力量在各個方面被探索。女性的文化、政治、社會身份在一定程度上通過時尚的變革開始被重新塑造,從而形成了當時的女裝風格特點。
4 結語
在五十年代這個特殊的時代,中國政治化服裝時尚達到了頂峰、西方對女性魅力的追求也近乎極致,呈現出對和平發展、突破傳統、女性主義的時代審美價值。如今,我們處于一個嶄新多元、瞬息萬變的時期,當下的時代審美價值是我們作為設計學者需要共同思考的問題。世界正在發生著巨變,人類的各種意識形態、價值理念激烈交鋒,各種矛盾復雜化、沖突多樣化。情感的淡漠、精神的焦慮、人文的斷層等關于人類本身的問題相繼出現,環境污染、資源浪費等社會問題還需要長久的應對。市場為重的設計價值取向在不斷割裂人與自然與生俱來的聯系,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我們需要找尋一個歷史與文化與可持續發展相統一的切入點——歷史與文化傳統、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自己的本性成為了設計的新價值。因此,關于人文的、人道的、人性的設計是我們這個時代需要的:將設計的審美著眼于歷史文脈的傳承、傳統文化的宣揚、人情的關懷和大自然的保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