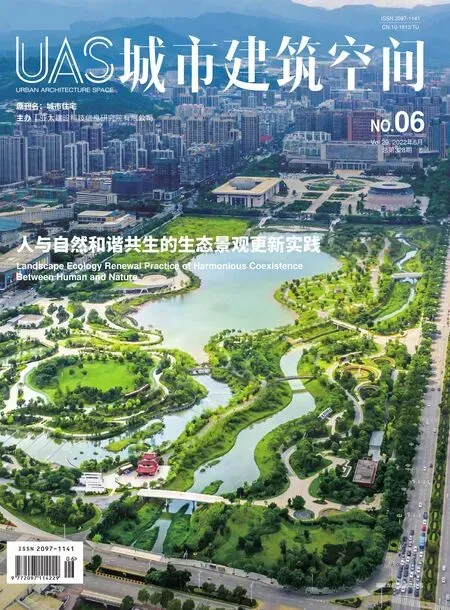場景視角下智慧城市場景構建策略研究
張淏楠,曲 葳,王飛飛,張劉引
(北京清華同衡規劃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100085)
1 場景逐步成為智慧城市發展新視角
1.1 智慧城市發展基礎與現狀
智慧城市概念最早源于2008年IBM提出的“智慧地球”愿景,同年,IBM相繼與我國多個省市簽署了智慧城市共建協議。2010年,工信部開展首批智慧城市試點建設工作,標志著我國智慧城市建設的大幕徐徐拉開。截至2020年4月,全國啟動的智慧城市試點城市已達749個[1],并呈現試點數量大、種類多、分布范圍廣泛等特點[2]。同時,通過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來應對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也為智慧城市建設帶來難得的發展契機,助推智慧城市建設進入快車道。
我國在智慧城市建設領域投入大量資源,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建設過程中仍遭到質疑,尤其是我國智慧城市建設主流現狀是脫胎于政務信息化建設[3],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以系統建設為主導的思維慣性,形成以技術驅動、產品導向為主導的智慧城市建設模式。各類智慧城市建設廠商以行業分類,將智慧城市劃分為類似智慧政務、智慧交通等若干類垂直領域系統。隨著行業領域細分,將各類“垂直系統”集成為智慧城市發展的新趨勢。由于各系統服務對象不同,建設目標也各有側重,因此當這些獨立建設的系統遇到復雜的城市運轉時,便有些力不從心。智慧城市建設者需從城市運行發展規律出發,針對各類活動參與者、行為活動運行邏輯等層面進行綜合分析,明確智慧城市建設方案。
1.2 智慧城市建設中的場景設計
近幾年,智慧城市中打造場景應用逐漸走入人們視野,而場景營造的技術邏輯與人居環境科學是非常相似的,通過利用創新技術手段與多學科融合的知識方法,來滿足市民的良好體驗,打造優秀的空間品質,這將成為推動智慧城市落地實施的重要手段之一。
但是目前在智慧城市建設中,場景思維在產品設計的研究上主要集中在需求分析、產品體驗和產品設計階段,通過智能產品實現萬物互聯,而場景所具備的傳播屬性、文化屬性往往被忽略[4]。場景不僅是輔助設計人員挖掘用戶潛在需求的手段,而且是指導智慧城市建設的主要抓手,逐步由智慧化產品向智慧化場景的轉變。智慧城市建設中如何真正體現場景感,將是未來的重要課題和研究趨勢。
2 場景理論研究
2.1 場景理論基本概念
“場景”一詞的含義最初是指電影中通過演員、對白、場地、道具、音樂、服裝等要素為觀眾傳遞信息和感覺。芝加哥學派場景理論的提出,在當時是一種新型城市研究范式,是對城市空間和社會空間的全面研究[5]。場景理論的興起以后工業社會為背景,城市形態開始由生產型向消費型轉變,對城市空間的研究將從自然與社會屬性層面,拓展到區域文化消費實踐層面[6],將文化價值因素納入城市研究范圍,以推動城市發展。
2.2 場景要素研究
雖然強調個體行為的文化與價值訴求是場景理論的出發點,但一般來說,場景的構成要素仍然建立在客觀和主觀兩大要素體系上[7]。客觀上包含社區、物質結構、人群和活動設施等;而主觀上則包括意義和價值、公共性及政治。
根據芝加哥學派的研究,場景包括5個要素:①鄰里,社區;②物質結構,城市基礎設施;③多樣性人群,如種族、階級、性別和教育情況等;④活動組合;⑤場景中所孕育的文化價值[8]。在具體的場景分析中,有學者將其合并為3個要素,即文化設施、活動組織以及文化實踐[9]。另有一些研究將場景進一步細化,強調場景包括實踐、地點、場合、情感等特定元素[10]。還有研究認為,場景是基于空間、時間和內容三要素構建的特定組合及其響應的潛在設施、情感聯系方式、價值觀屬性等[11]。無論場景如何劃分,場景中各要素有必然聯系。
3 基于場景理論的智慧城市場景體系
3.1 智慧城市背景下場景要素轉譯
從場景理論視角來看,客觀結構與主觀認識是有機統一的關系,將場景理論運用在智慧城市建設中,將物質設施建設與智慧城市參與人群的行為方式緊密結合,并將人群主觀感受介入場景設計,構建全新的要素構成體系,推動以人為本的智慧城市建設。
以芝加哥學派場景理論的研究為基礎,從場景構成要素“鄰里社區;物質結構、城市基礎設施;多樣性人群;活動組合;文化價值”5個維度入手分析,可以抽象為空間、設施、人群、活動以及文化價值,構成平時人們所理解的場景語句,即“什么人在什么地方,通過什么支撐,做了什么事,有什么影響”(見圖1)。

圖1 場景語句下的場景要素(圖片來源:作者自繪)
為找到智慧城市場景營造的具體方向,在智慧城市背景下將場景要素轉譯成“用戶、智慧應用活動、城市虛擬空間、城市物質空間、基礎設施、智慧城市價值觀”。根據當前智慧城市建設的實踐規律,以網絡連接、智能感知、數據中心為代表的ICT技術一直以來扮演著主要角色。參照GB/T 34678—2017《智慧城市技術參考模型》,以ICT技術為視角,圍繞“物聯感知層、網絡通信層、計算與存儲層、數據及服務融合層、智慧應用層”5個層次,結合場景理論,提出智慧城市子場景,最終提出智慧場景“人物角色、空間環境、行為關系、價值政策、數據”5類要素(見圖 2,3)。

圖2 場景要素向智慧城市場景要素轉譯(圖片來源:作者自繪)

圖3 智慧城市場景要素與子場景的關系(圖片來源:作者自繪)
3.2 智慧城市場景要素
1)人物角色 智慧城市場景如何營造的核心取決于人群,人群需求的多樣性塑造城市發展的愿景。在智慧城市場景營造中,需以人為中心對場景進行統籌考慮。一方面參與者為智慧城市建設的公眾、企業、政府等利益相關者,是智慧城市的需求主體,只有站在不同相關者的立場上思考并解決他們的問題,才能使智慧城市場景構建有的放矢;另一方面,在智慧城市時代背景下,人物角色的復雜性逐步凸顯,隨著先進信息技術的接入,場景之間可以隨時切換融合,導致場景中人物角色更加復雜多變。比如隨著即時通信技術的發展,線上會議場景中的參與者可能正扮演其他角色,他可能是一位辦公室白領,或是出租車乘客,甚至可能是居家照顧孩子的奶爸。因此,智慧城市場景中對人物角色要素的界定難度將會大大提高。目前可實現的方式是盡可能捕捉在不同場景下的人物與角色信息,生成用戶大數據,通過數據挖掘分析,呈現一個無限逼近真實角色的人物畫像。
2)行為關系 行為關系是智慧城市場景的核心要素。通過挖掘場景中人物行為模式與社會規律,梳理組成支撐智慧場景的業務(行為)序列,實現各類智慧化功能模塊。對行為關系挖掘得越深入,功能模塊就越貼合實際使用需求。以“無人超市”為例,在“無人超市”中購物這種行為并不等于刷臉支付。需圍繞在無人超市中與其發生的行為展開分析,挖掘顧客在期望便捷的購物體驗之余所需得到的更多信息;運營商則需要實時監控超市運行、設備以及安全狀態等需求。通過深入挖掘行為關系,構建內容豐富的智慧城市場景。
3)空間環境 空間與環境是場景最重要的構成要素,是場景中事件發生的物理載體。在智慧城市場景規劃設計中,一方面需要考慮空間環境中所承載的智能終端設備、網絡通信設施等智慧設施,支撐場景中數據的收集、處理分發以及人機交互等。另一方面,隨著互聯網技術對生活的高度入侵,人們的日常生活變得碎片化,從而消融很多功能空間,促使智慧城市場景空間環境要素不斷向“彼處”多個不同的空間延伸,這意味著智慧城市場景中的空間載體將呈現分布式、多元化等特征。
4)數據 相較場景理論,數據是智慧城市場景要素的新成員,是推動智慧城市建設最關鍵的部分,數據信息的流動交互串聯起場景的各類要素。一般情況下,智慧城市場景的數據要素多是復雜的多源異構數據集合,但可以從技術與實踐層面進行劃分。技術層面的數據包含對客觀世界的數據化,包括孿生空間模型數據、相關設施數據等;而實踐層面的數據包括行為參與者信息、活動行為數據、情感變化數據等,兩類數據共同支撐智慧城市場景運轉。
5)價值政策 價值政策要素在智慧場景中體現以人為本的價值觀,一方面指導智慧城市場景將實現哪些功能,以期實現智慧城市帶來的社會幸福感、歸屬感和城市認同感;另一方面,在智慧城市場景中體現以人為本的價值觀,也需要政策(法規)的約束或指引,對在建設智慧城市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數字鴻溝”“數據安全”等問題進行規避。
4 智慧城市場景構建策略
4.1 以空間為場景構建的基礎,促進技術融入城市發展
基于場景理論視角,智慧城市可作為在某一地點由智能設施或系統所構成實踐空間,運用科技影響城市持續運轉的日常活動,因此,構建智慧城市場景首要考慮其所發生的空間環境[12]。一方面,作為場景發生的基礎載體,必須充分考慮智能設施布局對空間帶來的影響,統籌謀劃在滿足場景運行的同時對空間高效利用,提出智慧城市場景構建過程中空間資源定量分配方案與信息工程實施環境的規范化要求。另一方面,強化與交通、環境、管線等領域在實體城市建設的相互協調性,組建物理建筑工程設計與智能化設計團隊的協同攻關,將城市空間設計與智慧場景設計深度耦合,促進智慧城市場景構建服務于日常生活,覆蓋城市的方方面面。
4.2 以數據為場景構建的關鍵,驅動智慧城市科學建設
區別于傳統場景理論的要素構成,智慧城市場景中新增加數據這一核心要素,突出了智慧城市場景在數字孿生、物聯網等新技術的介入下,場景本身成為“虛實融合”的復合場景這一特性。通過數據將現實世界和數字世界關聯互動,為觀察和預測城市微觀精細尺度下的人類行為提供了新思路。構建智慧城市場景的關鍵在于研究場景表征背后的數據體系,包括數據感知與采集、數據統一規范的處理方式及數據算法模型等,從而以數據驅動實現智慧城市場景需求挖掘、行為量化和場景精準再現。通過海量場景下大數據信息的累積、樣本修正和交叉驗證,更準確地揭示事件運行規律[13],將技術層面的數據模型體系和實踐層面的人類活動行為高效銜接,賦予智慧城市建設內生活力,為智慧城市發展尋找科學理論與實踐支撐。
4.3 以制度為場景構建的保障,賦能智慧城市落地實施
長期以來,智慧城市積極倡導以人為本的核心理念,強調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城市認同感,智慧城市場景要素中的“價值政策”正契合了這一理念。而在構建智慧城市場景過程中如何創造實際價值,除了對需求的深度挖掘以外,還離不開對制度、規則的制定。創新技術在融入城市并產生影響的過程中有其特定規律和路徑,為了將智能技術融合城市發展,需要構建容忍犯錯的研發和創新的制度環境,技術實踐的同時挑戰原有的制度框架,從而形成一套更加有效的社會問題解決機制與體系[14]。正是這一機制體系的不斷迭代,推動智慧城市場景的不斷更新,逐步實現科技與城市發展在流程、需求、價值、成效等維度的匹配,激活信息技術在城市規劃、建設、運行中的效用和優勢,規范場景中文化價值回歸社會公共價值和人本定位,從而真正實現智慧城市建設的終極目標。
5 結語
智慧城市作為推動數字中國、實現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抓手,是新時代背景下城市發展的主要方向。本文從場景理論出發,通過對場景概念、構成要素、構建策略的研究,以新的視角重新審視信息技術如何嵌入城市發展,探尋智慧城市建設新思路,強調智慧化建設既要體現在交通、產業、醫療等重要資源科學調配的宏觀層面,也要體現在“不停車收費”“無人超市”等微觀單元。未來將從場景視角出發研究其背后的業務流程、數據邏輯、智能產品組合等,深入思考智慧城市落地實施中存在的難題并提出對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