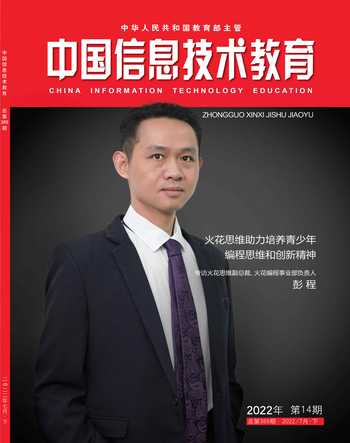從網絡到計算的轉型:教育數字化與集成創新
魏忠
今天,我們通過三場爭論,從科學、工程和經濟角度看待信息、數字和教育數字化的趨勢。
第一場爭論發生在1967年。在1956年背叛了諾貝爾獎獲得者晶體管效應的發明人肖克利的8位“叛徒”,再一次選擇背叛。他們這次背叛,是與大股東發生了一次重大的分歧:大股東認為賣晶體管能夠讓公司賺很多錢,而8位“叛徒”中的摩爾預測,如果把所有的晶體管放進一個板子里,不再考慮不同的應用,制造的成本會指數級下降,而維修成本卻符合邊際成本遞增原理。因此,8位科學家決定去做集成電路。今天我們聽得到名字的世界500強中的IT公司,幾乎都是這場爭論的各種繁衍。
第二場爭論發生在2015年。中南大學教授張堯學獲得了2014年度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這場爭論的焦點在于透明計算是不是真的。張教授的透明計算說的是一種用戶無需感知計算機操作系統、中間件、應用程序和通信網絡的具體所在,只需根據自己的需求,通過網絡從所使用的各種終端設備(包括固定、移動以及家庭中的各類終端設備)中選擇并使用相應服務的計算模式。而這種計算模式,如同集成電路一樣,如果能夠解決,那么從本質上,限制和影響信息孤島的成本問題會像摩爾定律一樣得到指數級緩解。
第三場爭論發生在2022年。馬斯克的星鏈被北京郵電大學的呂廷杰的一頓評論沖上了熱搜:“馬斯克一定不懂通信技術,因為在空天互聯網里邊沒有任何通信技術的創新。”這里不討論“通信技術的創新的概念本體”,從前面兩個案例中我們可以得到啟示,那就是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馬斯克為什么“沒有技術創新”的東西,如同集成電路一樣,會造成一場產業革命,而背后的“元認知”到底是什么。
集成電路領域的科學家之所以能獲得如此多的諾貝爾獎,其原因除了科學創新和技術創新的概念之爭,還在于他們在集成平臺下按照新的模型和規律(摩爾定律)大規模顛覆了創新的模式,這也是馬斯克“創新元認知”能在不同領域成功的原因。
讓我們再來看今天教育數字化應用所面臨的難題。教育的不同用戶關心的問題也不一樣,如師生用戶關心的是教學和科研,管理和服務用戶關心的是管理與服務,物流和生態科研關心的是學校系統與外界的物質能量交換。上述三類用戶可以用師生用戶前臺、管理服務中臺、開發開放后臺這三個平臺來定義和歸類。過去每個應用如同晶體管和集成插線板一樣需要去維護和定制,并且糾纏于角色權限問題,而如果分拆成三個平臺,每個平臺具備完全全息的應用,如同集成電路一樣用到哪個調用哪個,則不存在那樣的問題,這就是集成電路的思路。
張堯學教授所代表的“透明計算”思路給了面向數字化時代的一種想象,那就是把三網透明化,通過標準的不可篡改的內在規律封裝化,提供統一的調用,那么三網就不成為三網,而應集中在三網應該關心的從集成化到數字化為業務領域元認知提供的計算環境和基礎架構問題——云計算、邊緣計算、場景計算。依托這種架構的轉型,我們今后不再關心三網的效率與技術,而更應該關心三計算的教育核心,通過這樣的轉型,教師作用更大,平臺也更強大,在技術的支撐下,真正的教育變革才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