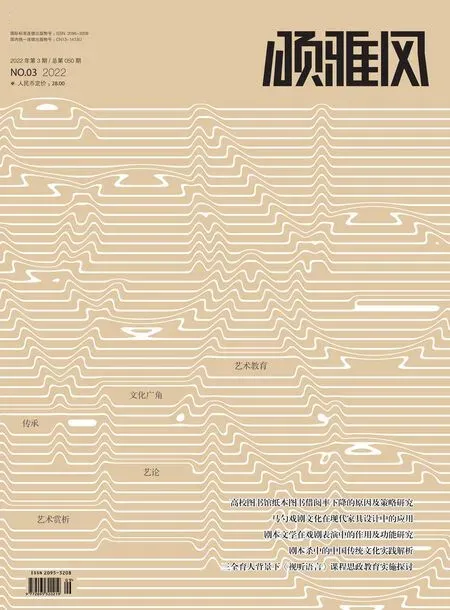淺析“六法”論在唐代仕女畫中的運用
◎劉泉
“六法”是早在六朝時期謝赫在《畫品》中提出的,對魏晉以來27位畫家的繪畫作品進行評論,并對繪畫功能、藝術作品的優劣、要求做出了理論依據,指出:“……雖畫有六法,……一氣韻生動是也,二骨法用筆是也,三應物象形是也,四隨類賦彩是也,五經營位置是也,六傳移模寫是也。” 所謂“氣韻生動”要求畫家在落筆作畫之前要做到胸有成竹,對整體畫面的把控氣韻貫通、生動靈活。“骨法用筆”要求畫家在作畫時用筆力道上要穩、準、狠,線條質量優良。“隨類賦彩”是說中國畫中的用色標準,按每類物象來處理色調,按季節處理物象的色彩。“經營位置”是說畫面的構圖。“傳移模寫”是指作品的臨摹。“六法”成為當時畫家判斷繪畫作品優劣的理論依據和判定標準。本文試圖以“六法”論為出發點,來認識唐代仕女畫的發展。
一、盛唐仕女畫的背景與發展
盛唐仕女畫發展源于新石器時期彩陶工藝的發展,陶畫、巖畫、地畫、帛畫中人物畫的發展,以及漢代畫像石、畫像磚中人物畫的出現為唐代人物畫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呈現的繪畫構圖形式也是以此類形式為主。在這一時期的繪畫藝術得到了自由的發展,人物畫的表現中,張僧繇的“疏體”與陸探微、顧愷之的“密體”等畫家均以自己繪畫風格的獨特面貌流傳后世。
唐代是一個開放型的社會,隨著盛唐時期軍事、國力的強大,政治的穩定,經濟的富足,唐代文化高度自信,中外經濟文化互通交流頻繁,使得繪畫領域得到快速的發展和成熟。人物繪畫中的工筆仕女畫逐漸形成自己獨立的藝術面貌,盛唐時期以女性文化為創作題材的繪畫作品繼承了前輩們的繪畫藝術技法,并融合當時社會的時代特征,具有獨特的繪畫風格面貌。
唐代畫家隊伍不斷壯大,為仕女畫的發展提供重要社會因素。繪畫隨著社會的發展,從創作題材上由最初為政教服務呈現的功臣像、道釋圖發展到描繪貼近現實生活的仕女畫,逐漸由繪畫的功能性轉換為增加繪畫的審美意趣而創作作品。有文獻記載的唐代仕女畫家的32名畫家中,其大部分畫家在官場中就職,使其更容易了解貴族女性的生活狀態,從而自由呈現仕女題材的藝術作品。
隨著盛唐時期社會收藏之風的盛行,在繪畫藝術的形成上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促進了仕女畫風貌的形成。宮廷畫師們的繪畫創作受到當朝統治者喜好的影響,在仕女畫作品中多以宮廷貴族中女性為對象,常反映其精致的妝容、豐韻的身姿、優雅的體態,如:晚唐時期周昉的《簪花仕女圖》,描繪的是五位貴族仕女與一名侍女在春暖花開的時節游園賞花的情景。畫家把幾位仕女的樣貌描繪得蛾眉如煙,發鬢高聳,首飾佩戴精巧,身著如蟬翼般輕柔單薄的帛衣,舉止文雅端莊,神采奕奕。畫作最右面的仕女頭戴折枝花,身著朱色長裙,側身右傾,手持拿拂塵逗左下腳邊的小狗,慵懶的雙眼望著那只寵物狗,小狗吐著舌頭,尾巴歡快地搖動,一幅憨態可掬的樣子。接著右面第二個仕女,身著朱砂色抹胸和拖地長裙,披輕薄微透的絲制外衣,手指輕輕撩起外衣的領口,神態怡然自得。為避免人物姿態的單調,畫家將仕女的另一只手向前微抬,此時人物的形態更顯靈活生動了。接下來再往畫面的左邊是一主一仆,畫家把主要表現的人物在比例關系上故意畫得很大,來突出主人的高貴,主人的發鬢中插一支盛開的荷花,身披白色絲制紗衣,一只手掌心向上,指節微曲,作輕輕拈花姿態,神情虔誠。身后的侍女衣著較樸素,姿態慵懶,或許是疲憊,將長扇倚在肩上。這位仕女身形較小,從她衣著打扮,人物姿態來看,應該也是一位貴人。畫家在這里做了遠近透視的處理。畫中女子裹著朱紅色的紗衣,雙手垂放在腹前,一副端莊高貴的神態。畫面最左邊的一組人物中是以一大一小表現形式來描繪人物遠近關系的,近處的仕女發髻高聳,頭戴芙蓉花,身著繪有鴛鴦圖案的抹胸拖地長裙,她的眉宇中略帶笑意,右手手持一只白色蝴蝶,微翹起蘭花指,身子微微向右傾斜,回眸看向跑過來的小狗,這與最右邊逗狗的仕女相互呼應,使畫面完整又富有韻律美。畫作《簪花仕女圖》取材于宮中婦女的日常生活,從仕女臉上的妝容、穿戴、身姿和臉上的表情可以看出盛唐時期經濟的富足、國力的強盛,而這一題材的繪畫作品受到當時統治者的喜愛,成為影響仕女畫發展的又一重要因素。
二、“六法論”在唐代仕女畫中的體現
“六法”之說自南齊謝赫在《畫品》中提出后,伴隨著魏晉南北朝時期民族大遷徙和民族融合的發展,文化逐漸興盛,儒家正統思想正在走下神壇,老莊玄學在士大夫中逐漸流行,加之佛教的傳播和發展,隨著繪畫的創作和實踐的進一步深入,需要對前人創作給予總結和品評,因此,繪畫評論和繪畫史著開始創立,“六法”論的出現和發展與仕女畫的形成、發展和成熟是緊密相連、密不可分的,并在唐朝時期仕女畫中得到全面體現,也是這一時期的典范性繪畫。在這之后的五代時期以及其后的時代變遷,唐代仕女畫的“雍容瑰麗”的時代風格和主題特征乃至仕女畫隨著時代的變化,其本體風貌也隨之發生流變,仕女畫這一主題畫種始終與“六法論”共同發展。“雍容瑰麗”的時代風格和具有典范性特征的唐代仕女畫經過唐王朝二百余年的發展過程,其蓬勃生命力源于創作和實踐對“六法論”本體因素的體現和踐行,同時又能夠同步伴隨著“六法論”創新發展而發展,在其后的整個古代時期都不斷進展。這一時期的仕女畫發展順應時代發展要求做出了調整,“雍容瑰麗”是此時的時代特征,并從這種輝煌的震撼力中逐漸轉變為“娟麗清逸”的時代特色。例如,在唐朝以后的五代時期畫家顧閎中為代表的《韓熙載夜宴圖》中,仕女形象在遵循“六法”的基礎上,有了更多的創新和發展,利用線條和顏色來刻畫人物形象、傳達人物內心的情感活動,構圖上的重復和再現等都有創新發展,才逐漸形成這一時期仕女畫所具有的“娟麗清逸”的時代特色。兩宋時期畫家李公麟在仕女畫白描的創作中,對除了“賦彩”之外,其余五法都有不同程度的推進,他特別將墨分深淺應用在人物白描方面,在吳道子的線描技巧上有所超越。在元代,著名畫家、書法家趙孟頫著力主張“復古”,特別是在人物畫上主張“師唐宋”。這一時期的畫家如“吳興八俊”錢選等人在仕女畫方面取得的成就再次印證了趙孟頫“復古”的主張。仕女畫發展到明代時期,當代名流筆下的仕女畫都風格獨具、特色鮮明,如:唐寅的《王蜀宮伎圖》《李師師》畫中的仕女形象,四個宮女形象色彩清致雅麗,李師師形象墨韻高古,是這一時期仕女畫成就的代表;而陳洪綬繪畫中的女性形象的古拙之美深深地打動著后人,明代時期杜堇《宮中圖》局部《西廂記》中的女性形象和《水滸葉子》中的仕女形象都讓人印象深刻。清代以文人畫派為代表的費丹旭、改琦其表現的仕女形象則有閨秀、陰柔的“纖弱”特質,這些仕女形象的創作也是與時代發展相適應的本體進展中的積極方面。
縱觀仕女畫歷代發展特征,唐朝仕女畫的本體發展特征可以從“六法論”的六個方面來深入解讀:
(一)氣韻生動方面

唐代工筆仕女畫展現一種圓潤秀勁、雍容嫵媚和高古典雅之韻。謝赫的“六法論”之要“氣韻生動”這一論述受到東晉顧愷之“以形寫神”之說的直接啟示。唐代的仕女畫中的人物形象都是從生活點滴中觀察提煉得來的典型人物形象,是“悟對”即從審美對象中“悟”出“神”的形象。如《簪花仕女圖》中的形象傳遞出一種盛世中隱含的頹廢之感。通過對人物形象的挖掘和刻畫,表達了他們寂寞空虛、百無聊賴,別有憂愁暗恨生的孤寂之情,這也是宮廷仕女真實生活狀態的寫照。也如張彥遠所說“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在其間矣”并且“此難與俗人道也”的形象;唐代畫家筆下的仕女形象都以寫實手法描繪生活中所見“貴而美之”的仕女形象,通過形象的刻畫,闡釋出了高古典雅之韻的深層次美感,這便是唐代仕女畫精妙無比、魅力永恒之所在。
(二)骨法用筆方面
周昉擅畫貴族人物的肖像及宗教壁畫,尤其擅長于仕女畫的創作。他開始效仿張萱,后來又與其區分,將張萱簡化了的蘭葉描,后創造出了琴絲描,形如琴弦,線條挺直卻又不失變化,這種方法所繪制的長線條流暢宛轉,短線條精勁有力,充滿了節奏感。此法用筆改變了前人用筆的外漏張揚,變得含蓄勁簡,人物形象的描幕勾勒依照仕女的動態和身姿變化,剛柔相濟、頓挫自如。在《簪花仕女圖》中用淡墨細線勾畫人物的面部手部和青羅紗裙,更好地表現出了人物細膩的皮膚和紗裙輕薄柔軟的質感。其中的每一條線都不同于之前人物畫中的線條,簡勁而有力。貴族婦女身上的衣紋則是采用蘭葉描來描繪,用筆行云流水、生動有力,更好地表現出人物衣紋好似隨風而動的樣子。在《揮扇仕女圖》中,以游絲描為主,鐵絲描為輔,勾勒了13位動作神態完全不一的仕女,畫面線條流暢。周昉吸取了前人的經驗,對線描技法進行了有的放矢的創新,有力促進了后世仕女人物畫的健康發展,用墨濃淡相宜、勾線根據人物動態和形象粗細不一,注重線條和用筆的輕重緩急來描繪仕女形象,這在傳統的工筆人物畫史上也是一種創新。用線條塑造起來的仕女人物形象,讓人無從察覺用筆的變化,僅僅感受到了人物形象的藝術魅力,仔細揣摩方可發現線條起收筆間的寬松和筆鋒轉換,表現出柔中帶剛,寬松間嚴謹大氣的用筆。這正是在線條上典范性的“骨法用筆”之精妙。
(三)應物象形方面
唐朝仕女畫創作大多是按照寫實手法進行造型創作的,體現了“應物象形”的樸素本原含義。“應”為對應,“象”是摹神取象。整體為與對象的形神應和之意。初唐時期,人物畫家閻立本在對歷代帝王與侍臣描繪刻畫中,在比例上都做了夸張。在仕女形象創作上注重客觀描摹,清瘦的形象是這一時代階段中反映到畫面上的基本形態。盛唐時期畫家張萱,中晚唐時期的人物畫家周昉,他們作品之中的人物形象比例適中,與現實生活中的形象比例一致,人物的身高基本上遵循七個頭長的比例;依據人物的身份、年齡和閱歷特征之表現準確,如張萱的《虢國夫人游春圖》中的老侍女的形象生動自然,她小心謹慎地懷抱小女孩。用寫實手法塑造現實生活中的人物形象的還有《搗練圖》中的煽火女孩、《簪花仕女圖》中持蝶仕女,對她們的神態塑造中捕捉到了現實的形上之神,各個都心事重重,這些技法的創作和運用在侍女圖中都是顧愷之“悟對通神”“遷想妙得”理論的延伸和實踐。
(四)隨類賦彩方面
唐代絢麗多彩、恢宏富麗的時代畫卷正是見證了一個強盛而開放的王朝,與此同時造就了唐代仕女畫“隨時勢之類、賦現時之彩”的色彩特征,正是由于唐王朝的開放包容,畫家的用色賦彩沒有受到條條框框的限制(如元代紅色為官服專用等色彩),給了畫家極大的創作空間,使畫面的色彩上可以發揮得淋漓盡致,于是才有了畫家能夠把大唐麗人們精致獨特的妝容和裝束裝扮起來的面貌躍然紙上,有了張彥遠“近古之畫,煥爛而求備”的評價。我們對比六朝時期的仕女畫近乎白描,五代時期的周文矩的白描仕女、南唐時期的人物畫家顧閎中的彩色仕女畫偏冷調子,同時還可以拿宋、元、明、清帶有文人畫“清雅”特征的仕女畫來做對比,可以清楚地看到唐代工筆仕女畫在色彩方面隨時代之氣著色的獨特追求。
(五)經營位置方面
經營位置主要體現于構圖方面,但不僅限于此。唐代仕女畫的構圖特點普遍是無背景或簡單背景,僅僅依靠人物本身的動作和前后高低關系來“經營”,使整個畫面呈現出一種整體勢態的均衡,達到傳神達意之目的。由于此時期的人物仕女畫的畫幅有限,這里的“經營”位置不能夠通過人物面部的特寫來打動人吸引人,必須是以人物整體的手、眼、身、勢、步等方面的態勢進行構圖經營,使畫面連成一個互為呼應、互為平衡的統一體。《簪花仕女圖》中六位貴族仕女與侍女賞花游園,間以兩只小狗、一只白鶴、一束黃花襯托,使原本的孤立人物產生了左右呼應、前后聯系的關系。在經營位置方面,唐代工筆仕女畫的獨特特點是,遠近不同的人物和景物都給予同樣的刻畫力度和純度、明度一致的色彩,只是通過所占畫面的大小來區分遠近,以此來表現畫面中的縱深關系,而不是靠虛實和刻畫力度的大小來區分遠近。這種獨特的構圖方式,它的精妙之處在于隨著畫面的整體“氣韻”來安排物像在畫面中的位置,從而達到“傳”總體畫面“神”的目的。
(六)傳移模寫方面
我們能從閻立本對顧愷之,張萱對閻立本、周昉對張萱作品的繼承和借鑒中看得出來“傳移模寫”的痕跡。傳移模寫的本意之一是臨摹,這一點我們可以從顧愷之談臨摹《魏晉勝流畫贊》中看出,比如臨摹中的絹絲要對正,并且注意神氣等等論說。應該說,上述畫家之間的轉移模寫就是畫面繼承的結果。傳移模寫另一個意思是傳、移、摹寫物象之神。這點實際上也是臨摹要義:“師古人之跡,更要師古人之心”,通過師跡進而師心,看古人是如何傳、移、摹寫物象之神的,進而去生活自然中寫生,這是古人早已認識到的臨摹規律,也應看作是古人認識寫生的規律。
綜上所述,以張萱和周昉為代表的唐代工筆仕女畫,是中國畫品評和創作標準“六法論”之較完美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