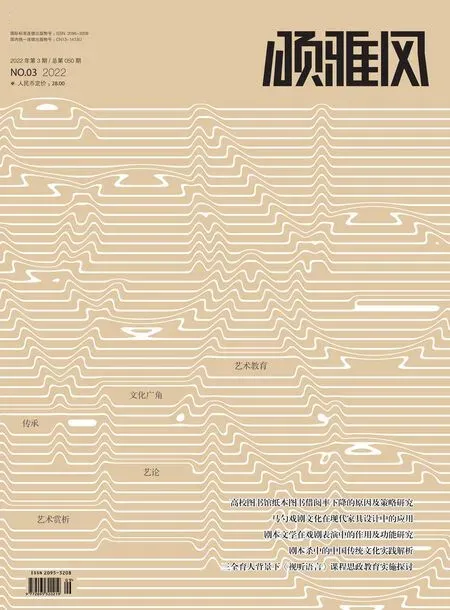關于 馬克斯·韋伯“合理化”思想的一種解讀
◎楊延杰
一、合理化思想是西方哲學發展過程中始終潛在的一個內在基因
歷史地考察,西方哲學經歷了從“仰望星空”到“腳踏實地”的艱難轉變,以蘇格拉底“詰問”的方式探究真理,作為哲學研究的開端,到柏拉圖以“理念世界——現實世界——有序世界”來構筑解釋世界的基本圖式,再到亞里士多德,系統化、分門別類式地深入研究,探究知識的邊界,規定認識的范式。沿著這一路徑,古希臘三賢完成了西方世界思維認知的整體圖式:以理性思考,以思辨分析方法,解釋世界,以邏輯規范推演,展望世界的未來。這一表達方式,是以合理化方式作為開端,也成為后來西方哲學進行建構的基本邏輯遵循。
古希臘神話故事中,有著諸多離奇古怪與荒誕不經,它卻深度契合著“神諭”和“宿命”,神話故事的經過都是對神諭的根本遵循和對宿命的充分演繹,這體現出先天既定與后天契合之間存在著最大的統一,這就從本初上體現出西方世界的合理化思想,也是潛在其意念中的“完美構筑”。在亞里士多德的世界里,“世界乃是由各種本身的形式與質料和諧一致的事物所組成的”,“形式”與“質料”的“和諧一致”,較為貼切地表達出世界構成的合理化意蘊。馬克斯·韋伯面對的是德國工業生產迅速膨脹的社會現實,作為一名學者,他要從學理的角度解釋資本主義生產大行其道的合法合理性,同時,他又十分重視精神、宗教、機制和制度等非物質性方面的原因,因此以反實證的研究方法,從宗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資本主義組織機制的高效化等方面突出強調精神、意志等因素產生的巨大作用,通過對比中國宗教、印度宗教、古猶太教對當地社會產生的不同影響,進而得出西方工業文明所謂的當然優越性。可以這樣說,承襲西方濃厚文化氣質的馬克斯·韋伯,先入為主地有著西方工業文明合理化的“藍本”,而后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反復尋找腳注佐證,得出其構思的合理性。因此,韋伯的學術視域中,合理化是被頭腦思維所左右了的,而不是被實踐生產決定的,他只是以學者身份宣揚西方根深蒂固的合理化思想,由此造成他的思辨深度不足,建設力度不夠,影響廣度有限。由于韋伯過早離世,使他對合理化思想的挖掘和展示中表達不充分:以天職為歸旨的合理化思想,表現出為完善資本主義制度積極佐證,為構筑資本主義精神努力做支撐,由于在實證方面存在著巨大瑕疵,很容易為后來學者揚棄,但是,韋伯對合理化思想研究中所關注的非物質性作用的傳統、學術建構中表現出來的特有氣質,都是在正確的立場上承載著西方哲學所稟賦的合理化思想。
二、馬克斯·韋伯對合理化的探索是一個由學術到實證、不斷精準化深入的過程
根據《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的解釋,“合法性”是指“某個政權、政權的代表及其‘命令’在某個或某些方面是合法的 ”,它是一種以價值觀念或建立在價值觀念基礎上的特殊判定。雖然韋伯始終沒有給“合理化”下定義,但合理化是他學術體系中一貫秉持和追求的思想。
(一)合理化是韋伯思想的一條基本之綱
韋伯出生于1864年,去世于1920年,他目睹了德意志民族從四分五裂走向統一,目睹德國在短短時間內實現經濟騰飛的巨大變遷,又經歷了德國挑戰國際秩序失敗的落寞,使他在精神層面思考德國資本主義的優越性何在,總結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高漲的機制何在,同時,結合西方文化合理化觀念對韋伯的耳濡目染,使他當然相信:合理化,是西方歷史、德國現實和資本主義世界未來逃脫不了的“神諭”和歷史宿命。因此,在韋伯的研究潛旨中,不知不覺為合理化理論給足了思想空間,合理化思想在學術研究中,就能以充足的勇氣擔當起解釋德國資本主義當然合法性的理論假設,以此為“官僚組織理論”“合理化”理論的出場提供了充足的假象空間和學理背景。這是韋伯在展現合理化思想中的一條基本之綱,也以此,韋伯的合理化思想包含著諸多豐富的內容要素,并隨著學術研究的逐漸深入不斷推進,從而使“合理化”思想在韋伯的視域中不斷獲得豐滿。
(二)合理化是韋伯學術探索的一貫追求
在學術研究中,韋伯始終帶有很強的問題意識與獨特的研究方法,他闡述了統治的“正當性”或“合法性”問題,指明了現代社會政治合法性的演進方向即在追求“法理型”統治,同時指出,現代社會的演進趨勢是,實質理性不斷萎縮和形式理性日益擴大這一看似悖論卻又無法克服的矛盾現實。在現實分析中,通過對于宗教和職業關系的研究,韋伯發現,研究不同的宗教,對比職業選擇、技能程度、精神氣質、財富狀況與宗教信仰,弄清它們現在或曾經具有哪些特殊因素可能引起研究需要的行為,能夠搭建起新教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直接聯系,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現代資本主義精神的一個根本要素,即以天職觀念為基礎的合理行為,乃產生于基督教的禁欲倫理。這恰恰表達出韋伯以天職觀念為歸旨的合理化追求,主要意思是:1.天職觀念是合理化思想的立論基礎,“天職”本身包含人的認識合理化和目的合理化。2.天職觀念是合理化的全部表達,服從天職就是順乎了合理化。3.合理行為將使合理化在具體實踐中以更加科學有效的方式向著“合理化”目標推進。這一思想的成熟過程,顯得異常艱難而又十分重要。
(三)合理化是韋伯直面現實問題的始終品格
韋伯與馬克思、涂爾干并列為現代社會學三大奠基人。馬克思基于“現實人”即無產階級的勞動者出發,深刻批判資本主義的生產性危機,揭露出危機只能醞釀更嚴重的危機,最后摧毀資本主義制度,并以此呼吁,實現每個人的全面發展達到“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科學社會主義。涂爾干把孔德的實證主義研究嫁接到社會學領域,開啟了社會學的實證主義分析研究。與之不同,韋伯的“天職”“合理化”思想的建構,是面對現實的反實證的復雜性思考,是對精神力量的“物質性”考量,是在強調,合理化既包含物質組成,包括一整套制度設計,還包括潛藏其中的精神文化,而其各構成之間有機協調、契合縝密,各歸各位是謂“天職”,共同推動著資本主義的飛速發展。韋伯以社會學研究視角,解釋了德國資本主義的當然合理性,為長期四分五裂的德意志民族重歸統一助長起一股精神自信。
如果說涂爾干的成功是“嫁接”了孔德的實證主義理論,那么韋伯就是吸收黑格爾關于“合理”的表達、馬克思關于社會理論豐富性的表述,建構更為全面的“合理性”,一廂情愿捍衛資本主義正當性。在《經濟與社會》中,合理性是指人們逐漸強調通過理性的計算而自由選擇適當的手段去實現目的,它區分為工具合理性和實質的合理性。他通過研究得出“近現代理性觀念所經歷的是一個實質理性不斷萎縮,工具理性不斷擴展的演變過程”,把研究伸向工具理性,特別是1889年《中世紀貿易公司的歷史》和1891年《羅馬的農業歷史和其對公共法及私法的重要性》兩篇文章,使他意識到歷史地考察事物發展變化規律的重要作用,與馬克思不同,韋伯沒有能夠深刻揭露勞動異化而產生剩余價值,而是從組織生產的各要素分析正當合理性,證明現代組織結構的重要性,論證資本主義精神的有效性,直到詮釋資本主義何以能蓬勃向上。他進一步指出,德國的飛躍是新教倫理精神與帝國制度的完美結合,展現出一整套文化、精神、制度在合理化過程中的自洽,展現出新教倫理精神驅動的優越性,這是韋伯非理性思維的全方位表達脈絡,然而,卻又陷入現實的重重矛盾和無法克服。
三、異化、非理性現實使韋伯的合理化構建在內外交困中無力向前
我們看到,在描述社會大工業生產時,韋伯以盲目樂觀向上的心態為資本主義大唱贊歌,從宗教改革的積極因素中探究新教倫理對生成資本主義精神的重要作用,贊揚所謂的資本主義制度在德國表現出的優越性和西方工業文明的優越性。然而,他沒有從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深厚根基出發剖析整個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造成了“合理化”思想沒有力度和深度,既不成熟也不完善,我們看到,韋伯學術成就的背后,始終無法調解一個復雜局面,致使他的精神一度失常甚至崩潰,這也就注定“合理化”思想是戛然而止的半成品,然而,他對解釋世界的嘗試、對追求美好制度的期望的滿腔熱忱,無疑具有重大的啟迪意義。

(一)資本主義的現實使合理化的實現顯得異常艱辛
通過對當時德國資本主義社會的考察,韋伯發現了資本主義合理化的另一面——因為異化而扭曲了合理化,使科學技術、工業文明走向邪惡化,人類社會的牢籠化,對單個個體的禁錮,健康向上的資本主義精神的被淡化甚至可能走向它的反面,從而形成一種十足的無序和“非理性”。韋伯對資本主義的系統性診斷,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深刻警惕,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精神的充足自信上,其目的是對資本主義精神的堅守、捍衛和宣揚,而不是對其鄙夷和排棄,所以,為了克服這些問題,就要恢復實質理性的應有地位,把價值、目的、意義等重新引入科學的范疇,對科學技術在工業社會及其文化系統中的角色加以重新定位,從而更好地推動資本主義社會的合理化進程。然而,克服異化顯得異常艱難和艱巨。
(二)非理性與復雜性在實踐活動中的作用難以把握
韋伯所處的時代,是實證主義和唯物主義蓬勃興盛的時期,而他獨辟蹊徑地引入與唯物主義、實證主義相反的研究方法,在捍衛資本主義世界合理性的同時,他試圖探求復雜性歷史因素中的非物質力量的重大作用,他說:“我們只想探究,在什么程度上這種文化的特定性質可以歸因于宗教改革的影響。同時,我們必須擺脫那種認為宗教改革可以從一定的經濟變化中源起,并且是歷史必然結果的思想。”可以說,韋伯面臨的問題是對當時占主導地位的主流思想的全面與否的深刻隱憂,是對用一種方法、一種主義解釋并涵蓋世界全面性的懷疑與困惑,他在強調新教倫理能夠催生出資本主義精神、資本主義制度的同時,更是把人類認知世界的視野引向深遠的復雜性和全面性的領域。這是韋伯開啟的一片研究界域,而這一任務任重道遠。
(三)個案分析與合理化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理論裂隙
韋伯通過社會調查、歸納分析、綜合演繹的一系列社會學研究方法,得出的結論的準確性和有效性有待于進一步佐證,并以茲跨度到宗教、精神領域,橫向比較新教與中國宗教、印度宗教、古猶太教的優劣差異,探尋精神的實際效用,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種形式化運動過程。他曾自豪地說“今天,流傳最廣的合法性形式是對‘合法律性’的信仰”,至此,“馬克斯·韋伯構建的現代合法性模式已經完全變成形式主義”。而韋伯的矛盾恰恰在于:復雜性地考量資本主義社會的全景式問題時,卻是由現實的“個案”甚至是精確到“個人”的理性算計、實證對比研究來完成,因為過于注重形式理性的重要作用而忽視了實質理性的內涵,不可避免地使合理化存在瑕疵,其中缺乏嚴密的邏輯銜接,由此而產生的對接裂痕無法消彌。
韋伯對合理化的描述和對“天職”觀念的構建,亟待在當今社會實踐中進一步討論挖掘,使合理化思想在服務現實的科學發展中,更加具有正確的引導功能和科學的構建功能,使前人的豐富思想成果能夠科學地服務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我國的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戰略貢獻出應有的理論養分和思想價值,使我國“以人民為中心”的新發展理念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宏偉愿景更生動地貢獻出全新的“中國方案”。